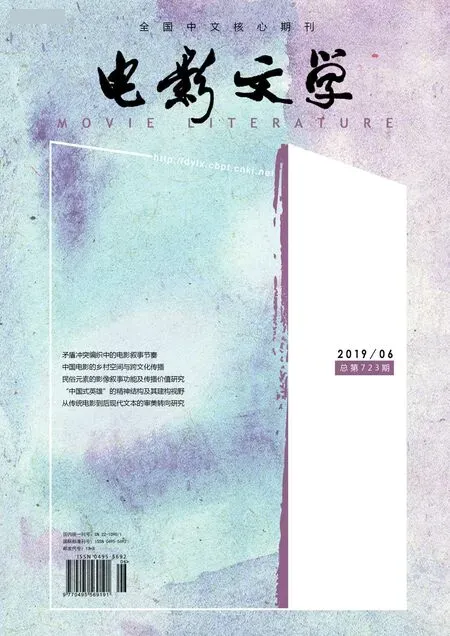《戰狼》系列“英雄”與“國家”的成長敘事芻議
沈維瓊 (新疆師范大學,新疆 烏魯木齊 830054)
近年來,國產主流電影體現出了強烈的類型自覺,以《集結號》《湄公河行動》為代表的國產大片,努力將類型片模式和社會主流價值相結合,以通俗且傳奇的言說方式、易于接受的類型手段、超級英雄的形象塑造,配合家國一體的愛國主義、大國崛起的民族自信、天下大同的人文情懷等精神內核,令這些影片能在票房和口碑上獲得雙贏。在多部佳作的映襯下,《戰狼》系列作為一種“現象級”的存在,不僅在類型自覺上可圈可點,在票房上也獲得極高的成績,《戰狼2》甚至“燃爆”2017年暑期檔中國電影市場,“上映4個小時過億,25小時過3億,46小時過5億”[1],最終以近57億的票房穩居亞洲影片票房第一位,并成功躋身全球票房Top 100。
兩部《戰狼》的大獲成功,當然要歸功于視聽語言的流暢與精益求精,技術、表演、取景等方面的匠心是可見的,尤其《戰狼2》開篇6分鐘的長鏡頭被很多影迷和評論者津津樂道,在藝術呈現上也完全能夠載入中國動作電影史冊。但真正值得思考和探究的是這個電影系列在類型敘事、精神價值和文化歸依上的潛在言說,尤其是關于“英雄”與“國家”的成長敘事,以類型模塊和潛隱話語碰觸到了藝術與時代的脈搏。
一、“敵人統一化”策略
《戰狼》系列成功運用了商業類型電影的敘事經驗,吸取了動作片、戰爭片、軍事片乃至公路片的類型元素和戲劇沖突。其類型特征被歸結為一種以“現代動作片為主打類型,兼容戰爭(軍事)電影,好萊塢超級英雄亞類型電影,折射中國武俠動作電影等的強強結合,強情緒強節奏的‘類型加強’型電影”。[2]多重類型的雜糅和喜劇效果的融合,在貢獻視覺奇觀的同時也讓藝術接受成為一件輕松和順理成章的事情。同時這種多元類型復合的模式在處理相關敘事場面和段落時具有較高的復制性,實際上,類型電影就是“為了滿足觀眾的娛樂消遣需要而創造出來的具有某種可復制性,甚至批量化生產的電影系列產品”。[3]
這種可復制、可辨識的敘事模式、軌跡和元素是類型電影敘事成功的一種保障。拋開具體如動作片、戰爭片等類型要求,《戰狼》系列具有一些共性的鮮明敘事特點,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在核心矛盾的處理上——兩部《戰狼》均落實了“敵人統一化”的策略:《戰狼》中大毒梟敏登誓要為被武警狙擊的胞弟武吉報仇,并且認定仇人就是射出子彈的狙擊戰士冷鋒,隨著冷鋒所在部隊與雇傭軍的不期而遇,二人狹路相逢并一決生死;《戰狼2》中遠走他鄉的冷鋒本是為替因執行任務或已犧牲的女友龍小云報仇,但在亂世意外成為保護華僑的一把利器。由于被冷鋒救護的黑人小女孩是雇傭兵領袖“老爹”的爭奪對象,所以二人糾纏不休,直到終極對抗時,冷鋒才發現此人正是自己苦苦尋找的仇家。
兩部電影均以家仇與國恨疊加的方式,讓男性英雄完成國家使命的同時也解決了個人恩怨。這種“敵人統一化”的敘事策略,將個人情感和國家使命高度統一,成為“十七年電影”時期的主體模式,后在主旋律電影中亦得到最充分的體現。代表作如《白毛女》《智取威虎山》《閃閃的紅星》等,均將“家族恨”與“階級仇”巧妙地融為一體,家國一體的仇恨及復仇成為新中國電影主流價值觀訴說的一種顯性策略,這種策略隨著不斷的延續已形成某種約定俗成,直至新世紀的國產主流電影都強弱不一地保留和呈現著。
從敘事和接受效果可見,“敵人一體化”策略在調動共性情感、增強民族凝聚力上的力量是非常強大的。傳統中國“家國一體”的社會政治結構與“忠”“孝”核心價值觀讓“國仇家恨”構成“復仇”主題的雙向統一性。當然,在這一共性的設置上,《戰狼》系列在具體“復仇”線索上的安排是有差異的:《戰狼》中反派人物敏登是主動出擊的復仇者,主人公冷鋒只是在被動承受。這樣設計的目的,當然首先要強調敵人的狹隘與無原則、無底線,但更重要的是要突出冷鋒所代表的“軍人”身份和價值。軍人的純潔決定冷鋒必須身家干凈,他身上不應該沾染仇恨的因子,甚至不應該有與境外毒梟私人間的關聯,如果產生了關聯那必須是對方蓄意為之。雖然冷鋒背負了父親的心靈創傷,但父親的創痛是“忠”與“義”取舍上的不可兼得,而“為國盡忠”的選擇不僅沒有錯,反而應該嘉獎。兩代人的負罪只是在證明英雄的正義和俠骨柔情,也強調軍人的自律之美。
另外,冷鋒的被動性設計具有鮮明的歷史隱喻意味。在空間場域的設置上,《戰狼》將云南邊境線作為戰斗高潮的展開地,毒梟與外國勢力雇傭兵的雙重身份結合,讓這場戰爭不僅具有緝毒的社會責任,也具有抵抗外敵入侵的政治使命。“毒品”對國人而言是有著深刻的歷史負累的,而“緝毒戰”自林則徐虎門銷煙開始就成為中國洗刷“東亞病夫”恥辱的核心戰役。毒品對國人來說不僅是一種摧毀身心的物質存在,也是西方列強欺凌中華民族的歷史恥辱柱。冷鋒與戰友的浴血奮戰和九死一生的勝利,其民族自救和洗刷歷史恥辱的意味是十分強烈的。
《戰狼2》延續了第一部的故事脈絡,但這一次卻將冷鋒處理為主動的復仇者,盡管復仇的最開始所要面對的敵人并不明確,但由于以“老爹”為首的雇傭兵處處威脅非洲平民和中國僑民的生命安全,讓冷鋒一次次地和“老爹”交手,并在最終決斗中通過螺旋花紋的子彈,發現老爹正是苦苦尋找的殺害女友的兇手。尋找兇手是冷鋒踏入非洲土地的原因,但戰亂四起之時,私仇被擱置,直到最終決戰之時,“老爹”射出的子彈和冷鋒懸掛胸前的子彈一致,此時國仇、家恨的兩條敘事線才相交,“老爹”也明白“現在是私人賬”更是挑明了這一點,而冷鋒“血債血償”的回答和致命重擊不僅是為死難平民和同胞復仇,亦是為女友復仇——家與國緊密相連,個人與祖國休戚與共。
“塑造同一個敵人”不僅讓具體的事件陳述和英雄塑造得以從容展開,而且“家”“國”同構后的共情也更易引起共鳴,配合二元對立的人物和矛盾構成,觀眾的民族情感和歷史情懷被點燃。這種策略是主流類型電影敘事最易操作也最見成效的,當然為了這一敘事慣例的實施,有可能會影響到故事的邏輯性,如《戰狼》毒梟與雇傭兵身份和任務的過度巧合、《戰狼2》中“老爹”忽高忽低的智商及對冷鋒莫名其妙的趕盡殺絕。應該說,這一帶有樣板戲意味的敘事策略盡管討巧,但必須付出一些代價,所以邏輯硬傷的出現幾乎不能避免,所幸“戰狼”系列以英雄的完整圖譜和大國自信的精神內核對敘事進行了彌補抑或掩蓋。
二、英雄的成長和完整英雄圖譜的構建
兩部《戰狼》講述各自的核心故事,但均一致弘揚中國軍人不畏艱難、保家衛國的精神,強化了強大的愛國情懷和自尊自信的中國人身份。在對“英雄”的塑造上,《戰狼》系列是不遺余力的,其中既有英雄之殤,也有英雄之難,在見證英雄成長的同時以一帶多,最終勾畫出完整的英雄群像,經由英雄們共同守護的核心價值在層層強化后成為堅強的誓言,“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體現出鮮明的主流意識形態特征。
在《戰狼》中,冷鋒是有著個人傷痛記憶的特戰隊員——亦是武警出身的父親為曾經執行任務被迫殺死負傷戰友而備感痛苦,深刻的負罪感不僅令冷鋒父親終生未能走出道德的審判,而且被兒子幾乎是“父債子償”地主動承擔。這種基于人倫情感的審判成為冷鋒的職業倒刺,他試圖用痞性十足、玩世不恭的方式去掩蓋心靈創傷,直到創傷情境的重現:所在特戰隊隊長被敵人狙擊手射中失去行動能力,戰士的營救只是制造了又一個死亡,隊長聲嘶力竭地“解決”自己的請求讓冷鋒明白了父親當年的迫不得已。所以這一次他必須得去改變結果,完成救贖,包括為父親正名和拯救自己。大隊長的成功得救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冷鋒作為英雄首先需要實現的自救,只有完成了自救的任務,才能順利地成為一名合格的軍人,之后才能去完成救人和救國的使命。最終冷鋒不僅完勝敵人,而且截獲了記錄國人基因圖譜的血液樣本,讓國人又一次躲過了可能帶來民族危機的敵國的滅種陰謀,“救國”和“救國人”的任務初戰告捷。
《戰狼2》順理成章接過了英雄塑造的第二棒,將“救人”擴大為不僅“救國人”,而且“救所有可救之人”。冷鋒踏上非洲本是為了個人復仇,但踏入亂世后,復仇的任務由于目標不明而被擱置,于是“解救”主題成為人物主要的行動力——冷鋒在槍林彈雨中不斷地進行著解救,這個解救從解救“干兒子”土豆到解救與自己有嫌隙的奸商,再到救助素不相識的人們,從拯救同胞到解救華資工廠的所有員工,冷鋒完成了英雄主義的升華和最終確實——強大的國家是他的堅強后盾,他的任何勝利都代表著國家/民族的揚眉吐氣,真正的英雄是必須舍棄個人恩怨,也必須始終為正義、為民族、為國家而戰。
愛國主義是《戰狼》系列電影的主基調,兩部影片均將英雄人物對國家利益的保護和中國國旗及中國護照的能量強調作為核心。作為新時代國民形象的代表,冷鋒不惜生命沖鋒陷陣、救民于水火,就是“為國為民”的現代“大俠”。不僅如此,第一部中的“大俠”冷鋒到了第二部已經成長為人類的、國際性的“人之子”冷鋒。兩部《戰狼》由此完成了從國家性的愛國主義敘事進入到國際性的人道主義敘事。
在進行英雄“成長敘事”的同時,兩部《戰狼》又完成了“民族悲情英雄”和“民族自豪新英雄”的巧妙轉換。
雖然不同于以《霍元甲》《黃飛鴻》為代表的傳統功夫電影塑造國家積貧積弱時代背景下的悲情英雄,但《戰狼》中冷鋒的“民族悲情”以隱喻的方式被呈現。盡管冷鋒是新時代新世紀的英雄,但他依然承載著歷史的重量,這個重量不僅來自父輩,更來自民族的被欺辱史。作為特戰兵,冷鋒在開場就與武吉率領的國際販毒組織交戰,這種不太符合作戰邏輯的劇情設計當然是在強化“毒品”作為國家/民族恥辱柱的意義,于是冷鋒的“緝毒初戰”與“緝毒決戰”都包含著為父輩復仇的言說欲求,而改造民族被奴役的歷史記憶對任何一個時代英雄來說都有承受歷史、訴說民族悲情的必然意味。
《戰狼2》中,面對受難的同胞和非洲難民,冷鋒在盡其所能地進行救助和保護,貧民區分發食物、街頭槍戰中保護平民……在華資工廠,工廠具體負責人林志雄強行將工人分為中國人和非中國人后,面對數倍于中方員工的非洲工人的求告無門,身處樓上的冷鋒以上帝的視角悲憫地觀看,最終發誓將帶走這里的每一個人——“我就是為他們而生的”,這種豪情和自信既來自英雄的本能和使命,更來自英雄身后的在世界新格局下日益強大的祖國。
除冷鋒外,“前輩”何建國、“后輩”卓亦凡以及中國大使館樊大使、醫學專家陳博士和身為現役軍人的海軍艦長,一個新時代英雄的群像被完整建立。不難看出,這一英雄圖譜具有前后承繼、彼此協同的關系,老中青的完整配置同時又囊括了政府、軍隊與民間,把新時代新英雄以生命和人民名義的普遍性和統一性做了強化。
在愛國情感上,“為國為民”是英雄行動的基本動能,因此“敵人”必然是非國人的,即曾經侵害或正在損害中國的外國敵對勢力。《戰狼》系列把終極敵人設置為來自歐洲的雇傭軍,他們純粹的白人樣貌和身體特征完全符合國人對歐洲人的想象,而雇傭軍的殘忍野蠻與自清末開始奴役中國的歐洲列強構成了強烈的關聯性。于是,冷鋒及其所代表的中國軍隊所取得的最后勝利在國家/民族層面,就具有鮮明的敘事訴求,即伴隨中國的偉大復興,中國已經具備了和歐美國家博弈的政治、軍事、經濟實力。以冷鋒為代表的中國男性英雄的智勇雙全和冷鋒的“那他媽是過去”的經典臺詞讓“東亞病夫”這一濃縮著民族之殤的稱謂成為“被終結的歷史”——新的時代已經被創造,那就是中國的崛起。
“英雄主義是人類社會由野蠻向文明演進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種具有集體意識的精神價值觀,它具有鮮明的民族和國家特色,有強烈的歷史感、時代感和人格的震撼力。”[4]在《戰狼》系列中,冷鋒從第一部“痞子英雄”到第二部“超級英雄”的成長,英雄特質的升華期間編織的是國家意識形態的符號代碼,代表了國家力量和民族自信的自覺承載,也代表“大國崛起”的時代命題下中國的國際形象訴求。
三、大國形象的文明特質
《戰狼》系列的走紅,根本原因在于影片對國家形象的持續性建構上,這種源于國家實力和國際威信的自信,通過兩部影片所呈現的國族符號、所傳達的群體心態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心理,建構起了一個強大、成熟的大國形象,并由此打破了“東方只能被西方定義,不能進行自我定義”[5]的神話,表征了中國在國際上開始擁有自我言說的權利。
在構建大國形象的過程中,電影在視覺形象上積極使用了圖解化的方式,如強大的軍事能力和精良的武器裝備,尤其《戰狼2》中,航空母艦被不同的景別、多樣的視角全方位地給予了展現,中國超強的軍事實力不容置疑。
在視覺形象累積的基礎上,影片又通過英雄的行動進行深度言說。《戰狼》系列以陽剛的男性氣質和國際背景下的人道救助講述著中國的“崛起”,但電影并沒有簡單停留在“大國”實力的展覽上,而是通過英雄敘事,對中國的國家形象和文明特質進行了展現——冷鋒作為男性的、理性的超級英雄,他的救助對象是不分國別和身份等級的,白人、黑人,中國人、美國人、非洲人均在他的解救中,“全人類守護者”的意義非常鮮明——中國的崛起根本不是通過創造和復制資本主義罪惡而生成的經濟、資本強權,而是站在全人類的視角和世界性格局上,在與第三世界被壓迫被奴役的人們休戚與共、攜手并肩過程中,主動站出以維護生命的平等權利、抵制霸權強權,并最終構建和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終極使命。
如果說《戰狼》還是基于救國情懷的愛國主義,到了《戰狼2》,國家與民族的設置被放置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國際人道主義援助的敘寫完成的是對新世紀中國國際新形象的確認。電影中,亂象叢生的“非洲”、貪婪兇狠的“西方”世界、守護生命的“中國”被分置,其上附加的是惡與善、過去與未來的倫理和價值判斷。其中,以陳博士為首的中國醫療隊對非洲瘟疫展開的積極有效的救治和疫苗研發,其救援不僅是技術幫助,更是生命救護。電影中中國烈士的墓碑層層疊疊,記錄著中國派至非洲展開醫療、建筑等人道援助而犧牲的英雄生命。中國的國際人道主義行為和精神通過墓志銘的形式被傳達,這時的愛國情和民族志已經上升為救助貧弱國家的大國自信和自豪——中國早已洗刷了“東亞病夫”的恥辱,在實現自救后獲得大國尊嚴,而這一尊嚴又通過維護和平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切實奉獻來加強。
在當下現實中,非洲的確是災難深重:以索馬里為代表的東非國家深受海盜之苦,西非的埃博拉病毒肆意蔓延,南蘇丹內部不間斷的熱戰,等等。但這些苦難并未全部集中于某個特定國家或區域。然而在電影中,這些苦難被聚集在一起,加上撤僑所指涉的中國2011年敘利亞、2015年也門的兩次大規模撤僑行動,“非洲”成為“種族苦難”的展演地,“等待拯救”就成為“非洲”想象的基本特征。
《戰狼2》中,攜帶埃博拉病毒自愈抗體的非洲小女孩帕莎無疑是一個既象征歷史又隱喻現在和未來的符號。當現實空間中,埃博拉病毒在非洲裔有色人種中肆虐的時候,關于基因病毒戰的假設被提出,即這極有可能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針對非洲有色人種的一次基于基因圖譜的生化武器試驗。對經歷過SARS瘟疫的國人來說,SARS病毒在華人中的流行、白種人與黑種人均有先天不敏感等怪相令國人部分地認可這一假設,第一部《戰狼》也以敏登搶奪記錄國人基因圖譜的血液樣本企圖進行細菌戰的陰謀實施為主要敵方行動,無疑又在暗示關于基因病毒戰的假設。如果這個假設成立,那么這一帶有病毒自愈抗體的非洲小女孩帕莎就是對美國勢力具有先天抵抗力的新一代非洲人民的象征。這一代非洲民族已經從曾經的被殖民和臣服、追隨美國的歷史慣性和泥潭中覺醒,因為這條老路意味著種族的滅亡,只有自身產生對美國勢力的抵抗才能帶來可能的種族延續。小女孩帕莎固然尚在童年,但她的女性身份意味著假以時日,她的繁殖能力和價值就會產生并迅速放大,非洲也由此獲得種族的延續。而這一切需要首先獲得自救的中國伸出援手才能維系和發展。中國與第三世界國家不僅是睦鄰友好的同一戰壕的戰友,而且可能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快速發展的順風車上會有它們的搭載。由此中國在國際形象上的意義就不僅僅是“救助和庇佑”這么簡單了,這種強大的國家觀和自信的民族觀,成為《戰狼》系列病毒和人種設置的深層話語。
四、性別敘事的深意
從性別角度而言,民族國家是男性政治的產物,在藝術世界里,男性、理性、陽剛與女性、感性、陰柔的二元對立模式是故事矛盾展開、影像系統風格化的一個向度,性別權利話語及其價值判斷在電影世界中具有強烈的滲透力。
在《戰狼》中,唯一的女性是特戰中隊的女隊長龍小云,雖然她美貌誘人,但這也僅僅是面對冷鋒的時候,影片更多時候強調的是她高超的軍事技能和先進的戰斗能力。在演習中,她準確判斷,迅速在敵方主控系統中植入病毒,讓其電子戰能力近于癱瘓。因此龍小云最主要的敘事動能在于體現現代中國軍人及其軍隊的強大,在這一面上,她是無性別的。在另一個向度,龍小云為數很少的幾次體現女性特質的情節都是面對冷鋒或被冷鋒的言行催化的時候——只有男性以更強大的樣貌出現,女性才自覺恢復女性特質,這實際上實現的是對男性英雄的烘托,女性特征在此時并不承擔更重要的敘事功能。
到《戰狼2》,女性身上被設置了國家、民族的信息,女性開始參與國家敘事,即塑造國家形象和強調文化認同。除帕莎所指涉的非洲種族延續的意義外,女醫生蕾切爾的設置強調的也是女性身份與美國國籍的結合,其符碼意義亦是被美國主流政權和文化拋棄的邊緣、弱勢人物。華資醫院被“老爹”控制慘遭屠戮的時候,蕾切爾挺身而出,冒著生命危險頂替陳博士,突出了其作為個體的優秀品質。然而,這樣一個優秀的美國女性第一時間被祖國拋棄——蕾切爾對冷鋒的救援開始時是不屑一顧的,因為她篤定美國大使館會救助每一個美國公民,直到被告知美國的救援艦已經駛離,她已經被遺棄。蕾切爾的遭遇一方面揶揄了所謂的“強國”在“等待救援”這一關鍵時刻的缺席,更表征了美國“恃強凌弱”的人權特征——它保護的是資本而不是人,不論這個人有多么優秀。這種狹隘的人權價值觀正是美國在國際舞臺上江河日下的根本原因所在。
雇傭兵領袖“老爹”作為白種男性,他的非理性殘暴特征暗示著第一世界的霸權話語,資本的原始積累和不斷擴充就是以屠殺和清繳為基本動素。“老爹”給冷鋒制造的困難盡管在敘事合理性上有待商榷,但這是基于對“西方”霸權和戰爭隨意性的一種指涉。“老爹”對所見之人不留活口的清理,甚至對雇主奧杜教軍的射殺,都在著力強調霸權國家或勢力對國際規約及游戲規則的蔑視和踐踏,對權利、資源的隨意處置、肆意占有等反人類特征。
在人性悲憫的層面,如果說《戰狼》還有民族雪恥的鮮明印記,那么《戰狼2》就是男性英雄拯救包括強大國家的被拋棄者、弱小國家未來希望的承載者,彼此形成的聯合抗暴隊列又構成了無差別的命運共同體,以中國為根本力量形成了拋卻一切差別的國際統一戰線,在國族認同的基礎上實現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審美化想象。由此,《戰狼》系列實現了從“小我”的民族大義到全人類人道主義的過渡,點燃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時代激情。
“拉康意義上的‘他者’永遠是自我的‘他者’,他國形象即是一國自身欲望的投射對象。電影中,自我與他者互為鏡像:第一世界與第三世界,強權與受難,殘暴與友好,不義與正義,二元對立的形象符號具有明顯的價值指向。”[6]《戰狼》系列通過多重隱喻,以愛國主義和國家敘事將中國塑造為強權西方的對立面——以和平共處和人道主義為終極宗旨,不畏強權、守護生命、伸張正義、傳遞友好,這些特質共同構成中華民族的大國威儀。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性命題下,在世界格局新變中凸顯著中國的獨特和力量——中國才是世界和人類未來的希望,中國是且必須是未來的希望,如果中國沒有未來,那么世界就沒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