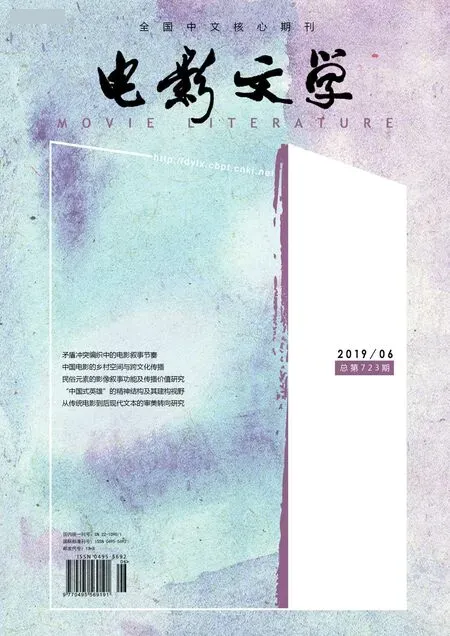濃妝淡抹總相宜:美國動畫成功改編啟示
時春風(fēng) 王 馨
(1.無錫太湖學(xué)院 藝術(shù)學(xué)院,江蘇 無錫 214064; 2.江南大學(xué) 數(shù)字媒體學(xué)院,江蘇 無錫 214122)
民族審美特質(zhì)是指被本民族認(rèn)同的、凝結(jié)著本民族傳統(tǒng)文化精神,并體現(xiàn)出民族尊嚴(yán)的文本、形象、符號和文化,是一個民族文化底蘊的流露。在紛繁的科技化和商業(yè)化迅速發(fā)展的現(xiàn)實社會中,人們常常會駐足回望歷史,渴望本質(zhì)的回歸,而弘揚民族特質(zhì),讓經(jīng)典再度流行,一直是影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越來越關(guān)注的一個焦點。當(dāng)然,對于全球的文化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大國——美國來說也無不例外,獨具民族審美的文化特質(zhì)從來都是迪士尼、夢工廠等動畫電影編劇和導(dǎo)演青睞的改編方向,在對文化內(nèi)容的重新編碼和整合上發(fā)展動漫創(chuàng)意產(chǎn)業(yè),也在吸收世界各國民族元素的基礎(chǔ)上促進文化的融合創(chuàng)新,更在引人入勝的影像敘述中滲透進美國的主流價值觀,并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觀影者的價值體系、思想判斷和道德情操。
一、改編歷程:忠實與創(chuàng)造
早在20世紀(jì)30年代,迪士尼就制作過許多根據(jù)外國名著,包括神話、民間故事和童話改編的頗具民族特色的動畫電影,如《白雪公主》(1937)、《木偶奇遇記》(1940)、《仙履奇緣》(1950)、《睡美人》(1959)、《小熊維尼歷險記》(1977)、《奧立華歷險記》(1988)等,這些故事經(jīng)由大眾教育、圖書館、出版機構(gòu)等眾多傳統(tǒng)媒體途徑,已然成為一個民族文化意義的精神文本和集體經(jīng)驗的記憶范本,美國動畫人在忠于原著的基礎(chǔ)上,大膽創(chuàng)新突破、另辟蹊徑,希冀用民族元素和異域風(fēng)格更大地拓展美國動畫電影的廣闊市場。
迪士尼改編動畫首先從人物造型上開始變革。如電影中的公主形象從早期的《白雪公主》里傳統(tǒng)歐美白人面貌向“國際化”方向發(fā)展,無論是《美女與野獸》中純真自然的貝兒公主、《仙履奇緣》中充滿智慧的仙蒂公主、《阿拉丁》中熱情開朗的茉莉公主、《小美人魚》中頑皮可愛的愛麗兒公主還是《睡美人》中溫柔婉約的愛洛公主,都融入大量的民族化審美特質(zhì),獨具異國情調(diào),別有一番風(fēng)味。而其中最特別的應(yīng)該是《失落的帝國》中的姬塔公主,阿拉伯、希臘、中國等畢竟都是現(xiàn)成文明,亞特蘭提斯卻是一個想象的世界,跟之前不同,迪士尼必須先創(chuàng)造出那個世界的風(fēng)格特色,發(fā)展出一套“Atlantis-Style”的特色之后,再將其融入電影的畫風(fēng)之中,姬塔公主的造型融入了許多古國文明族群的特色,包括希臘人、中東人、中國人、亞馬遜女戰(zhàn)士等,[1]因此,人物的性格也兼具美麗、勇敢、智慧和好奇,是一個既具民族特色又兼帶全球化的角色。
到了20世紀(jì)80年代,美國人在一般語境下的“政治正確”意識開始抬頭,為了避免出于種族、性別、性取向、身體殘障、宗教或政治觀點的不同而產(chǎn)生的歧視或不滿。動畫支持者試圖喚醒公眾的無意識偏見,使得他們可以有一個更加正式的語言,可以稱為與大眾不同的人群,迪士尼動畫此時更加關(guān)注多樣的民族題材,反對種族歧視,打破等級權(quán)威,賦予少數(shù)異族人群以話語權(quán)。《小美人魚》(1989)就是這一思潮下的集大成者,電影改編自丹麥著名的安徒生童話《海的女兒》,來自大海的人魚公主愛麗兒愛上了人類王子,為了融入人類世界,她用自己的聲音換取了一雙腿。在劇情方面迪士尼有所創(chuàng)新,把原本悲慘的結(jié)局改成大團圓,在紅蟹賽巴斯丁、比目魚小胖等朋友的幫助下,心地善良的人魚公主感動了海洋之神,海洋之神賦予了她永恒的靈魂。本片開創(chuàng)了迪士尼動畫的第二黃金時代,讓原本已趨沒落的百老匯歌舞片在動畫里找到新生命。
90年代迪士尼公司開始向迪士尼帝國(The Disney Empire)邁進,推出了一系列代表性的經(jīng)典名片,其中根據(jù)法國神話故事改編的《美女和野獸》(1991),也是迪士尼第一部改編為音樂劇的動畫電影,并獲得了1992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的提名,在2002年推出重拍了IMAX完整版。《阿拉丁》(1992)取材于阿拉伯民間故事《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拉丁神燈》,講述了蘇丹王朝時期阿拉丁王子與茉莉公主的一曲動人的戀愛和神奇冒險的故事,并在接下來衍生出劇情,制作了續(xù)集《賈方復(fù)仇記》(1994)與《阿拉丁和大盜之王》(1996),這一系列作品帶有顯著的東方文化的瑰麗特質(zhì):神秘的色彩、奇異的旅程、豐富的幻想。
在生機勃勃的改編歷程中,美國動畫人對經(jīng)典民族故事的掌控更趨成熟,不但對原作進行刪改、節(jié)選和擴寫,更在此基礎(chǔ)上嘗試移植、縮寫和詮釋,如根據(jù)法國文豪雨果的名著《巴黎圣母院》改編的動畫電影《鐘樓怪人》(1996),將原著中的現(xiàn)實美丑對立深化為人性的掙扎與反抗,在激烈復(fù)雜的沖突中透露出人性的善惡。“只有當(dāng)它不再是一種簡單的復(fù)制品和雜湊的混合物,不再是文學(xué)的圖解和戲劇的再現(xiàn),而是依靠自己的材料、運用自己的手段,創(chuàng)造出唯它獨有的藝術(shù)形象、具有自己的獨特的審美價值時,才能享有第七種藝術(shù)的獨特的光榮。”[2]由于時代投影、社會影響、文化教育、民族心態(tài)的差異,美國動畫人對同部作品產(chǎn)生不同的心理感受,出現(xiàn)不同的美學(xué)評價,并把它帶進改編作品之中,充分發(fā)揮創(chuàng)造性的想象力,將原著的內(nèi)容和形式做相應(yīng)的調(diào)整和改造,在影視劇作的形式基礎(chǔ)上,賦予動畫影片特有的浪漫氣息,形成新的和諧與統(tǒng)一。正如《獅子王》(1994)把莎士比亞的著名悲劇《哈姆雷特》中17世紀(jì)的丹麥王國搬演到非洲的大草原,將真實人物做了完美的角色置換,并同樣詮釋了放逐與成長的主題。
二、改編經(jīng)典:中國元素的生命力
2011年中國全國電影總票房超過人民幣130億元,比2010年的“百億”數(shù)值增長30%,至此中國成為全球第三大電影市場。但票房前三、過人民幣4億元的卻都是美國引進大片,更值得一提的是:排名第二位的是部動畫電影——《功夫熊貓2》,相對只有千萬票房的國產(chǎn)動畫電影,其中的距離不得不令人感嘆和深思。
中華文明源遠(yuǎn)流長,其悠久的繪畫、剪紙、皮影、年畫等中國藝術(shù)元素與動畫完美結(jié)合,成就了自20世紀(jì)60年代以來,獨具中國民族風(fēng)格的水墨動畫:《小蝌蚪找媽媽》(1961)、《牧笛》(1963)、《鹿鈴》(1982)、《鷸蚌相爭》(1983)和《山水情》(1988)等作品。它們多次在國際權(quán)威動畫電影節(jié)斬獲大獎。作為中國藝術(shù)家創(chuàng)造的傳承中華文明的動畫藝術(shù)品種,它運用動畫拍攝的特殊處理技術(shù)把水墨畫形象和構(gòu)圖逐一拍攝下來,通過連續(xù)放映形成濃淡虛實活動的水墨畫影像。剪紙動畫吸取的是中國皮影和民間剪紙的外觀形式,色彩明快,也極具鮮明的中國藝術(shù)特色,如模擬中國工筆花鳥畫的優(yōu)美剪紙動畫作品《草人》,通過將傳統(tǒng)的民族風(fēng)格和細(xì)膩的工筆花鳥畫相融合,在表現(xiàn)手法上尋求民族動畫藝術(shù)的新拓展。而影片《鷸蚌相爭》更是匯集傳統(tǒng)的剪紙形式與中國的水墨風(fēng)格,把水墨畫的典雅柔和與剪紙的簡潔概括相融合,發(fā)展成充溢著相當(dāng)成熟民族化氣息的優(yōu)秀作品,為我國水墨動畫短片的代表之作。《鷸蚌相爭》用充滿哲思的情節(jié)、舒緩的鏡頭、動人的配樂營造出中國傳統(tǒng)水墨動畫虛實相生的意境美,讓觀眾在30分鐘的視覺流動中權(quán)衡“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故事教訓(xùn),墨韻清新優(yōu)美,洋溢詩情畫意,具有濃郁的本土審美特質(zhì)。20世紀(jì)80年代水墨動畫的最高峰《山水情》,將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精髓活靈活現(xiàn)地表達出來, “天人合一”是一種講求天人和諧的審美觀照,在人類與大自然的互動交往中尋求生命的情調(diào),這種情調(diào)在特偉先生等老一輩的動畫家們的作品中都有所呈現(xiàn)。片中筆墨淋漓的山河景象令人驚嘆,配上悠揚的樂音,把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意蘊、審美情趣渾然自成地統(tǒng)一起來。中國水墨動畫將植根于中國傳統(tǒng)水墨畫中的寄思山水、棲心林間的精神韻味,在水墨動畫中近乎完滿地展現(xiàn)出來。
不可思議的是,中華文明不但造就了經(jīng)典傳奇,更深深地影響到美國動畫產(chǎn)業(yè),這些民族審美特質(zhì)是在五千年的歷史中沉淀下來的,其雕塑、建筑、服飾乃至戲曲、民樂等都為美國動畫人提供了取之不盡的借鑒元素。在中國動畫人無緣傳統(tǒng)文化創(chuàng)新的同時,國外動畫人則在深入挖掘中國元素,逐步認(rèn)知中國文化,并延續(xù)到其動畫電影中,洶涌而來地占領(lǐng)中國的動畫市場。
美國動畫業(yè)不斷從中國文化中挖掘動畫藝術(shù)的基本命題,《花木蘭》和《功夫熊貓》就是其中典型的范例。動畫電影《花木蘭》改編自南北朝樂府民歌《木蘭辭》,由美國著名動畫公司迪士尼制作出品,以傳統(tǒng)二維動畫手段為主,結(jié)合三維創(chuàng)作技巧,演繹了中國人家喻戶曉的木蘭替父從軍故事。全片整體風(fēng)格借鑒中國畫的表現(xiàn)技法,虛實相間,工筆水墨與鏡頭散焦原理結(jié)合,達到寫意與寫實的協(xié)調(diào)平衡,如影片結(jié)尾雪崩場景。由于本片中國元素運用得當(dāng),把中國的長城、宮殿、古戰(zhàn)場、騰飛的巨龍與悠遠(yuǎn)的民俗音樂相融合,意境悠遠(yuǎn),頗富東方韻味。
2008年夢工廠制造的一只肥大的中國《功夫熊貓》,更是帶著它的棍棒喜劇式中國武功紅遍世界。其故事背景、角色造型、場景、服裝以至音樂均充滿濃郁的東方審美特質(zhì)。故事的發(fā)生地“英雄寶殿”“翡翠宮”和“太平谷”的營造,大有桂林漓江山光水色“甲天下”之韻;五大高手,虎、鶴、猴、蛇、螳螂的設(shè)計靈感來源于中國武術(shù)著名的象形拳——虎鶴雙形、猴拳、蛇拳及螳螂拳,顯然其中摻雜了中國功夫電影的類型元素,“因為他(成龍)的功夫充滿幽默感,和主題最接近。其實,成龍、李連杰、李小龍的功夫都參考了,甚至包括周星馳”。[3]而筷子、青釉瓷碗、斗笠、卷軸、搟面杖、餃子、面板、針灸、中國綢緞縫制品等服飾道具也處處彌漫著華夏風(fēng)情。全片在清新自然的畫面中展現(xiàn)武術(shù)、廟宇、街市、竹林這些視覺元素,猶如一幅幅風(fēng)格濃郁的3D中國水墨畫,描繪了獨具中國風(fēng)俗的生活畫面,讓觀眾云游了秀麗淡雅的中國山水風(fēng)景。
西奧多·萊維特(1983)曾說:“到處有中國菜、空心圓面包、鄉(xiāng)村音樂和西部音樂、比薩餅、爵士樂。全球到處遍布帶種族特征的事物,這標(biāo)志著特色品的世界化。全球化并不意味著板塊的告終。相反,它意味著這些板塊擴展到全球范圍。”[4]順著這股“中國風(fēng)”,在《功夫熊貓2》全球公映之際,青城山、麻婆豆腐、擔(dān)擔(dān)面等中國“成都元素”被大手筆移植,成都市也主動邀請好萊塢夢工動畫和續(xù)集創(chuàng)作團隊,親密接觸大熊貓,并順勢與好萊塢“結(jié)緣”,要讓全世界影迷領(lǐng)略熊貓故鄉(xiāng)的風(fēng)采,同時《功夫熊貓》美術(shù)總監(jiān)雷蒙德·茲巴到成都青城山再度采風(fēng),有消息稱續(xù)集《功夫熊貓3》里的民族視覺審美表現(xiàn)重點可能是中國漢字。
三、改編現(xiàn)狀:糾葛與困境
在美國經(jīng)典動畫電影的改編過程中,當(dāng)代流行的價值理念以及適用于改編現(xiàn)狀的主旨話語被作為鮮明的改編觀念植入動畫作品。如動畫電影《海的女兒》中有對浪漫愛情的執(zhí)著追求,《獅子王》中有親情的責(zé)任與無私,《魔法灰姑娘》中有爭取平等、自由、獨立的宣言,而更多的作品則是積淀了價值觀中的英雄崇拜與個人成就等典型話語和價值理念,這種普泛性的價值話語通過動畫電影這一大眾傳媒渠道,傳輸至各個文化區(qū)域。
作為受眾,自然也比較能夠接受符合自己價值觀念的改編動畫,同時異國民族受眾也能從這些美國動畫電影中獲得審美的歡愉,因為在與當(dāng)今全球化發(fā)展趨勢保持和諧一致的同時,任何民族都具有同感語境,都能在美國動畫電影中從容自如地期待到所觀照的民族審美需求,這些動畫電影也能在民族文化的傳承中獲得延續(xù)的商業(yè)生命力。美國動畫電影中展現(xiàn)的中國元素?zé)o一不是我們司空見慣的,表達的中國文化更是每個中國人耳熟能詳?shù)模鼈儏s貼上了非中國制造的標(biāo)簽,形成凝固的好萊塢模式。但西方人用本民族的思維方式闡釋中國元素,只能停留在文化表層上,《花木蘭》改造成充滿西方文化精神的具有強烈的個體意識的花木蘭,甚至是當(dāng)代女性主義味道的花木蘭,其制作過程中,中西文化差異凸顯,如美國人不理解祠堂里老祖宗的性別之分,他們的魂魄手持如意還是拐杖;認(rèn)為開滿木蘭花的場景應(yīng)該替換成日本櫻花樹等。
另外,就觀者對經(jīng)典的民族審美特質(zhì)而言,改編則更面臨著記憶經(jīng)驗的權(quán)力重負(fù)。改編經(jīng)典,顯然意味著強行對個體記憶、情感做一定程度的修正,美國的動畫電影“正是通過自己獨特的藝術(shù)視角和語言,在具體的創(chuàng)作中,抽象、描述和重構(gòu)現(xiàn)存的、過去的或理想的社會形式,通過這些社會形式,人們變得有意識并且主觀地維持自我的存在”。[5]形成這個逼仄局面的原因在于,主創(chuàng)人員都帶有明顯的“外來者”身份,西方民族心理多年的沉淀,使他們無意識中用本民族的視覺、心理去感受和體驗中華文明,以本民族的思維模式、價值取向去解讀中國人的行為方式與生活習(xí)慣,對宗教儀式的心理深處、文化內(nèi)蘊并不能真正予以闡述,相反,只是作為一種象征符號,忽略了中華民族在一系列形式表象下始終保持住的、自身的價值選擇及感情體驗。
就總體而言,美國人認(rèn)為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有較強的吸引力和較鮮明的審美特質(zhì),容易捕捉和造型,并能創(chuàng)造較高的票房價值,而夢工廠的《功夫熊貓2》也驗證了這一預(yù)言。但正是這種跨文化身份造成那些中國元素動畫電影的深層靈魂依然是西式的,正如施萊格爾所說“每個人都在古代人那里找到了他們所需要的或所希冀的,但首先是找到了他自己”。[6]即使選用華人動畫設(shè)計師張振益造型花木蘭,雷蒙德·茲巴用8年時間鉆研中國文化、藝術(shù)、建筑,但多年西方文化的熏陶固定著他們的身份,“他自己被民族精神完全滲透了”(歌德語),任何“外來者”的血管里都無法涌動他民族的血液。
本雅明曾說,每種藝術(shù)形式和審美價值都有其獨特的歷史土壤。我們目前的任務(wù)是在數(shù)字技術(shù)時代的土壤中,發(fā)展出與之相對的具有豐富內(nèi)涵的人文精神和積極的藝術(shù)審美方向,使其適應(yīng)受眾的需要和人類的發(fā)展,達到“心物互滲”。[7]美國動畫電影在改編經(jīng)典故事,吸收他國民族審美特質(zhì)的道路上雖然糾葛與困境重重,但依然漸行漸順。在美國引進大片的重重強壓下,國產(chǎn)動畫電影長期以來面臨尷尬的境地,可幸的是,近年還是存在些許異軍突起的火花,如2012年新春前夕,上影集團重新激活的3D版動畫電影《大鬧天宮》也給觀眾帶來了不少驚喜;2014年春節(jié)檔上映的電影版《熊出沒之奪寶熊兵》取得了中國動畫電影票房不俗的成績,2.47億元;2015年上映的國產(chǎn)動畫電影《大圣歸來》也頗受好評;2016年7月,歷時12年、久經(jīng)打磨的動畫電影《大魚·海棠》重裝上映,短短兩日票房便破億元,創(chuàng)造國產(chǎn)動畫電影票房新高,縱觀全片無論是角色創(chuàng)作、人物造型、服裝服飾再造還是建筑樣式設(shè)計、場景造型美術(shù)風(fēng)格設(shè)定,都無一例外地呈現(xiàn)出中國傳統(tǒng)文化元素的獨特韻味,恰到好處地深度融合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可以說,他們在夾縫中另辟蹊徑,希冀用原創(chuàng)風(fēng)格和民族元素?fù)荛_長期以來籠罩的市場迷霧,通過進一步挖掘和結(jié)合傳統(tǒng)文化走出一條適合本民族的動漫品牌路線。從美國獨具民族審美特質(zhì)的動畫電影來尋求重拍或改編的魅力,或許對國產(chǎn)動畫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愿以此為契機,讓國產(chǎn)動畫經(jīng)典浴火“重生”,再創(chuàng)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