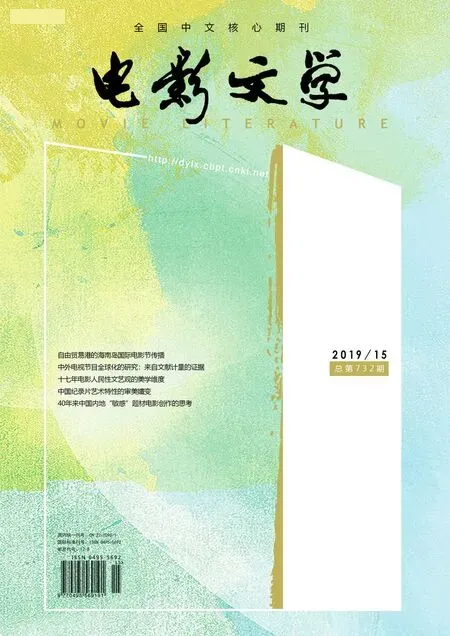十七年電影人民性文藝觀的美學維度
毛凌云(婁底職業技術學院 文化傳播學院,湖南 婁底 417000)
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文藝思想給文藝界帶來了新的美學視界,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明確提出了“文藝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人民性文藝觀,為新中國重構文藝美學話語體系和審美價值體系提供了重要指導思想。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電影(1949—1966)創作,嚴格遵循社會主義文藝思想,全面實踐“人民性”文藝觀,積極構建新的電影美學范式,“總共制作出了影片757部”,[1]代表作有《在前進的道路上》《英雄兒女》《白毛女》《平原游擊隊》《青春之歌》等。這一時期,電影人探索了時政、工業、農村、軍事、反特、歷史等各類題材的創作,構建“求真”“向善”“至美”“追愛”“逐夢”的影視美學空間,滿足新時代人們的審美需求,并引領人民投身于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對“建立起一種民族國家認同的政治共同體”[2]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以新生啟蒙為精神的求真
新中國成立初期,廣大勞苦大眾翻身當家做主,內心無比喜悅與激動,從個體到國家都希望“新生”的社會主義與舊社會徹底決裂,建立一個沒有壓迫與剝削的理想的社會主義國家,期待這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有著迥異于舊社會的價值體系與審美標準。正是因為廣大勞動人民十分珍惜“新生”的不易與寶貴,整個民族都在反思總結中國革命成功的經驗,普遍認為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關鍵在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以人民利益至上。這種以人民為中心的新社會,是一種求真的美學精神,凡事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人民的實際情況出發。求真的社會主義價值體系如何在新社會迅速得到全面認同,在文藝界顯得尤為迫切。
新社會需要的不是人民在舊社會的被迫服從,需要的是人民在實踐中積極探索和尋找社會發展規律。法國啟蒙思想家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指出:“如果人民單純是諾諾地服從,那么,人民本身就會由于這一行為而解體,從而喪失人民的品質。”[3]在封建舊社會,特權與壓迫鉗制著人民的思想與主張,人民被迫遵循特權階級的社會規范而茍且生存,也被迫按照特權階層倡導的審美標準而甄別社會是非,甚至被迫按照舊社會倡導的是非標準而矯正自己的審美認識。只能諾諾地服從,而不能有人民自己的審美“求真”。新中國的成立,壓抑已久的人性得到了徹底的釋放,人民的思想與主張可以自由平等地交流,每一個個體都極力想把自己的想法與觀點表達出來,不管是正確的,還是狹隘的,新生后的“求真”啟蒙意識迅速覺醒,人人都想表達,人人都期望自己當家做主之后的審美表達準確并被他人認同接受,自主審美意識隨著新生政權的建立而全面迸發,整個社會亟須用“求真”的審美觀引導人民的價值判斷。
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電影順應時代發展的要求,“電影人將人民大眾的現實生活搬進銀幕,用貼近人民審美習慣的表現方式,塑造了一批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銀幕形象”[4]。這一時期的電影塑造了一大批真實可感的具有新生啟蒙意識的典型人物,將典型人物的抗爭、控訴及新生啟蒙思想表達得淋漓盡致。謝鐵驪執導的《早春二月》中的女性形象陶嵐,深受五四新思想影響,勇敢示愛,其渴求個性解放的思想正是新中國成立后廣大婦女思想啟蒙的審美主張,對解放后女性沖破封建枷鎖去自主追求愛情與幸福,具有重要的引領作用。崔嵬、陳懷皚執導的《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靜,通過其成長的歷程詮釋“一個人只有投身到集體的斗爭中,只有把個人的命運和人民的命運結合在一起,這才能夠找到真正的出路”的思想,用電影形象與電影故事進行敘事,引領解放后的廣大人民將個人命運與社會主義建設結合起來,為人民新生啟蒙思想指明了方向。影片《思想問題》直面知識分子心靈,經過革命大熔爐的改造,一群背著沉重思想負擔的知識分子開始樹立起了革命的人生觀,面對新生的社會找到了方向,思想問題也因實事求是的審美價值取向而發生變化,變成了具有新思想覺悟的社會主義新人。
十七年電影通過電影敘事與電影人物形象的生動表達,充分體現了“求真”的啟蒙思想,為新時代建立起新的文藝美學規范起到了很好的推動作用。
二、以中國典范為風貌的向善
從飽經戰爭摧殘的歷史中走向新社會的廣大勞苦民眾,對嶄新而又陌生的新中國充滿無限的熱愛與期待,源自內心深處的摯愛之情溢于言表。由于新中國未來風貌的難以描摹與想象,中華民族幾千年來形成的具有獨特民族風貌特征的向善品格,便成了人們對新社會的審美期待或憧憬,他們憑自己的經驗分辨著善惡與好壞,急切地在內心深處構建著與舊社會虛偽、欺騙、壓迫迥異的向善審美觀。這種與新社會人民至上相匹配的美學精神,正是中華傳統美學的精髓,如何促進這種傳統向善審美價值觀迅速在新社會傳播發展,文藝美學顯然必須先行引導教化。
中國傳統向善美學品格是歷經幾千年中華民族文化淬煉而成的,源遠流長,在漫長的封建歷史演繹中形成了“仁義禮智信”及“溫良恭儉讓”的道德準則與傳統美德,人們遵循著傳統的道德準則與美德標準繁衍生息,也正是這種傳統美德形成了向善的人生哲學思想。《孟子·公孫丑上》中說:“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與人為善的社會品格讓老百姓形成了重義守信、吃苦耐勞、勤勞勇敢、忍辱負重、善良純樸的性格。新中國盡管建立了與封建社會截然不同的社會制度,但仍然無法一下子與幾千年來形成的社會文化品格斷然決裂。新中國成立之初,新舊思想激烈碰撞交鋒,封建守舊思想與進步新思想以各種形式爭辯沖突,甚至是陣地爭奪。用傳統典范的向善品格穩定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復雜局面,凝聚人心,是當時比較恰當的審美價值方向。
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電影積極構建適應新形勢發展要求的電影美學話語體系,用中國傳統的向善品格教育廣大人民大眾傳承傳統的優秀品質,尤其是對人性善的弘揚與倡導。“電影往往通過道德倫理化、親情化、目的化(善惡有報)等手段來影響公民的政治情緒和政治情感。”[5]影片《白毛女》控訴了黃世仁的殘暴,黃世仁受到群眾公審并被判處死刑,講述善惡有報的道德主題。影片《暴風驟雨》則通過田大爺和田大嬸對惡霸地主韓老六的控訴和人民政府對韓老六的依法懲辦,電影用公審儀式強化善惡有報的視覺沖擊感,用黃世仁、韓老六等為非作歹典型受到懲辦的下場教育人民向善。影片《洪湖赤衛隊》用電影視角敘述洪湖赤衛隊和革命群眾在同敵人斗爭中的大善品格,偷襲失敗的敵人惱羞成怒,威脅老百姓講出赤衛隊下落的時候,洪湖地區的革命群眾臨危不懼,誓死不屈,他們用集體的善良詮釋著正義的力量,以及革命群眾向善的本性。
十七年電影中的人物形象,用他們自己獨特的方式講述、詮釋、演繹著中華傳統文化的精髓——上善若水。電影人將善良的品格融入革命抗爭、新生奮爭的宏大敘事主題之中,引領新生社會制度下的人民傳承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品質,以積淀了幾千年中華民族文化智慧的向善品格,構建新時期文藝美學的審美導向,指引人們弘揚傳統向善的美學思想。
三、以英雄樂觀為基調的至美
新中國成立初期,經歷14年抗戰和三年解放戰爭洗禮后,人們面對的是滿目瘡痍、千瘡百孔的國家現狀,在這樣的基礎上建設新中國,意味著一場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改造與建設新的人民戰爭正在等著他們。飽經戰爭創傷的人民,身心俱疲,盡管建立了人民自己當家做主的新中國,但喜悅與激動過后的社會主義建設重任,根本不遜色于抗戰的艱難。歷史經驗證明,正是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形成的英雄樂觀主義精神,指引人們不斷抗爭,以人民的力量推進著歷史的車輪前進。這種至美的英雄樂觀主義精神,是長期以來形成的美學精神。繼續發揚抗戰與解放戰爭期間的英雄氣概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是打贏社會主義建設新戰爭的必然要求與不二選擇。新社會如何讓這種英雄樂觀主義的美學精神深入人心,形成建設社會主義的合力,正是文藝界十分關注的美學問題。
黑格爾曾說:“我們應當把世界歷史人物——一個時代的英雄——認作是這個時代眼光犀利的人物;他們的行動、他們的言辭都是這個時代最卓越的行動、言辭。”[6]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一個滿負英雄氣概的偉大國家,一代代英雄用他們的行動與言辭引領著民族不斷發展進步。中華民族之所以長盛不衰,是因為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崇尚英雄,且英雄輩出,是一代代英雄用智慧甚至生命推進中華民族沿著歷史發展潮流前進。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9周年座談會上指出:“近代以來,一切為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而犧牲的人們,一切為中華民族擺脫外來殖民統治和侵略而英勇斗爭的人們,一切為中華民族掌握自己命運、開創國家發展新路的人們,都是民族英雄,都是國家榮光。”[7]新中國成立之初,在中華民族獨立與解放戰爭中形成的革命英雄氣概和革命樂觀主義精神,仍然流淌在每一個華夏兒女的心中,為中華民族獨立和解放而犧牲的英雄形象仍歷歷在目,銘記在人民的記憶深處。在戰爭中形成的不怕艱難險阻、不懼任何苦難的英雄樂觀主義精神,正是推進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所需要的一種精神。
周揚在《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中提出:“目前文藝創作上頭等重要的任務”是“我們的文藝作品必須表現出新的人民的新的品質,表現共產黨員的英雄形象,以他們的英雄事跡和模范行為,來教育廣大群眾和青年”。[8]新中國成立后十七年電影遵循人民性文藝觀,積極構建英雄形象及樂觀向上的電影人物形象,以達到鼓舞與教育新社會廣大民眾的目的。影片《平原游擊隊》中的游擊隊長李向陽,是一個神出鬼沒、足智多謀的抗戰英雄形象,電影視角將李向陽的英雄神話般的力量與樂觀精神展現得淋漓盡致。影片《董存瑞》中的董存瑞手舉炸藥包炸掉碉堡,高喊:“為了新中國,前進!”其大無畏的革命犧牲精神令人敬佩,永遠活在人們的記憶中。影片《南征北戰》更是以敵強我弱的形勢取得了完全勝利,這種敢于大踏步前進,無所畏懼的英雄氣概,正是中國革命戰爭戰無不勝的精神魅力,也是新中國成立初期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所需要的精神品質。
十七年電影以革命英雄樂觀主義精神為電影表現的重要主題,通過系列戰爭題材敘述抗戰與解放戰爭中人民英雄的故事,在這個苦難深重的特殊歷史時期,人們用自己的壯舉和負重的身軀詮釋拓展英雄的內涵與外延。這一時期影片所展現的英雄氣概和樂觀進取精神,為“不愛紅裝愛武裝”的時代審美價值取向做了最好的注解,也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時代審美追求的最強音符。
四、以崇高情感為導向的追愛
新生政權建立后,受封建禮教思想束縛了幾千年的包辦婚姻思想被徹底摒棄,人們自主追求愛情婚姻的思想在年輕人中迅速擴散傳播。剛從戰火中走過來的人們,面對自由戀愛卻一時不知所措,既有對自主追愛權利的激動,也有對浪漫愛情的羞澀與懵懂,特別是沒有經歷五四新思想洗禮的農村青年女性,她們的內心是十分掙扎的,既依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傳統規矩,又向往“自由自在、不受羈絆”的自主追愛,由于沒有既成的愛情價值審美標準遵循,或者是習慣于傳統婚姻觀的省心的生活,獲得自主追愛權利的年輕人倒顯現出幾許焦慮。匈牙利詩人裴多菲的《自由與愛情》詩歌寫道:“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種富有崇高情感的愛情觀是在爭取民族自由與獨立的特殊歷史背景中產生的,也是抗戰與解放戰爭時期人們對于愛情的一種崇高詮釋。新社會如何引導人們傳承這種崇高的愛情價值取向,以人民為中心的文藝觀促使文藝界關注愛情審美范疇。
恩格斯指出,愛情是“人們彼此間以相互欽慕為基礎的關系”。[9]馬克思恩格斯的愛情價值觀將女性擺在與男性平等的位置,是彼此欽慕的愛情,也徹底改變封建社會女性的從屬地位。社會主義新生政權建立后,徹底摧毀了壓在人們頭上的三座大山,婦女完全得到解放獨立,理應享有平等的追求愛情的權利。在激烈的抗戰與解放戰爭時期,人們將全部的熱情與精力投身于民族救亡與民族解放事業之中,將自己的性命與愛情全部交付給了戰爭。戰爭勝利后,人們對于人類美好愛情的追求,既是人的本能需求,更是健康社會形態的審美追求。
十七年電影貼近人們追愛的迫切情懷,考慮到當時愛情審美價值標準的模糊與不確定性,電影人從顛覆傳統包辦婚姻的視角重構愛情審美價值體系,將愛情置于特殊的革命歷史敘事之中,愛情與革命絞合在一起,用戰爭勝利后的相逢詮釋“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的經典愛情觀。影片《柳堡的故事》講述抗戰時期新四軍副班長李進與二妹子的純潔愛情故事,電影用“相識—相戀—相離—相逢”的情節線索細膩地展現了革命戰士追愛的情感。影片《蘆笙戀歌》則通過一首主題歌曲《婚誓》講述拉祜族少數民族戀人真摯甜蜜的情感,揭示穩定強大的新中國對于老百姓安居樂業、追求愛情的重要性。根據趙樹理小說《三里灣》改編的影片《花好月圓》,講述農村青年靈芝和有翼分別實現自由婚姻的故事,表現新社會進步的婚姻愛情觀,將傳統的門當戶對的封建婚姻價值觀徹底擊了個粉碎。
十七年電影站在人性解放的時代立場,直視新中國成立初期青年男女愛情審美價值重構的歷史語境,電影人用電影形象構建當時具有反封建意識和自由戀愛的進步愛情審美價值取向,引領人們追求自由幸福的愛情,充實人民性文藝美學內涵。
五、以重建家國為激情的逐夢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面對千瘡百孔的爛攤子以及國際敵對勢力的封鎖,依靠人民群眾力量鞏固政權、建設國家,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當務之急。國家通過實施土地改革,徹底廢除了延續兩千多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真正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為鞏固和發展這種新的社會生產關系,需要不斷激發人們重建家國的熱情和夢想。
弗洛伊德在《夢的解析》中指出:“夢是本我被壓抑的力量與超我的壓抑力量之間的一種調和和妥協。”[10]夢想則是一種信仰與追求,是推進個體積極奮爭的力量源泉。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有夢想,有追求,有奮斗,一切都有可能。”新中國成立初期,重建家國的遠大理想和建設實踐中的重重困難,導致人們在建設實踐中產生出新的矛盾和焦慮。當理想信念超越焦慮時,人們便能積聚力量戰勝一切困難,取得重建家國的勝利。因此,在新中國成立初期,打消廣大民眾顧慮,堅定重建家國的必勝信念,是凝聚力量,推進社會主義改造與建設的關鍵。
十七年電影為解決當時的這種思想焦慮,電影人主動聚焦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的新人新事及新矛盾,用電影形象與故事幫助廣大百姓化解心中困惑,堅定必勝的信心,點燃重建家國的激情與夢想。這一時期涌現出了《光芒萬丈》《高歌猛進》《江山多嬌》《花好月圓》等一系列典型性影片。影片《光芒萬丈》通過記述周明英克服困難、決不氣餒的精神修復好發電機的故事,說明在新中國只要團結群眾,積極工作,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影片《江山多嬌》通過記錄青年突擊隊長岳仙動員群眾把荒山變成花果山的治山典型事跡,闡述新社會完全可以改變山區落后面貌,建設美好家園。
十七年電影通過新中國建設的典型事跡的生動展示,充分展現人們逐夢的源動力以及建設新中國的巨大熱情,也充分體現了人們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期待與夢想,為新時代文藝美學范圍拓寬了新視野。
總之,十七年電影以“文藝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人民性文藝觀為創作引領,進行多元探索,全面構建新中國電影美學體系,成為新中國電影藝術的一個高峰,其美學追求將對中國電影藝術產生深遠而持久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