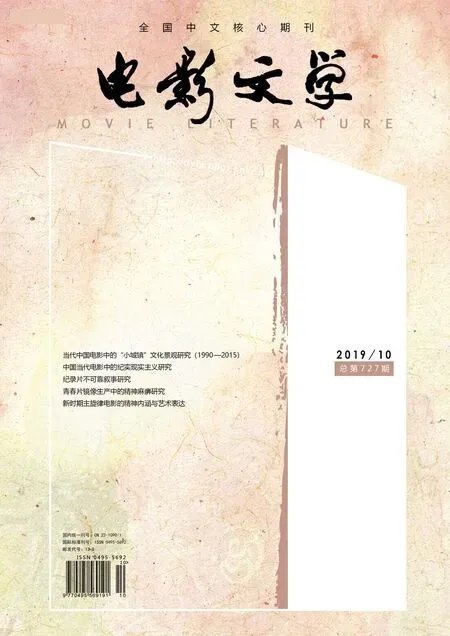中國當代電影中的紀實現實主義研究
林軒石 (長春工業大學 信息傳播工程學院,吉林 長春 130000)
中國的現實主義電影最早出現于1913年的《難夫難妻》,從誕生之初就深入到社會歷史發展的重要階段,站在不同的角度透析社會現實等若干生活問題[1]。紀實現實主義一貫要求采用質樸無華的電影語言,將鏡頭底下真實存在的現實世界展現給觀眾,完成對客觀世界的復制和再現,從而揭示影像作品對社會話語體系的本質需求。從新中國發展至今,隨著社會文化的變遷,也相應地調整了中國現實主義電影在不同階段的表現形式與精神內核,但仍舊實現了電影創作者與影像觀賞者的共謀。對中國當代電影的紀實現實主義思想進行深入研究,除了能夠了解影像文本獨特的創作范式和敘述技巧,更能夠與特定的時代背景緊密相連,從歷時性的角度分析電影作品的開拓與嬗變,為新世紀國產電影的文化軌跡和傳播方向找到新的突破點。現實主義美學作為新中國電影歷史的參與者,其高度凝練的紀實主義風格以及厚重強烈的現實主義氣息,更是緊緊抓住電影觀賞者的好奇心和注意力,從中找到具有共情色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也標志著現實主義美學正作為中國當代電影創作的強大驅動力,推動了中國電影市場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對新中國當代電影的現實主義美學進行研究,更有其合理性的社會價值。
一、高度凝練的紀實主義風格
正如著名的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所言:“電影存在的重要價值,在于它對客觀現實世界的復制和再現,將原本充滿神秘色彩的社會萬象以影像語言的形式反饋出來,從而完成了對電影本體論的研究。”[2]在這一過程中,電影語言借助紀實主義的影像風格,拉近了虛擬空間和社會現實之間的深刻聯系,將原有的生活現象以一種高度凝練化的鏡頭表現方式凸顯出來,使之成為具有獨特魅力的現實主義美學。總體而言,中國當代電影的完整性和真實性,集中體現了人類對理想中的現實世界進行藝術化加工之后的不同形式呈現,以嚴謹、客觀的創作態度來結構作品,同時又借助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想象,超越了人們對現實層面的認知空間。只有從話語文本的真實性表達以及社會現實的客觀化再現來了解作品,才能夠真正懂得現實主義電影一以貫之的創作原則,進一步挖掘影像語言背后的文化屬性與價值內涵。
(一)影像語言的真實性表達
中國當代電影中的現實主義作品,既致力于關照現實文化環境,又表現出特有的人文主義關懷,并采用紀實性主義的美學元素來凸顯作品立意,使其具備獨樹一幟的文化底蘊和藝術氣質。紀實主義風格的電影著重突出紀實性的美學特征,強調用客觀、真實的鏡頭語言還原生活的本質,以嚴謹的紀實風格表現出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因此在研究中國當代現實主義電影時,需要對其外在風格的影像表露進行重點分析。紀實性作品注重拍攝技巧的復義性和完整性,對處于同一時空中的故事情境,較多采用長鏡頭以及深焦距鏡頭進行影像風格的處理,打破了原有蒙太奇藝術一以貫之的藝術表現形式。同時現實主義題材的影片,在突出強調“紀實性”色彩的過程中,尤其尋求影像語言的真實性表達,既包括外部拍攝過程不添加任何雜質,又需要保證電影觀賞者心理層面的真實,可通過對電影作品的主觀印象自發地判斷以及了解事物。從電影出現至今,紀實美學就在現實主義題材風格的電影中占據了半壁江山,其別具一格的真實性影像表達更是彰顯了電影作品的藝術生命力和創造力。
對典型環境的真實再現,離不開細節行為的真實刻畫。正如恩格斯所表露的那樣:現實主義作品的典型環境描寫,實際上也是對細節問題的詳盡記錄,注重環境和角色的有機統一,正是通過紀實美學中對細節的深度刻畫得以展現出來。現實主義電影注重對物質細節的再現,電影作品通過細節呈現來尋求典型人物在典型環境中的心理認知狀態,從瞬間展露的物質生活中找到現實與虛擬空間中的內在共通感[3]。因此,觀影者往往將更多注意力放置到不為人知的細節生活中,根據真實且碎片化的生活細節來推進故事情節的發展,深入到超越現實主義之外的潛意識領域。對于當代中國現實主義影片而言,其高度凝練的影像風格和真實性的細節描繪已經成為極為重要的美學特征。電影創作者在創造電影作品的過程中,往往通過質樸真切的敘事元素來反映人們司空見慣的人或事物,強化鏡頭語言的表意功能,對現實社會的具體面貌進行全方位揭示,因而細節捕捉則成為影像表意的慣用手段。例如影片《親愛的》《失孤》等都改編自真實的社會事件,影片在拍攝過程中嚴格按照紀實性美學技巧來展現真實存在的社會現實。《親愛的》對于影片細節的深入描寫,更是將底層人物被生活折磨卻又負重前行的狀態表現得淋漓盡致。電影中隨處可見的陰暗小巷、略顯陳舊的家庭擺設、交織錯落的電網等,都利用長鏡頭的緩緩記錄,讓同一敘事空間中不同人物的情緒狀態、不同環境的生存面貌都全方位顯露出來。這種客觀鏡頭的敘事效果,除了增強影片的理性思考,寄托電影創作者的敘事表達要求,更能夠及時抓住細節的多面性,具有審美價值的必然優勢。
紀實主義所熔鑄的影像語言,實現了影像思維的客觀化表達。影片在忠于現實的基礎上,采取個性化的藝術加工和人物塑造展開情節描述,輔之運用鏡頭和場面調度等不同的語言技巧,通過人物的悲歡離合來展現現實環境的基本特征,并以最為真實的人情冷暖來調動電影欣賞者的內在情緒,強調客觀世界的主觀感受。巴贊對影像語言真實性的研究,聚焦于客體影像對于主觀意識的再現需求,唯有攝影機鏡頭拍下的客體影像能夠滿足我們潛意識提出的再現原物的需要,觀眾能夠體驗到影片背后所營造的身臨其境之感,內心情緒也會伴隨情節出現相應程度的變化,從而感受到紀實美學帶來的強烈震撼力。中國當代電影中的紀實美學,在承襲巴贊紀實主義思想的基礎上,將故事斷拍為現實生活的原始記錄事件,提升作品的可信度和真實性,并用影像的形式對其進行直觀化處理。值得注意的是,影像作品的真實性并非等同于客觀的現實,作為已被中介化的存在,使之重新建構起影片、創作者、欣賞者之間的內部聯系。
(二)社會現實的客觀化再現
對物質世界的客觀化再現是電影作品的本質和初衷,并透過可視化的視覺效果向內探索到人類的精神世界,從而拉近主觀與客觀的深入聯系。因此,影視作品創作的基礎在于對社會現實的完整復原,并以此為前提上升到紀實美學的重要范疇。現實主義電影中所蘊含的紀實性美學元素,致力于冷靜地記錄普羅大眾的生存狀態,再準確地將其藝術理念全面展露出來。對紀實現實主義電影而言,“真實性”和“客觀化”是其基本的敘事特征,但又與傳統的現實主義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紀實現實主義電影更加側重于對客觀物質世界的整體性描述,盡可能地還原現實生活的原始生存狀態,從而創作出具有強烈現實主義生命意蘊的影像作品。紀實現實主義電影聚焦現實生活的若干層面,對社會既有的矛盾和沖突進行挖掘和揭露,探討人性善與惡的永恒話題,并用嚴謹的紀實影像風格還原社會群眾集中面臨的處境,個人化的生活體驗也得以借助影像魅力施展開來,更容易引發電影觀賞者情緒和生理的雙重共鳴。
紀實現實主義電影一貫致力于展露生活的本來面貌,秉持著“從現實中來,到現實中去”的創作理念,構建出具有現代意識和社會風貌的經典影視作品,并透過電影故事情節分析影像背后所要傳遞的深刻理念,使外在的視覺元素同內在的精神內涵進行巧妙的對接,讓電影作品具有較高的人道主義精神。中國當代電影在強調現實主義元素的過程中,除了利用紀實性視覺刻畫全面呈現個體所面臨的生存狀態,保留了電影的戲劇化創作思維,同時亦注重影像文本的真實性和客觀化表達,任何影像文本在處理過程中都紛紛強調的是對生活本來面貌的記錄和再現,使影像作品的虛擬化和真實性融合在一起,在獲得信息的同時也贏得了共情。例如聚焦兒童性侵事件的現實主義影片《嘉年華》,電影從不同的人物立場出發對女主人公作為受害者的人物形象進行探討,更多是從社會罪惡的一面來顯露人性,引起社會對于女性兒童弱勢群體的關注;《我不是藥神》一經上映就獲得了票房與口碑的雙重贊賞,這部電影直面人民群眾生活的苦難,并從“藥價”入手去關注中國當前的醫患關系以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問題,并引起了中國政府的高度重視。這兩部電影都是從不同的層面來還原中國當前社會所面臨的生存危機,其中也穿插了眾多紀實主義的創作原則,用一個簡單的故事來結構影像作品,并賦予了電影文本厚重的社會價值。
現實主義的歷史性要求在創作影像作品的過程中,必須要以復雜且真實的社會關系作為描摹對象,同時需要反映出社會變革和發展過程中所體現的矛盾運動,從而完成對社會現實的客觀化再現。這也意味著中國的紀實現實主義電影,必須要建立在社會結構以及社會經驗的基礎上進行創作。對社會現實了解得越深刻,越容易從主題和事件的相互關系中了解矛盾沖突,影像作品的客觀性也會越發明顯。總體而言,高度凝練的紀實主義風格除了具備藝術形式的真實性之外,更應該注重事件的客觀性及其可記錄性。電影不僅能夠作為影像語言描摹過去和未來,更應該了解現實、記錄現實,以此創作更多膾炙人口的影像作品。中國的紀實現實主義電影發展任重而道遠,創作者在不斷拓寬自身視野范圍的同時,也需要創造出更多充滿人情味和人性化的作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使之從一般性的劇情故事上升到整體價值觀和現實問題的冷靜思索,解析中國社會存在的多面性。
二、厚重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
現實主義既是一種具有獨特邏輯和文化架構的美學思想,同時亦是對現有社會體制和生存狀態綜合凝練而成的世界觀。一方面,它建立在原有道德倫理教育的基礎之上,現實主義電影更多是通過不合時宜的倫理情愫,來側面展現普通人所共有的倫理道德意識和社會文化心理;另一方面,它必須承襲著時代發展的重要步伐,積極迎合主流文化價值取向,在對當前客觀事實的基礎把握之上,創作出具有審美情趣的重要故事情節,從而完成對主流價值文化的滲透與表達。能夠發現、聚焦微觀敘事的社會倫理電影以及側重宏大敘事的主旋律電影作品,均不僅局限于簡單的影像語言,更是在獨具風格的藝術創新中凸顯人物的本性、找到事實的真相。因此,對中國當代電影中的紀實現實主義美學進行研究,更需要聚焦電影作品背后所體現出來的現實主義精神,拓寬影響文本分析的深度和范圍,從外在的視聽語言深入到作品精神的內核,找到戲劇作品與社會現實之間的巨大聯系,更能夠了解現實主義美學的特殊蘊含。
(一)深刻的社會倫理觀念
現實主義電影一貫注重深刻的社會倫理觀念,但從其文化理念的表露上則重點呈現出兩個部分的重要內容:其一在于重點突出家庭倫理或政治倫理道德觀念,其二在于積極傳遞自由倫理的道德思想。在創作有關家庭倫理電影作品時,往往是通過父母與子女之間的代際溝通,來展現時代發展過程中新老一輩面臨的不同人生際遇。例如李安導演的《飲食男女》,作為典型的現實主義題材作品,就側重于從一個家庭的生活環境來透視不同文化背景下所產生的思維碰撞,也巧妙地融入了東西方獨特的文化差異理念。整部電影讓家庭倫理關系和烹飪題材作品進行有效銜接,以全新的視角來展現普通家庭所面臨的情感困境,讓影片的敘事風格更具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
家庭倫理影片在中國當代電影中占據了半壁江山,但須注意的是,新現實主義電影所強調的個體自由敘事同時也得到了較好的發展。尤其是中國第六代導演,更是將自由倫理精神與時代背景緊密相連,用獨特的敘事手法來講述邊緣人物的真實際遇和道德困境,使電影觀賞者在極富道德感的狀態下去感悟影視作品中想要突出強調的倫理道德觀念,并根據既有的文化體系形成對于影片的主動性認知[4]。中國的第六代導演一貫追求極致的影像本體,并以草根群眾或邊緣人物作為影視創作的重要主體對象,在人物的悲歡離合中融入自我的生存經歷,用影像為媒介關注年青一代群體在時代發展的浪潮中所產生的迷惘惶惑之感,形成了極富特色的紀實影像風格。賈樟柯作為第六代導演中的代表人物,其執導的無論是《江湖兒女》還是早期上映的《站臺》《小武》《任逍遙》,均是典型的紀實現實主義影像作品。他將中國底層邊緣人物的真實寫照和自身的生存境遇巧妙地結合在一起,讓更多電影受眾來關注這個被時代裹挾著卻又拋卻在外的特殊人群,并采用平民化的敘述視角展現弱勢群體的生存狀態,以發自肺腑的悲憫情懷來凝視社會關系變遷給人民群眾造成的深切影響,也架構了電影創作者對于自由倫理的經典敘事表達,這種形而下的個體敘事方式更側重于展現深刻的社會倫理意識,將現有的社會發展與個體際遇相結合,使電影超脫了感性意識的層面,更具有理性主義色彩。
(二)典型的時代精神風貌
國家政策的強力推動讓中國的電影文化一路高歌猛進,創作出具有不同風格元素的類型電影,也為中國當代電影的發展提供了眾多可供參考的路徑[5]。現如今,新時期電影的發展趨勢側重于建構起影像和觀眾之間的深刻聯系,對于紀實現實主義電影而言,更需要從群眾的角度出發,創作出具有典型時代精神風貌的影像作品。由于當前中國電影觀眾的精神文化需求越發顯著,對影像文本的質量和內核有所要求,特別是對紀實現實主義電影而言,更需要創造出反映民間疾苦、展現世間溫情的類型作品,積極強調主旋律的時代精神,了解觀眾潛意識領域的不同訴求,實現作品與觀眾的雙向互動,用現實主義精神來溝通情感,以合理化的敘事展現風貌,才能夠不斷創作出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影視作品。
中國的主旋律電影較多地繼承了現實主義影像風格的敘事手段,采用藝術化的創作方式承載了社會的主流集體意識,創作出具有典型性格和典型行動的人民英雄形象,積極響應時代的號召,也讓現實主義電影作品上升到更高的精神文化領域,吸引了眾多電影觀賞者的注意。例如2017年上映的現象級電影作品《戰狼2》,就是將現實主義與主流價值觀進行了完美的融合,使英雄人物表現出特有的時代精神風貌,也推動了中國電影邁向國際化的發展歷程。作品中關于英雄冷鋒的形象塑造,既反映了中國日益強大的國際性戰略地位,也表現出中國影視藝術想要追趕乃至超越國際電影作品的風骨和氣概;《十八洞村》同樣屬于主旋律電影作品,該片聚焦國家重大工程,以精準扶貧為重要主題來展現農村人物的生存命運,又融合了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讓主流影像作品迸發出更具活力的光彩。
三、結 語
從改革開放發展至今,中國的當代電影也曾創作出不同類型的影像文本。但值得注意的是,現實主義既作為一種獨特的戲劇美學形式被濃縮在電影作品中,又憑借其典型的人文主義取向和家國主義情懷得以上升到價值觀的重要范疇,對中國電影藝術的創新和發展起到了相當重要的影響,同時也形塑了現實主義題材影片的審美價值與道德觀念[6]。深入研究中國當代紀實現實主義題材風格的電影,除了能夠全方位解析中國電影創作流變的發展規律,更有助于電影創作者以高瞻遠矚的創造性理念推動中國電影藝術邁入全新的發展時代。
因此,對現實主義電影文本的創作,既要符合特定的社會文化語境,又要同新時代藝術發展的客觀需求進行巧妙對接,將電影欣賞者的觀賞價值擺在至關重要的地位,及時創作出反映群眾集體呼聲、彰顯人民價值取向、營造和諧美好家園的文化藝術作品,用藝術化的戲劇表達方式,彰顯現實主義美學的風骨和氣概,向上傳遞出具備正能量的精神風貌,才能夠更進一步順應時代發展的潮流,創造出具有中國獨特魅力的現實主義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