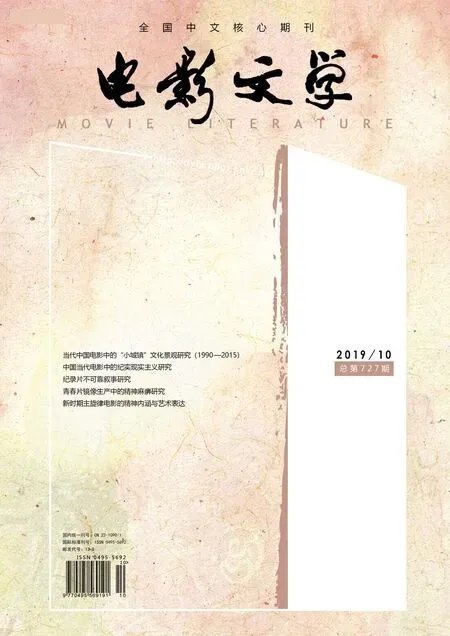論李安電影東西方觀眾的共同接受
曹文慧 (徐州工程學院 人文學院, 江蘇 徐州 221018)
被學界喻為“父親三部曲”的《推手》《喜宴》與《飲食男女》是李安初涉影壇的三部力作,且在東西方觀眾中獲得了一致的好評。“李安的‘父親三部曲’系列電影以別具一格的美學風格和文化內涵而受到中西觀眾的喜愛與好評”,[1]為李安電影事業的發展確立了良好的片緣與人緣。《推手》是李安初涉影壇自編自導的劇情長片,這部影片獲得了臺灣金馬獎九項提名,最終獲得了最佳男主角、最佳女配角與評審團特別獎三項大獎。《喜宴》上映后同樣贏得了東西方觀眾的一致好評,該片獲得了柏林影展金熊獎,西雅圖國際影展最佳影片、最佳導演獎,金馬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觀眾票選最佳影片獎以及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從此,李安在國際影視界聲名鵲起,一舉躍入世界知名導演的行列。《飲食男女》的后勁很足,海外的回響很多,包括內地、香港及世界其他地區。該片獲得了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提名,且名列1994年臺灣十佳華語片榜首,還被美國影評人協會選為年度最佳外語片第一名。“父親三部曲”之后,《理性與感性》和《斷臂山》為李安贏得了更多的世界性贊譽。“拍完《理性與感性》回響非常好,拿下金熊獎、金像獎、金球獎、英國影藝學院獎(BAFTA,British Academy of Film & TV Awards),全球票房逾兩億美金。”[2]《理性與感性》獲得了極高評價,使得李安成功地跨進了好萊塢主流電影制作的大門。《斷臂山》自威尼斯影展斬獲金獅獎后,一路捧金,獲得了第78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最佳原創音樂、最佳改編三頂桂冠。中國觀眾一樣非常喜愛這部影片。“《斷臂山》是一部需要慢慢回味的影片,這種回味其實是一種反應的過程,哪怕已經看得掉淚,也仍然需要時間來反應,就像片中丹尼斯要有時間才能反應過來自己對杰克的愛一樣。在我的電影經驗中,從沒有見過兩個如此陽剛粗獷的男人相戀,而且一直戀到老,也沒有見過一部影片如此把一份宗教和倫理意義上遭受天譴的不平常感情表現得正常如日出日落。從這個意義上,《斷臂山》呈現出它藝術片的品質,不同于制造千篇一律之夢的好萊塢電影,它讓人看到生活的無限性和愛情的無限性,愛情總是要超出我們已有的理解和界限。”[3]李安的上述五部影片在東西方觀眾的接受中獲得了一致好評,在此將這種接受狀態命名為具有廣泛觀眾基礎的東西方觀眾的共同接受。
一、尋找東西方觀眾共通的情感
李安的上述五部電影之所以取得了東西方觀眾的共同接受狀態,這與李安在影片中所體現的深刻思想內涵是分不開的。李安將“家庭”與“愛情”這兩大人類永恒的話語進行了個人化的獨特闡釋。這一獨特闡釋在某種程度上恰恰契合了東西方觀眾在這兩方面所具有的共通情感,從而開辟出東西方觀眾對上述五部影片的共同接受路徑。
眾所周知,盡管東西方文化存在著本質的區別與具體形式的千差萬別,但是人類文化中的共性也在東西方文化之間或隱或顯。因此,在強調東西方文化差異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源于人類生理、社會生活基本需要所帶來的文化普遍性。“不同文化或民族之所以能夠交流、溝通,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的生命存在通性或同一性。人之作為人,總是有許多共同的東西。首先,都有共同的生理特征、身體結構和與之相聯系的心理和行為方式,它們構成了人類共同的文化和心理與行為的自然基礎。”[4]正因如此,東西方觀眾在情感指向上存在一定的共性。東西方文化中的“家庭”與“愛情”這兩個基點,恰恰是李安所選取的兩個重要的來自人類情感的代表,它們都是人類永恒的話題所在,在東西方觀眾的情感指向上具有一定的相通性。
李安在“父親三部曲”、《理性與感性》和《斷臂山》這五部影片中將東西方觀眾在“家庭”與“愛情”中所體現的共通情感通過以下兩個方面來完成:一是“尋根”的家庭。“尋根”的家庭是指李安電影中的家庭契合了當下東西方觀眾心中對于理想家庭的向往與渴求。這方面主要體現在李安的“父親三部曲”中。東方文化中的家庭觀注重傳統的家庭倫理,重和諧,重道德。相比之下,西方文化中的家庭觀則強調個人自由意志的伸張釋放。但是,全球化進程加速了西方家庭價值觀念對于中國傳統家庭文化的滲透,中國家庭中出現了家庭倫理觀念的西化等問題,同時,西方的家庭自身也面臨著諸多問題。“保守主義者對家庭的變遷持悲觀的態度,哀嘆家庭的式微、父親從孩子的生活中消失、傳統價值的淪喪以及社會秩序的破壞。”[5]在這種情況下,東西方觀眾都在渴盼著充滿溫暖親情的理想家庭生活,李安將西方家庭與東方家庭中這點相同的部分進行了強化突出與有力強調,從而展現出共同的對于理想家庭的渴求。在“父親三部曲”中,東方觀眾可以重新審視西方家庭的價值觀給東方家庭所帶來的沖擊,而對于西方觀眾來說,李安則將東方家庭觀作為一個參照點默默地修復著西方觀眾的家庭價值觀念,而這一點恰恰是李安獲取東西方觀眾共同接受的獨到之處。“在金球獎典禮上,李安感謝所有人支持他回到中國尋根,根是什么?是一個長久居于都會、受西方價值沖擊困擾的精神所系。李安在所有影片中都努力復制這些傳統信仰,從《推手》《喜宴》《飲食男女》甚至《理性與感性》,從太極、社會習俗、生活諺語、做人處世,他不急不緩地琢磨著典型的價值困境,讓全世界觀眾以漸進的方式認識中國,以及為什么被西方價值沖擊后,可以向這個傳統或信仰得到救贖或變通的力量。”[6]可以說,不僅東方觀眾通過李安影片中所展現的傳統信仰找尋到了“救贖或變通的力量”,西方觀眾也在以東方傳統家庭觀作為參照系審視著自我的家庭信仰。因此,正是“尋根”家庭的信念契合到了東西方觀眾的心靈深處,使東西方觀眾產生了接受上的共鳴和認同。二是“普遍”的愛情。《理性與感性》和《斷臂山》就是李安從“愛情”這一基點表達東西方觀眾這一共通情感的影片。《理性與感性》拍攝之前,李安曾表態要讓這部電影重重地擊碎人心,要讓觀眾花上兩個月的時間才能痊愈。事實上,他做到了。《理性與感性》創造了哥倫比亞公司觀眾試映滿意度87%的最高紀錄。“影片在各地上映時,很多人可能都有這種體驗,覺得好像是在看自己民族的故事一樣。人的愛憎、喜怒哀樂可能會因文化的不同而表現為不同的方式,但是來自不同文化的故事可以打動不同的人群,除了文化普遍性,最能打動人心的應該是情感了。”[7]在《理性與感性》中,姐姐埃琳娜與妹妹瑪麗安面對愛情和婚姻時而痛苦萬分時而開心歡笑的鏡頭,無不牽動著東西方觀眾的心,產生著深深的情感共鳴。《斷臂山》盡管被西方主流媒體和電影界評價為一部“西部同性戀史詩”,但更多的是在強調其“超同性戀的一面”。《斷臂山》講述了一個蕩氣回腸的具有普遍意義上的“愛情”故事。主人公恩尼斯(Ennis)和杰克(Jack)相愛終不能相守,任歲月流逝,物是人非。盡管《斷臂山》講的是同性戀情,但在東西方觀眾的眼里,它已經超越了所謂的同性戀情,達到了一種普遍意義上的人類對于真愛這一美好情感的憧憬與渴求。“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斷臂山”,這部電影的宣傳語足以道出《斷臂山》吸引全球觀眾的根源所在,它不僅讓西方觀眾為之淚流滿面,也讓東方觀眾為此深受感動。李安堅稱《斷臂山》講述的是一部關于愛情的影片,描寫的是具有廣泛意義上的愛情,是超越了性別的具有人類普遍共通意義上的情感。而這也正是不同文化背景、價值取向與道德標準的東西方觀眾共同接受此片的原因所在。
二、通俗易懂的線性敘事結構
李安在上述五部電影作品中,所表達的東西方觀眾在“家庭”與“愛情”這兩大人類永恒話語上所具有的共通情感,是獲得東西方觀眾共同接受的重要原因。李安在影片中對這一深刻思想內涵的挖掘則是通過采取契合東西方觀眾普遍觀影心理的通俗易懂的線性敘事結構這一形式來完成的。可以說,李安在上述五部電影作品中所采取的通俗易懂的線性敘事結構,同樣是獲取東西方觀眾共同接受的一個重要原因。
李顯杰曾在其著作《電影敘事學:理論和實例》里這樣描述電影的敘事結構:“具體到電影敘事結構講,所謂敘事結構同樣是一個擁有多級層面的復雜概念。其首要的和最基本的一個層面,是指一部具體影片的結構(組織)關系和表達方式。”[8]所謂電影的“線性敘事結構”通常是指在電影的敘事過程中,按照故事發生的前后順序,依照時間的先后來介紹人物并展開情節,遵循故事的開端、發生、發展、高潮與結局完成對一部影片的敘事。這一敘事結構傾向于將故事的來龍去脈講述得清清楚楚且有頭有尾,講求故事的連貫性與完整性,并力求故事生動曲折,情節引人入勝。“故事是時間與空間的藝術。使事件在時間與空間上順序展開,是故事最原始,也是最自然的結構。它符合人們對時空感知的習慣,符合模仿客觀現實的存在形式。它既保證了創作行為的順利進行,也保證了閱讀行為的順利實施。所以,這種所謂線性的最基礎結構,提供了創作與閱讀的交叉點。在這個點上,創作者與閱讀者似乎可以毫不費力地相互交流。”[9]這一敘事結構比較完整地體現了故事的發展過程,是較為傳統的一種電影敘事方式。
李安的上述五部電影的敘事結構都屬于這種線性敘事結構,有著很強的故事性,形成了既清晰完整又跌宕起伏的故事鏈條。可以看出,這五部影片的故事情節都有著開端、發生、發展、高潮和結局的線性敘事結構。在“父親三部曲”中,李安詮釋的是“家庭”這一主題。《推手》中,朱師傅從來美國到離家出走直至租房自居,兒子朱曉生從對父親的不在意到苦苦尋找直至對父親的深深內疚,有著開端、發生、發展、高潮和結局的線性敘事結構,而且其間融合著片中每個人對“家庭”之內涵的思考。《喜宴》以一個善意的謊言將以高父為代表的東方家庭理念,和以偉同與賽門為代表的西方家庭觀念進行了碰撞與交融,從而影響著片中的人物達成互相的理解與體諒。同樣,李安在《理性與感性》中所表現的19世紀英國兩姐妹埃琳娜和瑪麗安在理智與情感的糾葛中,面對愛情與婚姻進行艱難抉擇的委婉愛情故事,以及《斷臂山》中兩位牛仔從相遇、分別、相見、永別的人生際遇發展中所演繹的那份永不褪色的真情故事,都是與李安所采取的通俗易懂的線性敘事結構完美地結合在一起的。
綜上所述,李安不僅在上述五部電影中表現了東西方觀眾在人類情感指向上的共通性,還將這一思想內涵與通俗易懂的藝術形式有機地結合了起來。“中國電影已登上世界影壇,并必將在世界上贏得愈來愈多的觀眾,但絕不是靠東方色彩,而是靠愈益成熟豐富的電影語言描繪出中國人身上與世界各民族相通的、能得到共同理解的東西。”[10]李安將深刻的思想和通俗的形式完美地結合在一起的電影實踐,有效地促成了東西方觀眾對其影片的共同接受與認可,也為當下的電影創作實踐提供了某些可以借鑒的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