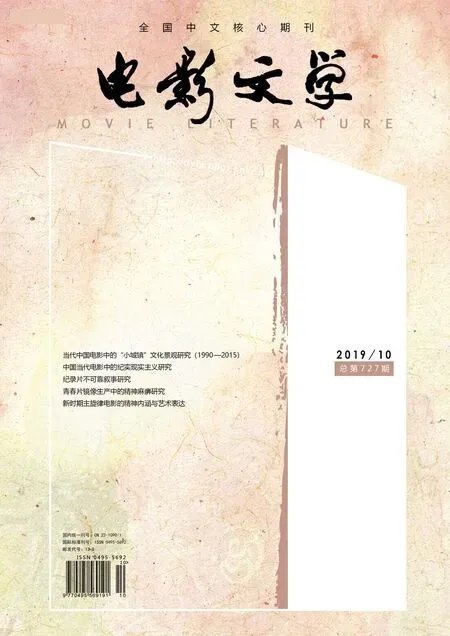《綠皮書》的現實主義表征
鄭 強 (鄭州西亞斯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在藝術多元化的當下,人們不得不承認現實主義藝術遭到其他話語的沖擊,尤其是電影藝術被認為進入了“后假定性”時代,觀眾更熱衷于為一個虛幻的,充斥奇觀的世界消費,現實主義似乎面臨著式微的尷尬。而在這樣的情況下,由彼得·法拉利執導的,根據真實事件改編而成的《綠皮書》(2019)卻帶有鮮明的現實主義表征,一舉贏得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原創劇本等獎項以及長時間在美國國內外市場上的熱映,宣示著現實主義的強大力量。
一、生活的“鏡像”
以寫實的手法對現實生活進行客觀可信的再現,這是現實主義最首要的基本原則。現實主義作品的性質與形態,都是基于這一原則上體現出來的,如無論是批判現實主義,新客觀現實主義抑或是神秘現實主義,作品都應該被視為生活的“鏡像”。
《綠皮書》中展開的,正是一幅現實生活的畫卷。電影中的主人公托尼·瓦萊隆加和唐·謝里在1962年相識,并一起經歷了一段前往美國南方的,充滿了酸甜苦辣的旅程。鋼琴演奏家謝里從紐約一路南下巡演,一直到全美種族隔離問題最為嚴重的伯明翰,兩人結下了深摯的友誼,直到他們在2013年相繼去世。電影所聚焦的,正是兩人這一段旅程,而片名“綠皮書”,則來自當時唱片公司給身兼司機、保鏢、助理等職于一身的托尼的一本 “黑人出行”指南(由黑人郵政員維克多·雨果·格林編寫),這一綠色封皮的指南介紹了在種族隔離,尤其是“白人至上運動”正掀起高潮的時候,黑人可以進入哪些旅館、餐廳等公共場合。謝里在明知南方對黑人的態度的情況下,毅然決定用自己的演出來提升黑人地位。而受雇于他,與他形影不離的托尼卻是一名意大利裔白人,且托尼自身就有著不自知的歧視思想,一路上,托尼就看到了謝里的種種遭遇,在不知不覺間,改變了對黑人的看法。
例如,在謝里晚上一個人去酒吧時,喝醉后被一群白人圍毆,白人壯漢們僅僅是因為謝里的膚色就認為可以對其隨意欺辱,托尼不得不以暴制暴,面對一堆拳頭和一把對準自己的刀,做出了即將拔出腰上手槍的動作震懾了對方,救回了謝里。又如謝里和托尼來到一所豪華的莊園后,莊園主十分有禮貌地接待了前來表演的謝里一行,然而在演出中的間歇,與謝里同行的三重奏另外兩位音樂家因為是白人,就可以使用洗手間。而謝里卻只能使用院子里一個簡易棚子里的茅坑,即使謝里是地位崇高的鋼琴家,甚至曾經在白宮演出過,他也不能動搖這種種族隔離制度,為表示反抗,謝里馬上讓托尼開車帶他回賓館上洗手間。謝里的黑人面孔還讓他遭遇了交警的尋釁,在托尼毆打了警察后,兩人被關進監獄里,如果不是謝里打電話給了總統肯尼迪的弟弟,得到了“特赦”,兩人還將毫無尊嚴地被關押下去,錯過之后的演出。初次出現在托尼面前的謝里,因為財富、考究的舉止和某種優越感,是托尼眼中的“黑人酋長”,然而他們越是向南方走去,社會對于黑人的壓迫感也就越強,謝里的狼狽無助之態也就越多。托尼感受到,歧視是無處不在的,他漸漸開始反思社會,也反思自己。
一言以蔽之,《綠皮書》記敘的是托尼和謝里兩人的個人體驗,八個星期的生活在吃飯、趕路、演出以及一次次與他人的沖突中度過,但是給予觀眾的卻是對一個時代的整體性感知,觀眾的觀影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進入20世紀60年代美國人生存世界的過程。
二、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
恩格斯曾經在給英國女作家哈克奈斯的信中針對《城市姑娘》提出典型人物的命題:“據我看來,現實主義的意思,除了細節的真實外,還要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人物。”后來這也被視為是現實主義的原則之一。所謂的“典型人物”,指的是不可替代的藝術典型,他必須是主創從現實生活中提煉出來的具體、生動,有代表性的人物,主創在表現人物的特征時,還有必要真實地、歷史地對人物何以具有這樣的特征進行揭示,人物與環境要具有統一性,同時人物的命運,還要符合或暗示了歷史發展的必然規律。在《綠皮書》中,前述人物活動的被鏡像化了的,南方與北方,種族矛盾緩和和尖銳交錯的環境,正是一種20世紀60年代初,平權運動還沒有充分展開,但已在醞釀之中的美國社會典型環境。而謝里和托尼兩個人,則是本身就具備了諸多代表性,同時又被電影強化了這種代表性的典型人物。
托尼由于姓氏瓦萊隆加發音復雜,因此有“托尼·利嘴”的別稱,出身市井的他正如他自己坦承的:“我生長在一個小社會,周圍全是我的親戚和熟人,我沒讀過什么書,沒見過什么世面,不像你受過這么多教育。”也正因如此,托尼擁有著謝里不具備的街頭智慧。如在夜總會做保安時,托尼知道夜總會即將要停業裝修,于是賄賂衣帽間女郎藏起了黑社會大佬羅斯古德的帽子,夜總會被不痛不癢地“停業”,衣帽間女郎因為拿了錢而不敢揭發托尼,托尼趁此幫羅斯古德“找回”了帽子,得到了成為黑社會大佬“兄弟”的機會。除此之外,托尼還有勇敢的一面,如在失業后敢去和大胃王挑戰吃熱狗等,正是這樣的街頭智慧和勇氣,讓托尼一次次地保護了謝里。但這種生存環境也造成了托尼的種族歧視意識,在電影一開始,因為家里請了黑人工人,一幫親戚全來到家中“保護”托尼的妻子德洛瑞斯,在工人走后,托尼還嫌棄地將工人用過的水杯扔到了垃圾桶中。在知道托尼要做謝里的司機后,所有親戚都覺得托尼沒多久就會將謝里痛打一頓。原本就是邊緣族裔的意大利裔們有著根深蒂固的對黑人的歧視。
而謝里則曾經留學蘇聯,擁有博士學位,懷著改變黑人地位的一腔孤勇離開紐約卡耐基音樂廳,低調而堅定地用演出支持黑人民權運動,相比起托尼的“小勇”,謝里具有一種“大勇”。而對比托尼的粗鄙庸俗,謝里則處處表現出優雅自尊的一面,在謝里看來:“暴力永遠無法取勝,堅守尊嚴才會贏,因為自尊總能讓你占理。”這是動輒對他人拳腳相見的托尼不能理解的。在路上,講究言行的謝里不愿意在車中吃炸雞,托尼卻大快朵頤,還將炸雞扔到謝里的手中,并示范如何將吃完的雞骨頭扔到窗外。謝里也學著吃炸雞,扔骨頭,但卻在托尼將有可能對環境有危害的杯子也扔到窗外時勒令托尼倒車撿回杯子。謝里甚至對托尼承認了自己同性戀的身份,袒露了自己“不夠黑,不夠白,也不夠男人”的痛苦。在托尼慢慢改變自己對黑人的狹隘認知的同時,謝里也主動接近這位處于社會下層的朋友,情誼最終超越了兩人在種族、階級上的隔閡。在電影的最后,謝里終于回絕了讓他感到不被尊重的演出,在酒吧的破鋼琴中放下身段彈奏了爵士樂,并和托尼驅車回家,參加了托尼家的圣誕晚宴。
可以確定地說,托尼和謝里是電影塑造的成功的藝術形象,兩人在種族、財富、性取向、文化程度等方面截然不同,分別是社會不同場景中的強勢者或弱勢者,但二人又有著善良、公義上的相同之處,兩個角色體現出了法拉利等人豐富的藝術經驗。
三、人文情懷與娛樂元素
現實主義與紀實主義的區別之一,就在于二者雖然都對現實生活進行較為完整忠實的記錄,并不刻意去改變其面貌,或干預人物行為的自然進程。但是紀實主義認為,世界是可疑而模糊的,因此紀實主義電影中的情感、道德判斷或意識形態分析是缺席的,觀眾必須自己去為電影中各種“原汁原味”的場景尋找意義。而現實主義則不然,現實主義所呈現的“大寫的真實”,背后一定有著某種意識形態,甚至可以說,現實主義的人文情懷以及理性力量,早已內化在其本體價值之中,電影人正是在某種先行的價值理念的驅使下進行創作的。
《綠皮書》批判了種族隔離這一與人類發展相悖的制度,提倡多種族之間的交流與溝通,并且對居于歧視鏈中的弱勢者給予了同情。謝里在努力為黑人群體正名的同時,遭遇的卻是來自黑、白雙方群體的共同敵對,黑人們認為謝里為白人演出,滿足白人的附庸風雅,不彈爵士而彈古典,以及他高高在上、西裝革履的生活方式是對種族的背叛,因此并不以謝里為驕傲,反而譏諷他。但是黑人在自我保護時做出的這種與白人劃清界限的行為,其實又是對種族隔離的一種變相支持。在電影中,謝里在托尼停下來修車時注視著一群正在田野里勞作的南方黑人,對方也用一種疑忌的眼神看著謝里,認為這個能讓白人給他工作的黑人是天外來客。謝里陷入沉默之中,他感到了自己的格格不入。尤其是作為一個同性戀者,他更是在社會群體中無所適從,如果不是托尼的介入,他將成為一個孤獨對抗整個世界的人。但電影又給予了觀眾不少溫暖而美好的片段,預示著諸多歧視終將消弭,如托尼帶謝里離開謝里被欺負的餐廳時,黑人侍者臉上露出微笑;原本都當黑人是潛在犯罪分子的托尼的親戚們,在謝里登門后毫不猶豫地歡迎了他;平安夜路遇警察,托尼和謝里原以為又將面臨沖突,不料警察只是友好地提醒他們車胎癟了等,人并不應該被貼上“黑”“白”“同性戀”的標簽而被羞辱壓迫,這正是電影傳達出來的一種具有積極意義的價值觀念。
值得一提的是,現實主義從來就不是一個封閉的話語類型,在不同的時代,現實主義都在進行自我更新。就電影而言,當代的現實主義電影更是積極地與商業美學進行對接,或是提升形式上的精致感,制造視覺沖擊力,如《拆彈部隊》(2008),或是在敘事上與類型片結合,如《國王的演講》(2010)等,都是得到奧斯卡首肯的,進行了商業和娛樂包裝的現實主義電影。而在《綠皮書》中,法拉利選擇了為電影加入大量幽默的情節,提高電影的娛樂性。托尼和謝里在一起時因為文化背景,文化程度不同而常常雞同鴨講,如托尼說妻子買了謝里的“孤兒”(Orphan)專輯,封面上的火爐旁邊圍了一群小孩,然后謝里告訴托尼那張傳記的名字叫“俄爾普斯”(Orphus),那些也不是小孩而是地獄里的魔鬼;在開車的時候托尼總是喋喋不休,于是謝里叫他安靜一會兒,而托尼就繼續嘮叨自己的妻子是如何也叫自己“安靜一會兒”,謝里在車上十分無奈;又如托尼在用“聽寫”的方式寫情書時,將“親愛的”(dear)寫成“鹿”(deer)等。種族和解的問題是復雜而沉重的,但是電影在進行“以小見大”的處理時卻能將“小”安排得笑點不斷,妙趣橫生,使電影受到觀眾的歡迎,這其實也是《綠皮書》給予我們的啟發之一。
可以說,《綠皮書》是一部具有現實主義品格的作品,電影在還原歷史人物生活表象的同時,也還原了他們生活的本真狀態,托尼·瓦萊隆加和唐·謝里作為典型人物被觀眾認識,他們的生存體驗能被觀眾較好地感知,而電影追求平權,主張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乃至提升人的生存意義的價值立場,也由此傳達了出來。奧斯卡以及觀眾對于《綠皮書》的嘉許,無疑證明了現實主義在電影市場多元化格局中依然有著深厚的社會文化基礎,電影對嚴峻殘酷生活的洞察,對不乏溫情和希望的人性的透視,正是其最有力的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