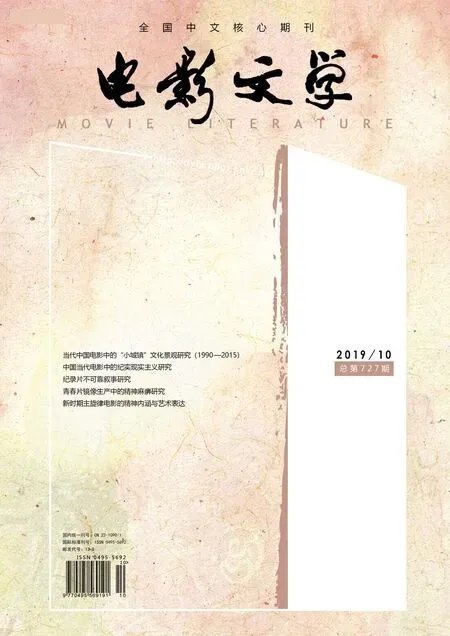《雪花秘扇》:西方后殖民視野下的東方女性身體符號分析
龍森祥 (玉林師范學(xué)院,廣西 玉林 537000)
《雪花秘扇》上映于2011年,為曾經(jīng)執(zhí)導(dǎo)《喜福會》《煙》的華裔導(dǎo)演王穎所拍攝。影片采用了傳統(tǒng)的雙線敘事結(jié)構(gòu),以女書和索菲亞的小說為線索,講述了發(fā)生在1800年湖南江永與2010年上海的兩組女孩的隱秘情感。《雪花秘扇》對影片中表現(xiàn)的民間風(fēng)俗、文化、規(guī)矩、陋習(xí)更多的是一種冷靜的“旁觀”,對影片內(nèi)角色所遭受的苦難,多是以一種平靜的、置身事外的眼光在跟隨與分析。也許正是因為這種始終保持中景的鏡頭選取、影片背后敘事者不介入、不干預(yù)的態(tài)度,構(gòu)成了影片在故事展示層面的非通俗性。特別是影片中出現(xiàn)的對角色身體細(xì)節(jié)的特寫、對主要角色形象的選擇、對“想象中的中國”的具象化裁剪和展示,都反映出影片在女性情感故事主題之外,所想要強調(diào)的內(nèi)在秩序與審美取向。影片中的種種肉身的特寫與言語的表征,隱含著男女性別政治、東西文化震蕩的討論,本文也基于此,試圖厘清影片中嘗試言說的、試圖言說的,與未曾言說的西方與東方。
一、三寸金蓮、女書與發(fā)髻——女性肉身的“奇觀化”
《雪花秘扇》作為一部以女性角色為主體的影片,女性是影片中占據(jù)篇幅最多的角色。不論是索菲亞和妮娜,還是雪花與百合,在兩人集體出現(xiàn)時,始終是在影片的中央的。運鏡無時無刻不在強調(diào)主角的存在,然而在敘事的節(jié)奏上,女性則相對讓位給了女性身體部位的元素與符號。開場的前三十分鐘,影片就已經(jīng)展示了纏足、刺繡、女書、哭嫁等內(nèi)容。和國內(nèi)傳統(tǒng)導(dǎo)演對三寸金蓮的描摹不同,《雪花秘扇》毫不遮掩地展示了纏足的大部分過程,影片中反復(fù)地出現(xiàn)了對纏足的特寫,不管是由母親進行纏足,還是百合出嫁后,新婚丈夫?qū)Π俸系摹敖鹕彙弊龀龅膼勰脚e動,這一系列的鏡頭語言本身就構(gòu)筑了一個荒誕的世界。在這一層的敘述與演說中,許多角色設(shè)置都是對調(diào)的:百合因為纏出了完美的“金蓮”,從農(nóng)戶人家嫁入了桐口最富庶的家庭;而出身相對富裕的雪花,則因為父母親族的衰敗,只能嫁給村中的屠夫。影片中百合自陳:“金蓮使我時運轉(zhuǎn)。”“金蓮”在這一層含義上則成為獨立于人格的物件,是女性被物化、被賞玩的具體展示,是外界男權(quán)社會道德規(guī)范建構(gòu)于女性肉身之上的規(guī)勸與訓(xùn)誡,是一種男性權(quán)力與審美凌駕女性的意志的實體化。
與“金蓮”相比較,女書則是對脫離了男性秩序規(guī)范后的一種“低聲私語”。在影片的前半段,幫雪花和百合結(jié)為“老同”的媒婆,直白地對二者說道:“女書是女人之間的秘密語言,也是你和老同的溝通方式,你必須和老同一起學(xué)習(xí),這樣才能夠了解對方的心。”換言之,女書與承載歷史文化、綱常社稷、仕途命運的漢字不同,女書從功能上只是女性寄托情感、自我表達(dá)、體認(rèn)的工具,被去除了其中的功利性。緊接著媒婆的陳述,影片后續(xù)展示了年幼的雪花和百合用手指在對方背上寫女書的畫面,這也間接暗示著女書承襲的是一條隱藏的敘事脈絡(luò),是敘事功能之外影片情感宣泄的展示,和“金蓮”等被規(guī)訓(xùn)與建構(gòu)的身體符號相比,女書反映的是內(nèi)心,因此對比女書和纏足,可以看到影片嘗試展示的陽性與陰性的敘述表征,這種陽性的規(guī)勸訓(xùn)誡與陰性的自剖自陳形成了兩種鮮明的敘事復(fù)調(diào),也烘托了1800年故事線中兩位主角的人生矛盾的對抗與拉鋸。
影片的角色服裝設(shè)計同樣也非常具有跳脫的審美趣味與隱喻象征的內(nèi)涵。在二人出嫁后,雪花和百合的發(fā)型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百合通過“一雙完美的金蓮”嫁給了當(dāng)?shù)財?shù)一數(shù)二的有錢人家時,她的頭發(fā)也變成了厚重的、規(guī)整的盤發(fā),在這沉重的發(fā)髻上還裝飾了許多黃金首飾。與她成為映照的是她的婆母,作為一個家族地位最高的女性,百合的婆母有著同樣沉重的,甚至是突兀的、獵奇的發(fā)髻。二人的發(fā)髻一絲不亂,而家族的嚴(yán)整秩序與發(fā)髻暗合,呼應(yīng)著一個極其有秩序、極其受人尊敬,但也嚴(yán)絲合縫到讓人窒息的封建家族世界。相反,雪花因為家族敗落的原因,嫁給一名屠夫后,她的頭發(fā)也一掃過去的氏族遺風(fēng),變得蓬亂、隨意,不規(guī)整。在雪花與百合廟中相會的情節(jié)里,雪花雖然有意華麗打扮,但頭發(fā)上依然掩飾不住有些蓬亂,這些細(xì)節(jié)也代替了影片的直接敘事,成為人物命運變化的暗示。
二、從“清末”到“現(xiàn)下”的雙層平行敘事及其敘事功能
故事采用的雙線敘事結(jié)構(gòu)縱貫了1800年晚清時期與2010年的現(xiàn)代。敘事的焦點也在雪花與百合、索菲亞與妮娜之間不斷猶疑和轉(zhuǎn)換。雪花與百合的境遇同時也是索菲亞與妮娜的人生際遇,因此兩者之間的故事展開則有了互文性,也同樣增加了對比。在《雪花秘扇》中,女性部分身體部位常常被導(dǎo)演以特寫的方式展示,如在妮娜奔走一天之后,她坐在醫(yī)院的長椅上,用手去撫摸自己穿高跟鞋的腳踝,鏡頭緊接著便切換到1800年的百合所裹著的小腳上。這種鏡頭的切換,無疑是在暗示觀眾當(dāng)代人對高跟鞋的審美與古代纏足的某些相似性,穿上高跟鞋走路搖曳生姿的女人與古代纏足后走路搖晃的女人并沒有本質(zhì)區(qū)別,同樣是犧牲舒適感迎合審美取向,纏足已經(jīng)被大眾所拋棄,然而高跟鞋則成為新的審美時尚。這種吊詭的邏輯背后所展示的,正是女性身體被觀賞、被規(guī)訓(xùn)的歷史與大眾的無意識潛意識。女性的肉身苦難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在社會法度的規(guī)訓(xùn)中被強加的、被設(shè)定的,影片中為了加強這一邏輯,格外強化了女性角色的作用,可以看到影片中對主角加以控制的往往都是以母親、婆母等身份行使權(quán)力的女性。
從“清末”到“現(xiàn)下”的雙重平行敘事,除了比較烘托兩個時代女性命運的變化與不變外,導(dǎo)演也在嘗試推演構(gòu)造一種女性主體發(fā)聲的敘述邏輯,這一點幾乎貫穿著“清末”和“現(xiàn)下”兩個故事的敘事背景中,在1800年的故事里,導(dǎo)演如同走馬燈一般向觀眾展示了許多歷史事件對湖南鄉(xiāng)村的影響,在一個半小時的展示里,鴉片傾銷、道光十二年大疫、太平天國等歷史事件的波瀾都隱沒在主人公的命運中,這種一攬子打包化的綜合展示也表現(xiàn)在對中國、對湖南民俗的表現(xiàn)上,不論是影片開場時,作為背景兩名女性演繹的越劇《梁山伯與祝英臺》,還是《伴嫁歌》《哭嫁歌》,抑或是對“三寸金蓮”的幾個特寫,對女書書寫的奇觀化展示,都不同程度表現(xiàn)出了一種“獵奇”的審美趣味。觀眾正是借由導(dǎo)演的眼光與窗口,踮腳向一個更隱秘化的深層敘事中遙望探看,這種探看顯然是更加私人與更加西方化的。正如新婚之夜,百合的丈夫?qū)Π俸系摹叭缃鹕彙钡陌V迷審視,觀眾此刻也從對中國傳統(tǒng)的文化民俗的觀看不可避免地轉(zhuǎn)移到了對封建陋習(xí)的奇觀想象中了。這種奇觀化與片段式的遐想不僅僅存在1800年的敘事中,在當(dāng)代依舊被保留著,甚至被無意識地夸大了。影片的當(dāng)代視角下,上海是一個沒有貧窮和潦倒,只有高檔酒會、紙醉金迷的幻想之地,圍繞在兩位女主角周圍的男人非富即貴,這種強加于現(xiàn)代中國的想象顯然與國內(nèi)現(xiàn)實相差甚遠(yuǎn)。因此很大程度上,觀眾可以將《雪花秘扇》視作為一個為西方觀眾特別設(shè)置的,提純后的幻想中的中國。
三、陰性與陽性、外部與內(nèi)部、東方與西方、肉身與擬人的雙向?qū)φ?/h2>
雖然《雪花秘扇》的影片敘事內(nèi)容多而繁雜、但大多只限于淺嘗輒止。導(dǎo)演似乎更樂于用一種含蓄的、雋永的、詩意化的手段方法,展現(xiàn)這一個跨越時空的故事。這種敘事策略的選擇并非是無跡可尋的,相反,這和影片主創(chuàng)的個人經(jīng)驗、審美取向、影片發(fā)行面向的觀眾、影視資本市場有著深刻的聯(lián)系。導(dǎo)演王穎、編劇和原作鄺麗莎、主演鄔君梅、制片人鄧文迪等都為美籍華裔,在文化情感上,他們投入了更多的文化尋根的熱情,嘗試從風(fēng)俗、服裝、民歌等方面展示一個古老的中國。然而由于生活經(jīng)驗的缺乏,在影片中這種相對的“古老中國”常常表現(xiàn)出與實際的脫離,如百合的新婚丈夫在成婚當(dāng)晚,半跪在地上親吻她的三寸金蓮,這一扭曲的情節(jié)在導(dǎo)演的鏡頭選擇下,反而有一種復(fù)古的情致。這種視角在國內(nèi)導(dǎo)演攝制的國產(chǎn)影片中是罕見的,而這種略顯“民族風(fēng)味”的影片題材設(shè)置,也與該片預(yù)設(shè)的觀眾面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guān)系。《雪花秘扇》作為美國福克斯公司投資的影片,投資人、主創(chuàng)團隊、導(dǎo)演大多是遠(yuǎn)離故土多年的海外華裔,缺少對當(dāng)代中國生活的直接經(jīng)驗和直接感受,一些取材取向和中國發(fā)展之間有著斷層。而影片在上映時為全球發(fā)行,在審美取向上必然會為了迎合國外觀眾而做出取舍。因此,從一定層面上說,《雪花秘扇》正代表了海外觀眾群體對“想象中的中國”的審美趣味,對纏足過程的拍攝、對中國古代女性的命運展示、對現(xiàn)代上海接近于想象的畫面裁剪,如同電影的“陌生化”手法一樣,是滿足觀眾審美娛樂的趣味環(huán)節(jié)。也許正是這種處理,也導(dǎo)致國內(nèi)觀眾在觀影過程中感受到了某些“水土不服”,畢竟在現(xiàn)實中很難在國內(nèi)看到用英語代替普通話交流的中國人,也很難看到一個幾乎沒有平民,只有精英高管和燈紅酒綠的上海。導(dǎo)演在嘗試用片段和想象拼貼中國當(dāng)下的日常時,必然也會因為這種拼貼喪失其現(xiàn)實感與生活性。
然而這樣?xùn)|西方看似和諧的陽性與陰性、男性與女性的結(jié)構(gòu)一旦回歸于影片的“清朝中期”時空時,又發(fā)生了嚴(yán)重的倒置和錯位。在后半程百合婆家因流行瘟疫遭受重創(chuàng)時,百合則替代了本應(yīng)該承擔(dān)責(zé)任的男人,成為家庭事實上的管理者。這種調(diào)換既反映出在整體故事中男性角色的虛浮和游離,也從性別政治層面上跳脫了傳統(tǒng)西方眼光下的東方故事的窠臼。而百合的個人成長史也容易讓觀眾聯(lián)想到賽珍珠《大地》中“阿蘭”的形象,同樣是貧苦的出身、同樣作為家庭的精神靈魂支柱,兩者都表現(xiàn)出了對“地母”身份的包容、接納、忍耐。
這種常見的東方“地母”式的形象,與薩義德提出的“后殖民主義”的部分觀點有著呼應(yīng)。薩義德認(rèn)為西方眼光建構(gòu)下的東方世界常常既包含著蠻荒、粗糙與神秘的引誘,又包括了陰柔、包容、忍耐的美德。西方人對東方一直存有誤讀和誤解,因為西方理解東方的文化基礎(chǔ)并不存在。在《雪花秘扇》中出現(xiàn)的女性,她們既無力,卻又承載了家族的責(zé)任;她們既軟弱,卻又常常展現(xiàn)出強烈的情感力量;她們既聰慧謹(jǐn)慎,卻又往往被西方(男子)引誘與欺侮。《雪花秘扇》所表現(xiàn)的矛盾也正是女性身份符號、身體符號被西方觀看、閱覽、解讀、再生產(chǎn)后不得不產(chǎn)生的矛盾。《雪花秘扇》雖然主創(chuàng)人員皆與中國、與東方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但從本質(zhì)上,脫離了東方的、中國的文化語境,也就脫離了理解的客觀基礎(chǔ)。在《雪花秘扇》影片的結(jié)尾,導(dǎo)演通過蒙太奇,實現(xiàn)了百合與雪花的百年跨越,在上海金茂大廈的樓頂,兩位纏著三寸金蓮、穿著清朝旗袍的東方女子相視而笑,達(dá)成了和解。這或許也是影片創(chuàng)作者在雪花和百合的故事之外,更進一層意圖表達(dá)的東方與西方之間跨越時間、空間、身份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