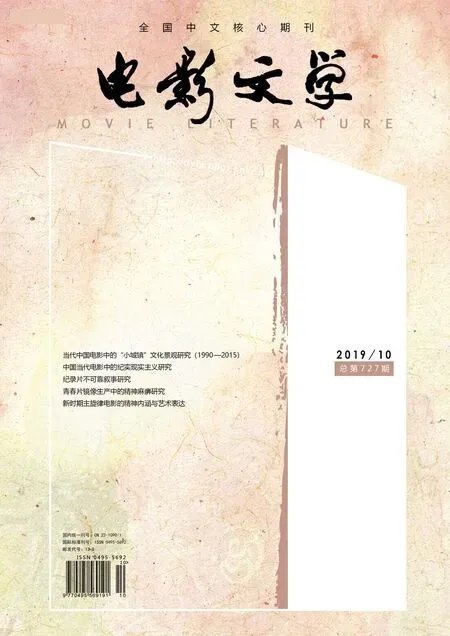視覺藝術心理視域下繪本動畫電影創作模式探析
徐 茵 徐曉紅
(1.常州工學院 藝術與設計學院,江蘇 常州 213000;2.常州大學 藝術學院,江蘇 常州 213019)
瑞典著名兒童文學家林格倫說:“希望兒童文學作品都能作為兒童生活的延伸部分而存在。”繪本承擔著將文字抽象思維轉化為兒童易于接受的形象思維的重要角色,而繪本動畫電影更是以視覺感官多維度呈現的存在成為兒童生活中精彩的“延伸部分”。動畫電影的終極受眾群體是兒童,關注兒童的心理需求以及教育的目的,使得建立在繪本創作基礎上的影視作品更具有生命力和市場拓展性。本文借由對根據經典繪本改編的動畫電影的分析,認知視覺藝術心理所起到的決定性作用,深層次探究繪本動畫影視作品行銷的審美特質。同時,通過分析中國傳統繪畫中特有的圖像敘事范式,力圖找到國產動畫發展的新思路,進而找到一種行之有效的動畫電影創作方法。
一、繪本動畫電影中視覺藝術審美的原始張力
繪本動畫電影是依托繪本創作,為兒童建構一個真實可感、寄托無限想象力的感知空間。這個感知空間中所有視覺元素相較于其他影視作品有一個最吸引人的特質就是具備能夠直擊心靈、充滿無限張力的視覺力。這個力量從何而來,又是以何種形式激發觀眾的認同感是研究繪本動畫電影創作的核心問題。我們對藝術形式的原理性研究,是以人們最根本的心理、生理需求為出發點的,真正觸及人類靈魂的藝術效應呈現出“純粹”“真實”“自然”的特性,這種特性在原始藝術和兒童畫中展露無遺。繪本單純而富有哲理的內涵、簡單而精準的視覺形象、直白而巧思的畫面組織,恰恰是這種具備純粹藝術性的視覺藝術形式。阿恩海姆認為:“作為一個藝術家,他必須依靠那些直接的和不言而喻的知覺力來影響和打動人們的心靈。”[1]根植于人類內心世界的最基本的需求形成原始張力,這個張力是藝術表現的內在動力,也是人們建立視覺審美體驗的基本前提,當這種張力與人類生命屬性形成意義上的共鳴時,就能產生深刻的影響。視知覺張力來自主體對生活的感悟和創造性的想象力,原始藝術中出現的大量螺旋紋、凱爾特繩紋等裝飾形式是早期人類不受拘束、由本性驅動的對形式美的自由表現,是人類天性結合生活實際需求的產物。兒童完美地保留著這種本性驅動行為,大膽、直接、熱烈地表達對客觀世界的認知。兒童心理學家發現,5~9歲的孩子畫圖,會自覺地尋找與內心對應的外部事物,看似不經意而又持續肯定的連續線條,就是本性驅動的表現結果。這種原始“野性”的張力表現是畫家保羅·克利所看重的,聲稱自己的藝術也要“從亂畫開始,帶著線條去散步”。被認為美國第一本表現孩子強烈情緒的繪本《野獸出沒的地方》(莫里斯·桑達克)中,看似凌亂無序的線條恰巧將處在激烈情緒下的兒童心理烘托得淋漓盡致。在由該繪本改編的電影《野獸家園》中,整體影片從片頭影視公司的出場鏡頭到整體畫面形式風格都完美地摹寫了原作想要表達的視覺、心理效應。
繪本因受眾群體是兒童,天生被要求具備這樣的原始張力,創作過程中以單純而特定的形象、連續有意味的連貫畫面直入人心。繪本動畫電影以原繪本的“張力”結構為基本框架,以特有的鏡頭語言重塑影片,將這種張力放大,更好地調動受眾體的審美認知,達到心靈上的高度共鳴。兩者的結合正如米開朗琪羅《創造亞當》中上帝和亞當手指輕觸的那一刻,產生了無可估量的審美感受。中國動畫電影正在崛起,度過了模仿跟風的階段,正處在自主生長期,應該認真審視國外動畫電影發展的成功經驗,從創作的源動力去找尋出路。我們應該看到我國豐富的創意文化資源,以及傳統繪畫中特有的視覺形式的審美表現,破除思想禁錮,走上文化自信的自主發展道路。
中國繪本發展起步較晚,但是有著歷史悠久的人物故事畫發展歷程。中國繪畫藝術強調和保持住藝術觀念上的理性的單純簡潔的特點,以強調固定的物體形狀為主要目的,把絕大部分注意力放到了揭示物體恒常性結構關鍵的部位——輪廓線。在某種程度上,中國繪畫藝術的原始張力更接近兒童的認知習慣。特別是魏晉以前的繪畫,符號化的現象普遍存在,更多通過程式化、夸張、概括、充滿想象力的審美形態來強化事物的本質特征。形象被藝術家賦予了一種內在的力量,是經過提煉的傳遞強有力信息的審美符號。同時,通過多種形式的畫面結構布局,將故事生動地再現在畫面中。四川彭州出土的漢代“采蓮漁獵”畫像磚中,借助高度概括但又生動有力的形態以及“異時同圖”的構圖手法傳遞信息,將捕魚和狩獵這兩項日常活動組合在一起。如此清晰明朗的視覺形象和“非理性”的不同時空的創意組合,恰恰符合人內心追求的本質性的審美需求,中國繪本動畫電影正可以借由這股“原始力量”進行創作,提高文化傳承性的同時提升作品內在的藝術張力。
二、主觀情思下的意向性視覺形象
視覺藝術心理審美結構的產生是一個不斷精簡、進化的過程,在進化中,最有效率和實踐性的能力得以保存在基因鏈中。人的天性是根據“內在需求”對外界快速反應和判斷,只有那些極為簡化又高度概括的形態才有可能被記憶、傳遞。從藝術表現形式來說,特征突出、高度簡化的視覺形象天生具備這樣的特質,正如繪本中的視覺形象表現的那樣,符合兒童的視覺接受習慣,直取主要印象,保留那種未被影響的直覺和無拘束的想象力。經典繪本中經過千錘百煉形成的視覺形象簡潔生動,保持一種極具生命力的呈現狀態,與受眾體結成牢不可破的情感紐帶。由繪本改編的動畫電影更是以動畫特有的視聽語言豐滿了故事情節,鮮明了視覺形象的性格特征,使觀眾獲得全新時空建構的新奇感、簡潔飽滿角色塑造的親近感。國內動畫電影缺失一個視覺形象前期印象積累的培育過程,形象的塑造上呈現出內涵過于單薄、高文化內涵低辨識度的兩極分化局面,“親民”的視覺形象寥寥無幾。如何鍛造簡化有生命力的視覺形象是繪本和繪本動畫電影的制勝關鍵。
從心理學角度出發,人的視覺反應在一定條件之下會產生誘發性突變,借由一個形象的視覺感受對另一物體產生關聯性情感投射。例如看到破土而出的柔軟嫩芽,看到富有張力的曲線,于是,曲線本身被投射上類似的感受。凡·高中晚期的繪畫作品中呈現出強烈的主觀表現意識,他把具象物抽象簡化成動蕩的線條,用豐富的色彩和富有生命力的線條來表達個人強烈的主觀情思。曼羅·里夫與羅伯特·勞森合作的經典繪本《愛花的牛》中,有一頭極富個性主見的“佛系”公牛——費迪南,在特定歷史背景下它被看作熱愛和平友好的象征,創作者用黑色線條勾勒出不同角色的外貌和動作來表現出性格和別致的情境。2018年1月上映的《公牛歷險記》則在原作的基礎上對費迪南的形象做了進一步改良,我們仿佛看到西班牙阿爾塔米拉洞穴壁畫《野牛圖》生動地展現在我們面前。影片保留原作者為視覺形象塑造的獨特審美意向。將個人的主觀情思展現得淋漓盡致,角色形象更為細膩飽滿,正如片中刺猬姐弟形容的那樣“溫柔又可愛,就像黃油”。視覺感知在某種程度上是被動和即時的,面對視覺藝術作品,受眾群體特別是還沒有建構起完整、合乎邏輯認知習慣的兒童對視覺傳播的信息,是要求能在電光石火的瞬間迅速與視覺形象建立起情感關聯。
視覺形象是帶有創作者為其設定的清晰強烈的主觀情緒的,在造型藝術發展的歷史長河中,中國繪畫早有深入詳盡的研究,并呈現大量優秀的作品。特別在中國傳統人物畫的創作中,強調繪畫形象的真實并不是對于對象做簡單化、概念化的外貌描繪,必須把握對象的精神特征、風貌。顧愷之以“遷想妙得”一詞概括了有關這個問題的觀點,強調把自己的主觀情思遷入繪畫對象中,創造出浸潤創作者思想情感的審美意向,這種審美意象,由于精神特質已經被藝術家的思想所強化、所理想化,因此就有了更加感染人的魅力。[2]中國繪畫中存在大量經典案例可供創作參考,陜西咸陽永秦公主墓出土的石槨線刻《宮女圖》是一幅精彩佳作,畫中一位年輕嫵媚的宮女獨自佇立,拈花自賞,如癡如醉,人物姿態、神情生動有致,畫面布局精巧錯落,營造了一個幽靜清雅的環境,引動觀察者對墓主人生前生活狀態的無限遐想。潑墨人物畫鼻祖梁楷筆下的“潑墨仙人”,以一氣呵成的潑墨法塑造整體形象,用概括簡練的勾線法提煉局部細節,把一個憨態可掬、行事不羈的仙人形象展現在我們面前,審美意向性的大膽革新體現了梁楷玩世又悲天憫人的處世寫照。創作者主觀情思下的意向性視覺形象是藝術作品在被刻畫“第一形體”的同時被賦予“第二形體”審美本質的結果。繪本及繪本動畫電影創作之初,視覺形象的產生過程中能否依據此創作要義,立足作品想要表達的精神內涵進行“精雕細琢”成為提高作品辨識度并和觀眾形成牢固情感紐帶的關鍵。
三、以繪本圖像敘事互動關系為基礎的繪本動畫電影
兒童心理學家皮亞杰認為,知覺是以空間、時間、因果三者之間的關系同時成立為契機的。視覺藝術的形式效應是一個動態的交互過程,我們對事物的認知,是人的視覺和物象關系相互作用的結果。依據神經系統學的相關理論,大腦和視覺形象之間借由視覺皮層制造視覺經驗,形象在視覺空間中出現、變形和消失以及形象間的拼接組合的過程是視覺皮層綜合大量信息進行線索分析和找尋邏輯對應的過程。從視覺主體來看,視知覺是客觀物象的本體特征、生活經驗得來的視覺認同組建而成,是“所見”與“所知”互動的結果;從視覺對象來看,視覺效應的產生是視覺符號之間相互關系的結果。真正掌握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是建構完整意義上視覺審美效應的關鍵,繪本以及繪本動畫電影則是通過圖像敘事互動關系獲得相應的審美效應。其中,涉及對視覺符號的互動關系、故事發展的意向空間設計以及作品整體視覺節奏的研究。
繪本以及繪本動畫電影都是視覺符號的集合體,每個視覺符號都會按照故事發展的邏輯規律、主體間的互動、主觀視點的代入以及創作者強烈的個人喜好等各路軌跡發生發展,引導觀眾進入故事中心,感受作品傳遞的審美情感。對視覺符號的解讀就是對視覺形象意義的解讀,其中視覺符號的象征性可使特定形象成為串聯作品內在精神主線的關鍵。《公牛歷險記》中,“花”的形象貫穿影片始終,在情節發展的轉折點起到重要的引導作用,無論是小牛費迪南精心守護的斗牛場上的小野花、小女孩發髻邊令逃跑的費迪南感到安全的小花、山羊導師贈送的花形玩具禮物等,都使觀眾感受到強烈的對自由生活向往和追求的情感,這個視覺符號的成功使得角色更加栩栩如生。同時,視覺符號之間的關系分析成為推動情節發展的重要動力,在巴爾特的符號學理論中,提出視覺符號之間因為“心靈的共同性和共享性”可以在共同或不同的文化背景下感知到“彼此傳達信息的意向”。也就是說,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心靈可以借由特定意義的視覺符號彼此進入,獲得“共享精神世界”的情感共振。繪本是用一組講究連貫韻律的畫面講故事,制作繪本的第一步是做“版面設計”,就像電影的“layout”,故事內容能不能順利進入觀眾的內心,“layout”中所有視覺符號的互動關系是關鍵。繪本及繪本動畫電影最擅長運用的影視技巧之一是運用主觀視點,將鏡頭畫面的經營重點放在角色所看到的事物上,借著主觀視點將觀眾代入角色,形成觀眾和角色之間的有效互動,進而形成相應的情感投射。由蘇斯博士經典繪本改編的動畫電影《霍頓與無名氏》,通篇都讓觀眾不斷地在主、客觀視點的切換中緊跟影片發展的進程。特別感動于由霍頓借著微弱聲音的傳遞形成的想象中的“呼呼小鎮”的全貌和小鎮居民的生活日常,深深喚起觀眾對微小事物的關注,改變了對客觀世界原有的認知。這也是蘇斯博士最初的創作初衷,改變人們不僅僅是兒童認知世界的方法。中國動畫電影在某種程度上更多的是向觀眾展示著什么,觀眾看到的是一群視覺符號按照導演設計的軌跡在表演,沒有很好地考慮如何設計代入感,讓觀眾以切身的視角和感受去追尋事實的真相。
繪本及繪本動畫電影中的視覺符號不僅以其特有的視覺藝術審美特性傳遞著重要信息,而且會借由特定的設計產生意向性的空間效應。由克里斯·范·奧爾斯伯格繪本故事改編的動畫電影《極地特快》,影片開頭通過克勞斯找尋圣誕老人蹤跡的不同視點以及反光的器皿、透光的鎖眼等各種投射不同空間的視覺符號的精心設計,將觀眾快速帶入影片情境。此類設計產生“形有盡而意無窮”的作用。“形有盡而意無窮”,指的是視覺藝術心理中意向性視覺符號的運用能產生無限空間體量的變化,拓展藝術形式的感知力。例如,視線的方向是無形的,但它可以“占有”空間。中國傳統人物畫在處理人物之間的相互關系和表現人物的性格神態時,講究“晤對通神”,特別是在繪制群像時,不僅注重刻畫各個人物的不同神氣,更重要的是如何處理人物間的相互關系。顧愷之《列女仁智圖》中,經過對人物動作及眼神互動的設計,使畫面形象之間產生了自身的相互制約,限定了空間位置的關系。當畫面上起時,形成了一種可令人神游其中的空間境界。張萱《搗練圖》以巧妙的構思體現人物的心理狀態,畫中眾多人物借由相互交織的眼神,形成一張隱形的人物密切互動的關系網,使得畫面人物呼之欲出,動感十足。其中,有一個正對觀眾的搗練女的眼神直擊觀眾之眼,就如影視中“打破第四面墻”的技巧作用那樣,使得畫中營造的意向空間與觀眾所處的真實空間融為一體,令觀眾產生時空交錯之感。作品立足人的審美需求,不僅將視覺主體和視覺對象間的互動關系表現得淋漓盡致,更是通過精妙的意向空間設計提升了審美意蘊。
繪本動畫電影中,整部影片的敘事結構借助一個個視覺符號序列組的不同組合,按照不同基調的影片節奏,主題明確地將影片呈現給觀眾。心理學認為,節奏是人對感知事物過程中生理、心理和情感表達的內在需求,具有審美價值。視覺藝術不能直接體現節奏在時間上的連續,只能通過視覺符號有序地重復和排列得以實現間接的節奏感。視覺節奏主要由視覺主題、視覺符號序列組銜接的韻律、高潮節點控制,成功的繪本和動畫電影都出色地完成視覺節奏的設計任務,讓觀眾被看不見的“引線”指引,點燃情緒,最終在節點處獲得情感爆發。優秀的繪本和動畫電影都有一個共同的特征,都如同一棵樹干挺拔、枝杈分明、樹葉繁茂的大樹,單純的主題是“樹干”,順勢生長的情節是樹枝,豐富有情態的片段是樹葉。作品想要呈現的主題太多,故事就沒法集中,沒法精準地將有趣味的片段進行串聯。[3]正如影視作品中強調主題剪輯,所有鏡頭銜接強調主題的和諧、延續,這種過渡常常讓我們能夠很有邏輯地從頭到尾看一個故事。主題明確的基礎上,視覺符號序列組如何銜接也是至關重要的環節。動畫影片中視覺“節奏”透過韻律起伏,創作者可以引發觀眾的情緒,可以讓觀眾在一個安排得當的情緒空間中,張弛有度地釋放情感,能更好地感受鏡頭豐富的變化。同時,高潮節點的設計又讓影片在敘事過程中,彈奏出最強音讓觀眾積蓄的情感找到突破口。根據宮西達也繪本作品改編的動畫電影《你看起來好像很好吃》中,小甲龍寶寶“很好吃”與被食草恐龍養大的霸王龍哈特之間父子情深,在傷痕累累的“很好吃”說出“我們的賽跑我沒有輸,從今以后可以永遠在一起了吧”的時候,觀眾的情緒被推至頂點,深深地被這份對親情的執著所感動。視覺藝術的節奏控制是以事件內在發展規律和受眾的心理接受為依據的,在動畫電影的創作過程中,當所有的鏡頭節奏都到位時,才能給觀眾帶來最好的情緒和感受。
四、結 語
從受眾審美心理的角度來看,繪本作為一種有意味的視覺表現形式,以其富有生命力的視覺圖形符號、充滿積極互動的圖像敘事呈現給觀眾無窮盡的認知和想象空間。視覺藝術心理依賴視知覺探索、組織和感受視覺符號及影像傳播,創作主體以及受眾接受的心理研究是藝術創作緊密依托的基礎。創作主體若能將繪本中的視覺藝術審美特質轉接到影視作品的創作中,將能更好地凸顯視覺主體形象的認知度、提高影片敘事結構的掌控度,進而加大受眾群體的接受度。立足民族文化藝術的傳承,對中國傳統繪畫圖像敘事的深入研究則是為國產動畫電影發展過程中尋求原創素材和創作方法提供有效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