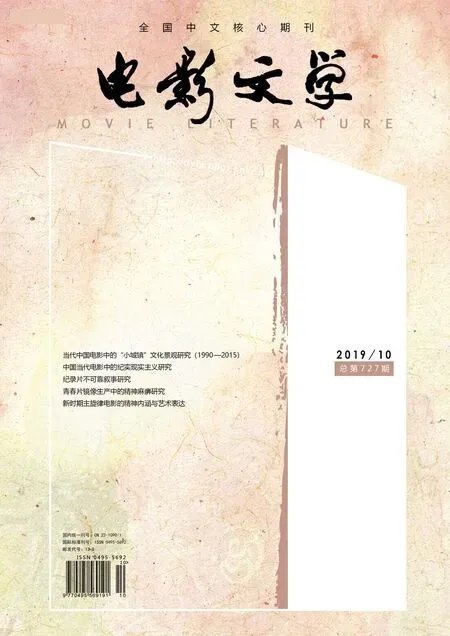“宿命”下的身份尋求和價值追問
陳 彧 (湖北工業大學 外國語學院,湖北 武漢 430068)
電影《別讓我走》改編于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石黑一雄的同名小說,2010年由頂級MV導演馬克·羅曼尼克搬上大銀幕。影片上映后獲得諸多好評,其藝術影響力得到高度認同:獲第23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影片題名獎,第10 屆鳳凰城影評人協會獎三項提名。綜觀《別讓我走》的敘事設置,電影立足于克隆人特殊群體,在對克隆人定制型人生軌跡的敘事中,制作者突破科幻電影“自由主旋律”模式,將對宿命論主題、身份尋求和價值追問等內容的思考通過電影形式藝術地展現了出來。在細膩、悲情、發人深思的敘事中,在美麗、傷感的電影畫面以及演員高超表演的推動下,電影流暢地利用多種敘事模式,構建一個看似平靜實則暗潮洶涌的獨特的克隆人世界。
一、對科幻電影自由主旋律的突破
科幻電影通常以描寫神秘現象、超能力、離奇驚險的故事為主體內容,以嚴密性、邏輯性和趣味性為主要特色,打造打動觀眾并引起共鳴的自由主義主旋律,如《機械姬》和《西部世界》等人氣甚旺的科幻影視作品,講述的都是關于爭取自由和逃亡的故事。《機械姬》中的智能機器人為了擺脫人類的奴役,騙取人類信任并設計囚禁人類工程師,隨后逃跑并成功融入人類社會。 《西部世界》中人類通過改裝真人,制造出供人類消遣和任意屠殺的娛樂工具 “人造人”,當自由意識被喚醒后“人造人”開始了有組織有計劃的逃亡[1]。不同于其他同類題材電影,《別讓我走》突破科幻電影弘揚自由主旋律的藩籬,片中的克隆人遵循“長大—捐獻器官—死亡”這個設定型、程式化和工具性的存在軌跡:克隆孩子生活在幽靜的寄宿學校,看上去他們的生活似乎跟真實人類無異,經歷著青春期的躁動、愛戀、孤獨和分離,成年后的克隆人接受命運的安排,開始捐獻器官直至生命終結。
爭取獨立自由是科幻影視作品最常見的主題,逆強大獨立自由主潮流而行的科幻小說《別讓我走》一經出版便驚煞世人。電影對小說主題的恪守正是用“偉大的情感力量,讓我們跨越了虛擬與現實世界的深淵”(1)2017年10月石黑一雄獲取諾貝爾文學獎時瑞典文學院的頒獎詞。,給觀眾留下思考:逃離是克隆人的出路嗎?然而整部電影都在傳遞這樣的信息:克隆人的認命,無計可施,世界的無處遁逃,個體生命的默然反抗和對尊嚴的無力呵護。電影中湯米、凱西、露絲并未選擇逃跑的設定是最為高明和貼近現實的處理。在既定的存在目的和功能面前,克隆人的逃離毫無意義,逃與不逃沒有任何區別。在電影故事的預設背景里,人類嚴格控制著克隆人的思想:從小灌輸逃跑沒有好下場、捐贈器官是一種使命的邏輯。在無數次被洗腦之后,凱西他們習慣并接受被設定的身份。人類對克隆人的認知更是從根本上毀滅了克隆人的自由意識,克隆人是被創造出來的、沒有靈魂只能提供器官的類似于怪物的人造生物。電影里夫人見到克隆孩子們時流露出“竭力壓抑那種真正的恐懼,唯恐(他們)之中的一個人會意外地觸碰到她……她怕(他們)就如同有人害怕蜘蛛一樣”[2]39的表情;當湯米等一行克隆人在市中心尋找本尊(2)“本尊”指制造克隆人所需要的DNA的提供者。時,西裝革履的人類拋來鄙夷眼神;凱茜和湯米與夫人再次見面時,夫人 “一下變得僵硬起來——就像有兩只巨大的蜘蛛向她爬去”[2]276的反應。所有這些讓克隆人意識到在人類眼里他們不過是無靈魂的物品,而自由跟物品無關,何況戴在手上的電子手環在無間隙地監控著克隆人,讓他們無所遁形。影片里年輕克隆人的死亡剝離了凄美和浪漫,成為人類對其程序化設置中的一個步驟,猶如格式化硬盤,不帶任何感情色彩。電影對自由主旋律的舍棄和對宿命論的順從讓觀眾陷入深思:自詡最智慧的人類缺乏對其他非人類生命個體的尊重,克隆人面對宿命的無奈與觀眾面對生活中諸多問題時的束手無策構成強烈的情感共鳴。
二、對宿命的逃避與反抗
《別讓我走》給觀眾帶來強烈震撼的是對克隆人定制型存在意義、程序化生命歷程和格式化生命結局的敘事設置。生活在寄宿學校的克隆孩子們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誰、來自哪里,卻被警告保持健康是最重要的頭等大事。六七歲的時候開始了解并學習接受克隆人身份,在洗腦式信念灌輸后獲得自我認知:捐獻器官直至死亡是與生俱來的責任和命運,長大后他們不從事任何工作,只須等待開始捐獻器官,在第三或第四次捐獻時失去生命。
電影片頭顯現的系列DNA數據,把觀眾帶入醫學技術獲得突破性進展的科幻時代,那時人類壽命已經超過100歲,器官移植可以治愈任何疾病。電影語境告訴觀眾一個既成事實:人類創造克隆人的唯一目的在于獲取他們的器官,為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提供供體。接著故事在女主角凱茜.H的回憶式講述中慢慢展開: 英格蘭鄉下綠樹草場的原野風光、青春的人物、淡雅的服飾最先給觀眾文藝片的錯覺;隨著凱茜舒緩平靜的敘述,慘淡故事逐漸展開,壓抑和灰暗的主基調讓觀眾開始認真對待克隆人命運的科幻主題;當電影前設問題的謎底最后在凱茜和湯米拜訪夫人的對話中揭開時,當故事在湯米的離世和凱茜即將開始的捐贈人結局中落幕時,觀眾愈發強烈地感受到克隆人悲劇命運的無法逃避性[3]。影片在貌似簡單的形式下掩藏著復雜的內涵,它將克隆人難以名狀的困惑和經過洗腦教育后的行為完美地整合到故事情節之中,以幻想替代現實,以尋找愛情來宣泄心中的壓抑。露絲在第三次器官捐贈前把死亡當成擺脫痛苦的談話內容;面對死在手術臺上的露絲,醫生冷漠地關掉標示生命終結的心電監護儀,電影鏡頭轉向玻璃門外毫無表情地觀看這一切的凱西;凱西和湯米通過多種努力,克服各種困難企圖獲批延期捐贈器官,得知緩捐只是一場謊言的湯米站在黑夜中無望地哭吼并最終死于第四次器官捐贈的結局;在富有悲劇色彩的主題音樂烘托下,凱西站在黃昏的晚風中凝望黑爾舍姆學校舊址,影片在凱西平靜的告白中走向劇終:她已經接到捐贈通知,一個月后開始第一次捐贈。然而在寧靜中結束的電影故事透露出的悲涼讓觀者久久不能平靜,對凱西他們在宿命面前的無力反抗和消極接受充滿了憐憫和不安。
三、徒勞的身份尋求和價值追問
小說《別讓我走》節奏緩慢,凱茜的回憶并沒有嚴格遵守時間順序,但瑣碎的敘述逐漸為讀者解惑答疑。克隆人關于“我是誰”的謎底在拜訪夫人的對話中揭開,克隆人用藝術和創造力證明愛情,用愛情贏得生命延續的努力是一廂情愿的臆想。電影借助藝術化處理,有效地折射出克隆人的身份尋求、價值追問等倫理訴求的主體愿望。
電影《別讓我走》的片名源于片中多次響起的同名歌曲。少女凱茜抱著枕頭跟著音樂的節奏在宿舍起舞,視覺和聽覺的疊加讓觀眾對歌曲的理解同步于凱茜: 有一個女人,別人告訴她終身不能生育,她終于有了小孩,她把孩子緊緊抱在懷里,害怕被拆散,所以她一直唱著“寶貝,寶貝,別讓我走”。枕頭是嬰兒的象征,被人類制造出來的、不具備孕育生命能力的凱茜是悲哀的,音樂的運用把電影帶入一個高潮,實現電影人物和觀眾的情感共鳴。
那盤錄有《別讓我走》歌曲的卡帶在影片中多次出現,串起三位主人公的感情經歷:磁帶莫名失蹤,露絲盡力幫助尋找,這是少女友誼的見證;成年后湯米幫凱茜尋找并購買一盒相同的磁帶,這是愛情的見證。珍藏—丟失—尋找的過程折射了克隆人身份倫理的臆想和幻滅:失去磁帶是外力對臆想的撕裂,重新獲得暗示著凱西和湯米在友情和愛情的支撐下獲得逃避宿命的意愿,夫人殘酷的現實告白徹底擊毀他們的奢望與努力,回歸到器官捐獻者的本位。誰能“別讓我走”?這是人類科技進步帶來的倫理困惑,露絲、湯米的死亡也許能給觀眾提供答案。
身份和存在價值是人之為人的根本。有著與人類相同的外貌,并被證明具有思想、創造力和靈魂的克隆人卻不具備身份。電影里的克隆人是沒有姓氏的,他們是凱茜·H、湯米·D 。人類社會里姓氏代表個體的獨特性和他與社會、歷史、家族的聯系,克隆人編碼式姓氏是人類對他們物化處理的結果,是對他們生命起源和社會身份認同的阻斷。通過社會信息的附加,這種姓氏如同烙在奴隸臉上的烙印,讓克隆人成為具有“馴服的身體和臣服的主體”的社會無意識的存在[4]。即便如此,克隆人仍然期望通過尋找“本尊”獲取前世今生的蛛絲馬跡。電影藝術地處理了露絲尋找“本尊”時的場景:露絲和朋友雙手擋住眼側余光,臉貼玻璃窗好奇而羨慕地張望在旅行社里工作的人類。這個畫面與《弗蘭肯斯坦》中怪物透過玻璃窗窺探普通人家的生活情節構成互文。雖然電影畫面中的克隆人青春靚麗,但自然人拋過來的鄙夷眼神告訴他們在人類眼里自己只是源自渣滓、歸于廢物的醫療用品。當露絲在色情雜志上找到自己可能的“本尊”之后,她真正明白克隆人本來就是照著渣滓做的,所以才能被輕易拋棄,這個世界從來都沒有他們的位置。他們只是有用器官組合而成的肉體器件,供人類任意拿取,捐獻健康器官是他們存在的唯一功能。被允許的性生活是為了促進器官發育,卻不具有繁衍后代的能力,這是對克隆人無根性、無繁殖性、徹底工具化最為有力的表達。然而主人公凱西在宿命面前采取的不卑不亢的態度中也夾雜著淡淡的、幾乎被埋沒的向上的力量——謙卑而自我地向前走;露絲在第三次器官捐贈前平靜地討論死亡;湯米在得知所謂延緩捐贈時間的謊言后表現出來的憤怒和悲傷讓觀眾看到克隆人對建構身份和追尋自我價值方面的無力嘗試。這是電影留給觀眾無限悲哀后的一絲安慰。
四、結 語
石黑一雄文風細膩而優美,作品表現出國際化的文化特質,蘊藏著極強的穿透力[5]。電影《別讓我走》通過恰當的敘事方式,通過演員的表演、音樂和畫外音的運用、鏡頭的交替給觀眾帶來直接的視聽感知,在壓抑、絕望而又略帶唯美特質的電影語境里,把克隆人被出生、被沒有前途、被捐獻、被死亡的悲催命運推送給觀眾。透過凱茜凝望黑爾舍姆那片草地時的留戀眼神,觀眾感受到克隆人對生命、對世界、對彼此的愛與依戀的終結。《別讓我走》不同于其他討論克隆人話題的電影作品,主人公們默默承受悲慘宿命,這種電影主題引發讀者對“我是誰,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的哲學思考,以及對當今社會有關人的創造力和靈魂作用的反思。慶幸的是凱茜在片尾提出“我們的生命,與那些我們所拯救的生命,究竟有什么不同”的質問,讓觀眾在壓抑中看到依稀的希望:未來的世界或許能在平等地尊重一切生命形式的過程中變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