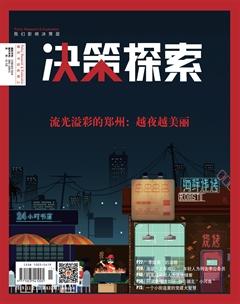文化遺產保護,如何讓城市更有溫度
柳森
日前,上海市民口中的“老市府大樓”保護性改造項目正式開工,計劃于2022年局部對公眾開放。在討論如何對該建筑群進行“保護性綜合改造”時,設計團隊確立了“讓這棟建筑重回城市,成為老百姓能走進來的城市社交場所”的宗旨,讓很多市民印象深刻。但具體如何做,才能讓市民們樂于“走進來”?除了建筑設計上的匠心,包括綜合管理、動線設計、服務細節等在內的“軟件”如何跟上?
上海社會科學院應用經濟研究所文化創意產業研究室副主任曹祎遐,近階段正在對英國多處歷史建筑、文化遺產與公共文化機構進行探訪,這讓她對上述問題有一番自己的思考。
共籌 共建 共享
為惜物之心架一臺永動機
問:考察文化產業大國英國在創新創業和文旅融合方面的歷史經驗與前沿探索,是你此行的主要任務。據說,考察伊始,最先讓你深受觸動的,就是英國在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開放性與公共性。能講講他們是通過哪些具體做法實現這一點的嗎?
曹祎遐:有一個現象,可能很多到英國或歐洲其他國家旅行的人都看到過。在很多歷史建筑、文化遺產的現場,都設有一個捐贈箱。這個箱子設于大部分到訪者的必經之路,它讓人“很難錯過”卻絲毫不突兀、不莽撞,與整個場景融為一體。它的形式(如箱體、顏色、材質、文字說明)幾乎沒有定式,但大都莊重、簡潔,讓瞥到它的人會自然而然地放慢腳步,走到跟前去看一看。
以前去英國或歐洲其他國家旅行,我只記得經常會看到這樣一個箱子。但這一次,因為停留更長時間,又高密度地到訪此類場所,我才意識到,原來這個小小的捐贈箱,不僅是大部分歷史建筑、文化遺產的標配,還是英國早就已經開啟的文化遺產“共享模式”中的一個關鍵環節。
這一模式以推動文化遺產保護“共籌、共建、共享”為宗旨,所以,如果游客有心,可以看到所有捐贈箱周圍,都有關于這些捐贈“到哪里去”“將如何被使用”的說明。有的甚至會詳細地羅列上一年度的捐贈情況,以及整個遺產一年來的運營成本、維護成本、公眾捐贈之外其他資金支持的來源、數額和去向。
這些數據和說明,傳遞著一個強烈的信號:文化遺產來之不易,良好的保護與開放背后運營成本極高,但因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籌資而獲得了很好的愛惜和支持。言辭之懇切、細節羅列之嚴謹,我想,哪怕是對文物保護沒有任何專業知識的人讀了,也會感到一股敬重、愛惜之情,并且會進一步懂得,這一切并非“天然的恩賜”,而是需要社會成員共同參與,一起愛護、疼惜。一個小小的箱子,不僅聯結著政府給予文化遺產保護的多種渠道基金,也是對民眾實施文化遺產保護教育的即時工具。
當然,光有理念上的傳遞、感化還不夠。作為運營者,會首先自覺地以精細、周到的服務回饋所有到訪者。比如,為了讓參觀覆蓋全人群,以無障礙設施為代表的、具有很強公共性與開放性的服務設施都布設得非常到位。考慮到“單身社會”的到來,有的場所甚至為方便參觀者攜寵物進入創造了條件,只為能夠創造更多可能,讓社會各界成員都可以方便、舒適地迅速融入整個參觀環境中。
在我們研究文旅融合時,文化創意產品的“復購率”是一項關鍵指標。它能夠反映出主創團隊是否具有持續的創新能力,為受眾創設出值得一來再來的理由。同理,一個充分重視營造“共籌、共建、共享”氛圍的公共文化場所,才能吸引公眾不斷地到訪,將之視為個人文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問:對于參觀者來說,這樣不僅能感受到自己是受益者,還能從自己出發,為這個項目的可持續發展做一些什么,這樣的感覺很好。
曹祎遐:是的。這一模式使得到訪者從歷史建筑、文化遺產保護中受益更多,對共籌、共建、共享模式的認同也會更進一層。自覺愛護、力所能及地資助,成為一種主動選擇。這樣一來,整個遺產保護的資助、支持系統,就進入了良性循環。而對于普通公眾來說,他們會高度認同,文化遺產保護不單單是政府管理部門的事,也是社會方方面面的事,尤其是自己可以參與的事。
坦白來說,如果所有維護、資助、服務都由政府來做,不僅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后期管理和服務綜合改進上也會力不從心,公眾還不一定認可,最終很可能會事倍功半。
志愿者講解
是一項重要的“社會工程”
問:在歷史建筑、文化遺產的開放性與公共性方面,還有什么細節設置,可以給我們以啟發?
曹祎遐:我到訪的多處文化遺產都是以社區公共空間的形式開放。能否成為社區公共空間,從附近的居民去得多不多就能看出來。在不少歷史文化場所,經常可以看到周末舉家來遛娃的家庭。在一些人流容量較大的花園、草坪,還可以看到一些家庭搭帳篷來野餐。
這一方面是因為他們有親近自然的傳統,另一方面能看出當地民眾即便在野餐、玩耍的過程中,也非常注意對周邊環境的愛護。這應該是公眾與場地管理者基于互相信任、彼此體諒,長久互動下形成的結果。這不是管理者單方面足夠包容、足夠用力去“管教”,就可以實現的。
另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細節,是有一次我參觀一座都鐸時期的建筑。那里的志愿講解員年齡涵蓋20歲至80歲,有的來自知識界,有的具有文藝表演特長,有的是當地一些文化團體的成員,也有一些自由職業者。即便在免票日,提倡游客利用參觀手冊自我導覽,每個房間仍有一名志愿者對參訪者的問題予以解答。這種做法特別有人情味。
為我做講解的志愿者告訴我,這里有相當一部分志愿者是非常了解當地歷史、文化的老年人。他們對自己的這份“工作”非常熱情。他們不僅在意這份“工作”背后的傳承性,可以將一些有關過去的細節更好地介紹給年輕一代,更熱愛這份“工作”帶給自己的價值感,很愿意通過為他人貢獻自己的知識和時間來發揮余熱。這一類情況,目前在志愿講解員隊伍中越來越多,大概可以占到總人數的一半。
如果仔細去聆聽,還會發現,這里的講解大多是對話式的。講解員會先了解你來自哪里、對什么感興趣,然后決定自己講解的切入點。這就不是一種單純的介紹性講解了,而是與你的知識、生活背景進行鏈接。這跟背稿式的講解差別很大,不會毫無來由地“塞”一堆東西給你。給聽眾的感覺是不刻意、不生硬,以一種跟人相處的方式來溝通和交流。
問:現在上海很多公共文化機構也很注意建立自己的志愿講解員隊伍,激發了很多熱心市民的主觀能動性。但這一類組織尚且存在志愿服務時間比較集中在周末、志愿者隊伍可持續發展能力較弱等問題。
曹祎遐:這確實是一個問題。我之前接觸過的老年志愿者素質都非常高。我們可以認為這是當地國民素質和經濟實力的體現,但我也能夠看出來,他們的志愿講解行為由來已久,是不斷嘗試、練習、積淀的成果。
畢竟,一段成熟的講解是沒有辦法通過培訓來速成的。另外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正因為這些講解員比較年長,很多是退休人員,所以他們的閑暇時間更多。因為年長,相對而言,他們更靠譜、更守信,確定下來的志愿服務時間一般不再輕易去改動。
我之前在一處具有幾百年歷史的建筑中遇到一位年長的講解員,其祖輩就作為居住在這里的后人曾為該建筑提供志愿講解服務,一直堅持到80多歲離世。如今,這位老人也在這里繼續為參觀者做講解,并將此視作自己的使命。
據我所知,也有一些第三方團體專門從事歷史建筑或文化遺產志愿者管理工作。為了讓志愿服務更好地持續,第三方團體除了很細致地為這些志愿工作服務,還會去挖掘志愿者的故事、記錄那些因志愿服務而發生的故事。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把志愿者隊伍當作一個有凝聚力的團隊去營建,也為保持志愿者的工作熱情積極助力。
在動線設計中
實現專注與開放的平衡
問:現今,國內在各種文化機構的建筑和室內設計上,都開始注意到“動線設計”的重要性,即做好各種功能與展示之間的過渡與銜接,既呈現好的內容,也照顧到參觀者包括步行、瀏覽、生活需求在內的各種體驗。但真正實現得好的案例還不多,總覺得有太多的細節需要兼顧,顧此失彼的狀況經常發生。
曹祎遐:這方面,有兩次參觀讓我印象深刻。一次是在利物浦中央圖書館,一次是在英國國家鐵路博物館。
歐洲的公共文化設施大多是“舊瓶裝新酒”。外表看著是有歷史感的建筑,里面卻是現代化的設計,符合人性化的需求。
如何處理好新與舊的關系,實現自然而又別具一格的過渡與銜接?利物浦中央圖書館創造性地將旁邊一座歷史建筑的內部打通,變成了專門的“探索”主題區。這個區域既是公共信息發布的空間,也是親子閱讀的場所,很符合這個區域“探索”的概念。通常,在沒有特別的主題信息需要發布時,這里就是一個功能完備的親子閱讀空間。當發布需求生成時,這里在布局上幾乎不需要做什么改動,就能適時適景兼容各項主題發布活動。這樣一種集成復合的空間利用方式,有利于空間價值最大化,也讓這個空間在各個時段都匯聚起充滿生機的人流。
英國國家鐵路博物館的參觀游覽動線則突破了傳統博物館的展示方式、格局與形態,在偌大的空間中看似隨意地擺放各類列車車廂,實則呈現了不同年代、不同技術、不同作用的鐵路運輸功能。人們在中間可以隨意穿梭,甚至在極具歷史感的列車車廂中享用美食。在該博物館的二樓,有鐵路藝術作品區、閱覽區和資料查閱區,形成一個小小的知識空間。
在這樣一個多重線索交織的空間中,你并不覺得一不小心會就迷失其中,而是在各種完備的標識導覽中,順暢地領會到整個展覽的幾條核心線索。隨便怎么逛,都有新的發現和收獲。
很多人也許會以為,實現這一切的背后是一種善于集成和關聯的智慧。但我此番體驗下來,一個是感受到了設計者對參觀者體驗的重視,比如以參觀者的步行和觀覽流暢度為要。另一個感受是,設計者不能太貪心,在設計展覽伊始,就應當明確自己的目標受眾是誰,是全年齡、全人群,還是部分文化或專業訴求較高的受眾。一旦把參觀人群進行細致分層,就能確立展覽主要往哪些方向或細節使勁,也可以知道不同板塊的內容如何在同一時間段完成不同類型觀眾的分流。明確了上述幾點后,再梳理主題下的邏輯線索、安排展覽各塊功能的聯動或對比,整個參觀現場就會形成一種有活力的秩序。
問:也就是說,在動線設計的過程中,要對展覽或場館的核心人群有所界定,而不是貪大,希望以一種一勞永逸的方式,把所有人都服務好。
曹祎遐:沒錯。這樣一種對展館核心使命與核心人群的專注,與堅持展館本身的開放性并不矛盾。在全社會的范圍內,與其讓各類場館重復性地服務大眾,不如大家各美其美、資源互補。
在英國國家鐵路博物館,幾乎看不到布設于玻璃鏡框中的展品。整個展館在一個開放性的空間里,一眼望去,幾乎一覽無余。這種對展覽“開放性”的堅持,恐怕是根深蒂固的。
英國國家鐵路博物館還有一個設計很能反映出其對公眾的態度。可能也是因為鐵路題材的關系,該館展品本身體量大,展覽庫存量也大。于是,在該博物館展廳的一角,把倉庫的一部分直接銜接到了展廳中,成為展覽的組成部分。
這個空間既延續了本身的倉儲功能,又是一個別具一格的展示區。眾多藏品直接在架子上陳列。不同架子之間又巧妙地被擺成了一個歐洲人喜聞樂見的迷宮樣式。在現場,很多孩子開心地在“迷宮”里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戲,身邊擺著精心陳列的展品。
這樣一種布展形式,既結合了美觀與功能性,也給人以靈活、生動的感受。最重要的是,由此帶給參觀者的信息量非常大,動靜結合的形式也讓參觀者更容易滿足。在此過程中,展館本身的開放態度讓人印象深刻。
誠如我們經常說的,一個孩子在兒時如何被對待,長大后就會如何去對待別人。同理,一個歷史建筑、文化遺產對待孩子的開放態度,也是這個場所對待公眾、對待文化傳播的態度。此間所有的用心,會被一代又一代人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