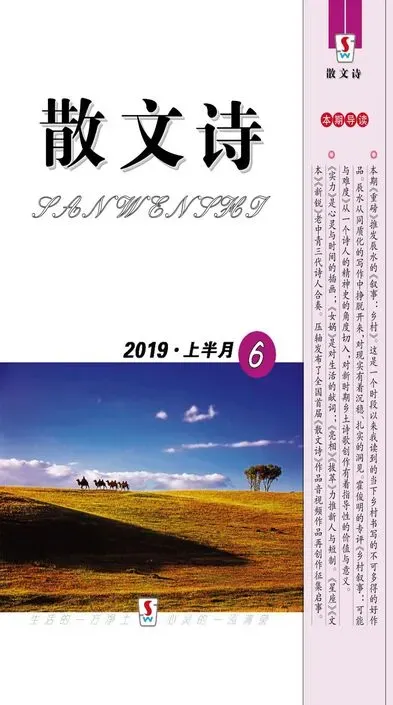世界散文詩:在思想的隱喻里展開或釋放(二)
◎黃恩鵬
一、經典文本創作的精神向度
恩斯特·卡西爾(Enst Cassirer)在談及審美情感在藝術創造的作用時說:“在這個世界,我們所有的感情、本質和特征上,都經歷了某種質變的過程。情感本身解除了它們的物質重負。我們在藝術中所感受到的,不是哪種單純或單一的情感性質,而是生命本身的動態過程,是在相反兩極——歡樂與悲傷、希望與恐懼、狂喜與絕望——之間持續擺動的過程。使我們的情感賦有審美形式,也就是把它們變為自由積極的狀態。”①審美情感,讓詩有了一個非同尋常的存在狀態。這個狀態,是由語言來承擔的,更是附就在時代命運的轉寰之中的狀態。在詩人看來,詩文本應體現愛、悲憫、勸誡、昭示和人性的自剖,以及對于人本精神向度的追尋。這些,都將為散文詩創作之詩意鍛造,提供一個可以參悟生命本質存在的理想出口。
我讀世界散文詩,就是有著這種感受。縱觀偉大的作品,沒有哪一部不是高貴的精神與深重的痛苦相連。社會性與天性之間的對立,鑄造了作家的獨創性。在古老中國也同樣如此,那炎炎烈日下,一位健美的漢子奔逐的身影,他是孤獨的、虛幻的,也是唯一的、不滅的雕像;他是初出茅廬的年輕人,也是執著于目標的俠士。他借助閃電的燃燒,將自己定格大野之上。我們不能說他只是中國的,他是世界的。我們讀世界散文詩,也不能說它是“別處的”,它同樣屬于我們民族自己的。“精神性質”,讓作品有了一個存活和傳承的理由,也是作品的巨大魅力所在。它決定了一位作家或詩人能否成功的關鍵。但也許,就詩人生存環境而言,還存在這樣那樣的窘境。但存活的生命,必須是詩性的和精神的。
詩性與本性相融,便有了不可撼動的情懷。心靈的溝通,愛默生的解析也許更為直接和準確:“靈魂的每項許諾都有無數的履行手段,它的每一種歡樂,都成熟為一種新的需求。無法抑制、隨意流動、永向前看的天性,在最初的善意中已經提前表現出一種在其普遍的觀照中必將失去特殊關注的仁慈。”②這種“靈魂的許諾”“最初的善意”“特殊關注的仁慈”,在一些作品中有所體現。如魯文·達里奧的《復活的玫瑰》、塞薩·瓦葉霍的《骨骼點名冊》、安德烈·紀德的《大地的糧食》、泰戈爾的《吉檀迦利》、紀伯倫的《先知》《沙與沫》、赫·布羅克仁的《海的墳墓》、希梅內斯的《四月詩情》、屠格涅夫的《鶇鳥之一之二》《大自然》、東山魁夷的《與風景對話》等等,都在作品中貫注一種生命之本體或與自然相親相融的仁慈力量。
但是,黃鐘毀棄,瓦釜齊鳴。在我們身邊,傳統的價值觀正在失落。文化意義上的精神性質,正在逐漸遠離我們而去。在迷惘的失落中,我們,誰能不怕險惡,為現實痛伐那些丑與惡?誰能心存感恩,為這個大地做些什么?誰能理解巴勃羅·聶魯達所說的:“當詩人們關在研究室里的時候,人民在用膠泥、土地、河流和礦山來歌唱。他們培植了迷人的鮮花,譜寫了出色的史詩,炮制了小說,描述了災難。他們歌頌了英雄,捍衛了權利,為圣人加冕,為死者痛苦”③這一追求人文自覺的呼聲?他的《英雄》是這樣的——
我發現了我的英雄,正好在我去找尋他們的地方。仿佛是我把他們裝在我的憂慮里一樣。起初我不知道怎樣識別他們,如今,熟悉了生命的布局,我已經懂得給他們賦予本來沒有的性質。可是我又發現自己被這些英雄壓迫得太累,只好放棄他們。因為我現在要的,是在橫逆之下傴僂著的人,是挨第一下鞭子就尖叫的人,是把人生看作沒有陽光的潮濕地窖、不會笑的陰郁的英雄。
可是,如今我找不到他們了。在我的憂慮里充滿了年老的英雄,昔日的英雄。
聶魯達可以說是擁有讀者最多的拉丁美洲詩人,他20歲時就寫出了《二十首情詩和一首絕望的歌》,且出版同名詩集。到1961年,這37年內重印了不知多少次,印刷達100多萬冊。之后更是多之又多。聶魯達受波特萊爾和蘭波的影響較大,常受爭議的《大地上的居所》第一、二卷最為明顯。后來他又放棄了一位法國詩人思想對作品的滲透。因此,他還風趣地說:“法國衣服不適合我的身材”。他的作品澄凈透徹,寫史詩,也寫別人從來沒寫的日常。《回憶錄》中,大量的作品都是散文詩。
這章《英雄》,寫得就是別具一格。開始的“我把他們裝在我的憂慮里一樣”與結束的“在我的憂慮里充滿了年老的英雄,昔日的英雄”形成了“圓環”。英雄不是某種模式認定的那種標準。在詩人心中自有著另一形象。“我發現了我的英雄”是一種獨立的思考、與英雄模式不同的形象。他們,讓我“懂得給他們賦予本來沒有的性質”。這個“性質”,是什么?從尋找,到放棄,是因為英雄的古舊與高不可攀。是英雄的固有的那種“國家模式”,它離大眾實在太遠,讓人感覺到“壓迫得太累”,不得不放棄。這不是“我現在要的”。我現在所想要的,“是在橫逆之下傴僂著的人,是挨第一下鞭子就尖叫的人,是把人生看作沒有陽光的潮濕地窖、不會笑的陰郁的英雄”。打碎英雄的神圣,成一個有血有肉的凡者,這其實并不難,難就在內心該如何界定英雄的標準。那離得太遠的,并不會印證心靈里的真切的有血肉、知道切膚之痛的生靈而不是一種雕像式的英雄。從鑲嵌在句子里的詞義——“找尋”、“憂慮”、“識別”、“賦予”、“放棄”,可以看出詩人情感的起伏,為接下來的自己內心里的“英雄模式”,做出了很好的詮注。
如果說聶魯達的坦然面對,還不足以讓讀者了解他的思想,那么,他在晚年寫的回憶錄,卻足以說明他對于祖國和人民的一種情感,其創作的精神向度也就成了一種追求了:“第一批子彈射穿了西班牙的六弦琴,當噴出來的不是音樂而是鮮血時,我的詩歌便像幽靈一般在人類受苦受難的街心停駐,并開始沿著一股根與血的激流升騰。從那時起,我的道路與大眾的道路匯合了。我頓時感到自己從孤獨的南方走到了人民的北方,我愿自己卑微的詩歌代作劍和手帕,為人民揩干凈沉重的苦難的汗水,向他們提供一件爭取面包的武器。”④
聶魯達大量的作品,反映了拉丁美洲的歷史。而“義務與愛情,是我的兩只翅膀”(《海濱之花的頌歌》)。義務,讓聶魯達有著言說不盡的心聲。他的作品,無論是詩歌還是散文詩,都是大史詩和小史詩,它反映了詩人從空虛的個人主義者變成被壓迫者的代言人的轉變過程。這章《英雄》就是這種轉變過程的反映。他的語言的精神指向是巨大的,石頭和語境,泥土和方向,都在作品里呈現它閃光的東西。他的許多作品,將拉丁美洲大地的山川、景物人格化,并巧妙地運用歷史典故,表現拉丁美洲人民渴求解放的迫切心情。
再如他的短章《火車頭》:
那勁,那麥子氣息,那繁殖力和哨聲和吼聲和雷聲!打過谷,撒過木屑,采伐過樹林,鋸過枕木,切過木板,噴過煙,油漬,火星,火焰,發出震動大草原的呼哨。我喜它,因為它像惠特曼。
全章僅84個字,用了諸多個意象——麥子、哨聲、吼聲、雷聲、谷、木屑、樹林、枕木、木板、煙、油漬、火星、火焰、大草原、呼哨,等等,幾乎概全了的生命體征,來描述火車頭的力量,當這些力量混在一起,就代表著整個大地的力量。它就像詩歌的號召力一樣。這種號召力像什么呢?像詩歌。但是,有哪一位詩人的詩歌能擔當起“引領”的重任呢?只有惠特曼!是詩人最喜歡的詩人。如果說前面一連串的抒情和贊美不足以表達為什么喜歡的理由。那么,最后的一句來得卻是突兀、筆鋒犀利而又富于差異!美國文化精神象征的惠特曼在聶魯達的心里總是一個有著“繁殖力和哨聲和吼聲和雷聲”的火車頭形象。正因如此,他的詩《我自己》與惠特曼的《自己之歌》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可以說是延續了惠特曼的精神指向與生命情懷。
聶魯達不是形式主義者,創作的方向亦不是為了自我抒寫,而是一種表達思想銳利的方式和手段。因此,他從不過多注意語言本身,而是以現實為精神指向的標注,始終描準現實,來揮灑筆墨。無論是主觀的、客觀的、個人的、社會的或者自然的現實,都是如此。他的語言本身,是傾向于現實社會、國家、集體,而不是他個人;不過是一種準確或者近似、清晰或者朦朧地表述現實的符號。最終目的,還是展示這個國家隱藏著的精神氣度。聶魯達要讓自己的詩成為武器,改造世界與現實人生。他在寫作五百行長詩《馬丘·碧丘之巔》時說:“在到達祖國之前,我路過秘魯,來到馬丘·碧丘的廢墟。因為山區沒有平路,我們騎馬來到這里,從高處眺望被安第斯群山包圍著的石建筑物。白色的霧氣從大河上裊裊升起,我顯得非常渺小,感到自己也曾在這里挖過壕溝,鑿過石頭。”
在一些散文詩作品中,“我”就成了一種既有共性又有個性的實在。而不是抽象的、泛指的、中性的“我”。如《還早哩》:“默默的、莊嚴的寧靜。偶然傳來一聲鳴啼。還有工人的腳步聲。靜寂而持續著。然后,一只心神恍惚的手在我的胸前試探我的心跳。永遠叫人驚訝。”《遠方的女子》:“這女子剛好裝滿我的手,她皮膚白皙,金發,我會用手捧起她,如同捧起一籃木蘭花。這女子剛好裝滿我的眼睛。我的目光擁抱她,我的目光擁抱著她就什么都看不見了。這女子剛好裝滿我的欲望。在我生命的烈火前面,她赤裸著身體,而我的欲望把她像活炭一樣燃燒。”《帳篷》:“有時,我會像毛蟲一樣爬出帳篷。在帳外,我會躺在濕的苜蓿上面,浮動的腦子充滿思念,我的目光凝注遠方的星星。郊野和岸邊星夜使我感動至暈眩,而我的生命在黑夜里漂浮,像落進旋渦的蝴蝶。”《告別的船》:“我抵達地球的岸邊,他們讓我的船在一個海里下錨,那是我從來未見過的,藍天下最碧綠的海。我的錨在海底的黃沙上憩息,已經習慣了水波綠色的親吻,跟纏綿的深海花草玩耍,在悠長的白天,白色的水妖會把它們當作坐騎。”
另外,在《名字》《錨》《歌》《愛》《煙》《夜風》《海美人》《旗》等章中,都有所體現這種主體生命意緒對客體生命的感知與應和,其精神性質在文本中閃爍著太陽一樣的光芒。可以說,聶魯達大部分作品,都是與國家命運相聯的,有著
積極的精神向度和明朗的意義指向。至于他的一些奇怪的遣詞造句,晦澀的比喻聯想,對于詩人來說,則是少有的心理矛盾之真實反映。
注:①引自【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甘陽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第189頁。
②【美】拉爾夫·華爾多·愛默生:《愛默生散文選》,蒲隆譯,譯林出版社,2008,第51頁。
③【智利】巴勃羅·聶魯達:《聶魯達論詩:人民的詩人》《漫歌》,江之水、林之木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679頁。
④【智利】巴勃羅·聶魯達:《聶魯達與<漫歌>》參閱并轉引序言部分,《漫歌》江之水、林之木譯,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第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