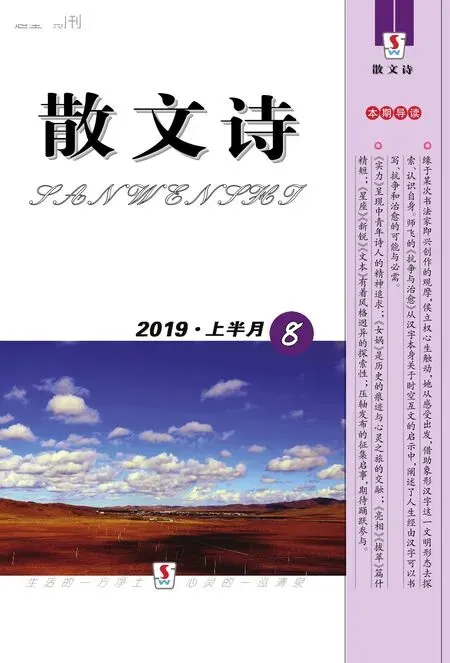世界散文詩:在思想的隱喻里展開或釋放(四)
◎黃恩鵬
紀伯倫的長章《先知》和《沙與沫》,有人譽為“思考了一千年”的著作。“造反和叛逆喧囂”,更像是一片真善美的凈土。他曾說過:“心靈本是純樸簡單的,心靈的表現也是純樸簡單的。”從宇宙與人與社會與真理的關系上思考人本存在的諸多問題。無論從內容、形象、隱喻或情緒上說,他的作品都充滿了宗教意蘊。在這兩長章作品里,他把精神提升到相當的高度,“任何精神都體現在上帝中”。在他的作品里,上帝被喻為“陶工”“射者”“至高無上的詩人”;是上帝把宇宙、世界和人生凝聚起來并賦予其意義。上帝永遠是人類尊崇膜拜的圣者。而內心的大地神靈也一樣坦言:“人類的一切若止于人間便毫無價值。”在上帝的光環照耀下,紀伯倫抒發了對耶穌、神靈、先知和人的熱愛。他把精神的圣靈符號完全貫注其上,賦予其理想主義的色澤。而人類的精神追求和終極目標,也許就應建立在個人的心靈之上,并超驗其神圣的宗教。在精神的感召中,提倡的是一種新型的神論。即人與神的相依相偎的關系。他的上帝其實就是人類自己。“我們就是上帝”從根本上詮注了這種精神體驗。
在《沙與沫》中他寫道:“魔鬼死在你出生的當天。現在你不必穿過地獄去會見天使了。”從根本上理解了人對精神力量的需求。精神需要上帝,這似乎是天經地義的。而天堂,其實就在我們的平常生活中:“在門背后,在隔壁的屋里”。在自然的狀態下,人既不高于卑者,也不低于先知。人作為生靈一種,既不高大也不卑小。是大地,又是蒼穹,既是平凡的沙與沫,又是不平靜的大海。人應該時刻發掘自己的神性(精神性質)來克服自己的卑瑣肖小,從而實現自己的生命價值。自然界的競爭應從混亂走向有序,應從“小我”上升至“大我”“真我”之境,真正實現萬物合一,與上帝合一。他還認為,強健的靈魂又是寬恕的,寬恕是受傷者的榮譽。紀伯倫最鄙視的,是人品行中的奴性,他向準備廢黜暴君的人們建議:“先要看看他在你們心中的王位是否已經徹底摧毀。”其精神氣象始終氤氳在他的散文詩文本中。他認為,心靈是永恒不敗的精神領地,在這個精神領地里,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君主。
安德烈·紀德的《大地的糧食》是相對于《圣經》中的“天糧”或“神糧”而言的。主題的先入定調便有了慈憫眾生的意味:《福音書·約翰福音》中耶穌這樣對眾人說:“這是從天上降下來的糧,叫人吃了就不死……”由此,我讀到的是一種博大的關愛眾生之音擲地而起。那么這“大地的糧食”普澤之精神性質就十分明顯了。大地,是一種精神哺育的符號,糧食則是生存的衣缽所在,須臾離不開的東西。“大地的糧食”象征人類在大地上謀取幸福的精神食糧。如同紀德所引用的《古蘭經》中的一句箴言:“這是我們在大地上享用的果實”。大地,永遠是給予。而人類,不管是善良的還是罪惡的,都是享受者。一種普澤眾生的力量,由大地而起。
《大地的糧食》中,以一個假想的導師梅納克來對弟子教誨為口吻,以長者般的溫和口吻對著世人說話,也是詩文本特點所在。從自我的內心出發,直接抵達眾生。從施予和被施予出發,努力達致獨立不羈的人道精神。倡導人們在大地潤養身體之足的同時,也讓精神壯健起來。幫助人們認識自我、認識世界。紀德從《圣經》中獲得啟示,以超越了個人主義的情懷,去深入利他主義。他認為“個人的勝利在于個性的放棄之中”,如此,個人才是真正的幸福。也就是說,紀德最終相信利他思想定然讓這個世界煥發出勃勃生機。而人類的獨立精神,是從利他主義出發而不是從個人利己主義出發的。當19世紀中葉時,實驗主義哲學統治了科學和哲學的全部領域時,文學上則是以自然主義代替了浪漫主義,從而彌蕩久遠。而整個世界對于詩人來說,是不是就沒有它的精神上的存在意義了,則是一個大大的問題。當尼采喊出了“上帝死了”這一驚天動地的聲音時,一切形而上或意識形態的本質意義則立即喪失。這是相當可怕的。生活在大地上的眾生,如果失掉了自己內心與世界的聯系,只剩下孤獨的自己,那么還有什么意義呢?這孤獨的自己事實上是無法存在的。否定了上帝,就是否定了萬物。因為萬物就是上帝。萬物存在,這個世界就存在。尼采的這一隔絕的結果,定然會造成極端的個人主義盛行,個人的自尊自大也會越來越囂張。那么“人定勝天”所造成的結果會是怎樣?這種剝離了自然與人的關系所釀成的危險是顯而易見的。當叔本華的意志哲學以及崇尚宗教與神秘力量就得到了推崇。安德烈·紀德的《大地的糧食》之“感恩精神”就適時地走近了眾生。感恩大地既是對于世界對于本然意蘊的眾生的肯定,其深遠的影響就可想而知了。因為這種“感恩精神”招致了人們對于社會道德規范的思考,并且積極地注入了人性大善的力量。人們將呼吸到另樣的一種清新氣息:大地。母親。自由。愛情。解放。人生。人權。生存。和平。等等這些普澤世人的終極理想,人們在思想道德領域要實現的東西,在這里統統找到了。而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也受到了影響,它突破了人類心靈的桎梏,找到了一個理想社會應該有的:平等和自由,也為道德重建注入了新的生命之源動力。
唉,我們不知道,在找到上帝之前,應該到什么地方去奉獻我們的祈禱。隨后,人們終于想到,上帝無處不在,上帝處處都有,上帝是不可找到的神。于是,大家胡亂地下跪。(卷一)
大地上令人眷戀的美啊,你的表層盛開鮮花是一種奇跡。哦,深浸著我的愿望的景色!(卷三)
……啊!鳥兒能唱得這么響亮,這超出了我的想象。甚至樹木好像也在叫喊,用它們的全部樹葉吶喊——因為在樹上見不到鳥兒。我心里想:它們這樣叫,會叫死的。(卷七)
紀德本人承認他的《大地的糧食》是從《圣經·福音書》中獲得詩的靈感。他認為通過音樂的形式捕捉到心靈的思考。這思考當然是詩性的。由此,文本總是洋溢著歌唱性。《大地的糧食》全書共計正文8篇、頌歌1篇,寄語1篇,由一連串富有詩意的斷想,加入一些激情的詩篇、日記、輪舞曲、歌曲等架構而成。在結構形式上不拘一格,為的是能更好地適應“讀法”,葆有諸多新文體“雜揉”的風貌。詩中從一而終的情緒與想象的充沛。以詩性的語言、意象化的語言傳遞著人的情感、馳騁著人的想象。在如“進行曲”般的行文中,揳進了歌唱性質的“片斷”,從而將音樂性發揮得淋漓盡致。它的內在節奏,形成了內在的旋律美和音樂的曲式美。呈示、展開、再現這三部式吟詠,成功地增強了其內在的勁力。思想格局宏大,內涵宏大而不停留于感覺,把詩情與哲理融為一體。關注人類的命運,探討人的本性,解剖人的靈魂,將一種可貴的“大人類”思想完全呈現在世人面前。這種力量是與自然合拍的,而不是剝離的。它將影響我們時代的進程,倡揚我們的時代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