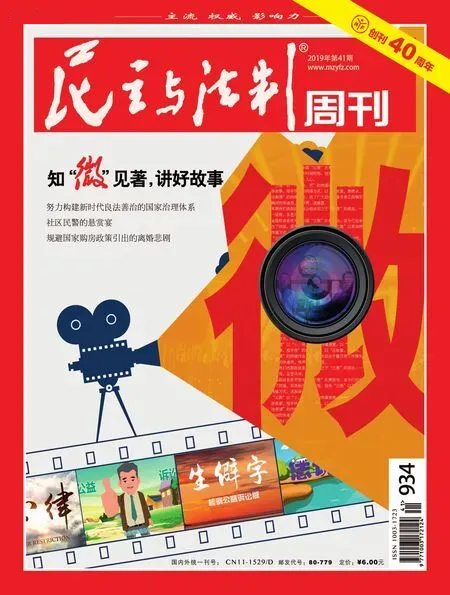連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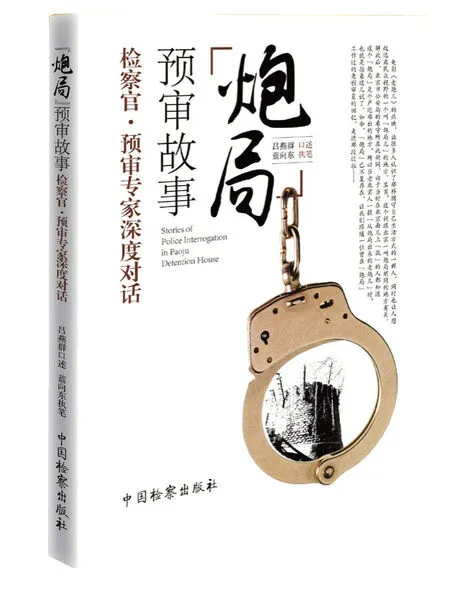
“炮局”預審故事檢察官·預審專家的深度對話
呂燕群 口述 藍向東 執筆
預審故事之十二
一站七
在老預審員口述“炮局”往事的開篇中,我們談到“文革”后,炮局是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處)分局的所在地。公交分局的拘留所(看守所)即北京市第三看守所也在此地,主要關押公交扒竊案件嫌疑人,一些“涉黑”團伙的首要分子也在這里接受預審。
預審員老盧今天講了一個與公交扒竊案相關的故事。
北京的公交比較發達,車多賊也多。
有一天“炮局”來了一個新人,外號“一站七”,是一個專門在公交車上扒竊的老賊。這外號還有一番講究,是圈里的同行給叫響的。
干小偷小摸這行當,老北京話叫“佛爺”,是下三濫里邊層次最低的。老北京還有一種說法,叫做“老炮兒吃佛爺”,講的是“佛爺”后頭一定得有靠山,而這靠山就是“老炮兒”。啥叫“老炮兒”,前邊已經講了,就是那些幾進幾出“炮局”的人。別看這些人在“政府”眼里是犯罪嫌疑人,在普通老百姓眼里是社會的渣滓,但是這些人出了“炮局”,在社會上也屬混出了些名堂,在那幫小混混眼里就是老大了。這“老炮兒”講的就是流氓仗義,小混混被欺負得他們罩著,打架擺平的事兒就指著“老炮兒”干。因此,“佛爺”小偷小摸掙的錢都得拿出一些進貢“老炮兒”。
雖說“佛爺”在社會上也只是小混混,份兒低,但是在公交車上扒竊那是靠“本事”吃飯。
那些剛學會偷摸的“菜鳥”反偵查能力弱,剛一下手通常就被警察給逮住了。老賊則“鬼”得很。在車站等車的時候通常已經瞄好了乘客,上車的時候貼在乘客身后探虛實,卻不著急下手。有時候剛上車又馬上下車,幾上幾下看似“演戲”,實際上試探后邊有沒有警察跟著。這就叫火力偵查,他們的行話叫“掃雷”,這“雷”當然就是他們的死對頭反扒民警嘍!
據說公交扒竊這個行里也有個規矩,只要車上發現偷摸的活兒比自己干得漂亮的、本事高的人,其他小偷就得知趣地乖乖下車。
上世紀八十年代,北京公交扒竊圈子里,名氣最大的就數“一站七”了。
干嗎取這么個外號呢?你不知道,這個人一上公交車,坐一站地竟然能偷七個乘客的錢包!你說本事大不大?
“一站七”雖然“切”錢包的功夫了得,很少失手,但是這次被請進“炮局”后,和其他慣偷不一樣的是他很快就撂了,而且還豎起大拇指夸起了咱偵查員呢!
“吃公交這條線多少年了,今兒栽了,我還真是服了你們公安了!”“一站七”說。
故事還得從兩人在公交車上斗智斗勇開始。
講這故事之前,我們不妨先聊聊扒手們的“黑話”。“天窗”指的是上衣兜,“平臺”指的是下衣兜,“屁門”指的是后褲兜,“鼠洞”指的是兩邊斜插的褲兜。這些行話除了小偷恐怕也就只有偵查員和預審員知道了。
話說“一站七”在東單上了二路公共汽車。一上車,就掃了一下“雷”,結果發現一個兒不高、胡子拉碴、長得土了吧唧的“老帽兒”和他對視了一下。“一站七”心里咯噔一下:今兒怎么那么倒霉,莫非一上車就碰到了“雷”?
“一站七”畢竟十分老到,雖然對這個老農心有疑慮,但還是不動聲色。他心想,我得拿法子試試他!
說來也蹊蹺,那位老農上了車之后,居然冒冒失失地往“一站七”這邊靠,還用鼓鼓囊囊的上衣口袋蹭他。
“一站七”心想,我是何許人,別把我當土老帽兒!想讓我“開天窗”上鉤?門兒都沒有!
公交車快到天安門的時候,那個老農湊到售票員跟前,用濃重的河南口音問道:“俺頭次來北京,天安門到沒?”
“一站七”一聽這口音、這問路,對這老農多少有些不屑,但還是沒有放松警惕。
“我得逗逗他!”“一站七”仗著自己藝高人膽大,也想逗個悶子。
“一站七”下了車,在前門汽車站附近進了一家不起眼的小飯館。他隔著飯館的窗戶玻璃往外瞅,瞧見那老農也下了車,一屁墩兒坐在馬路牙子上,從左邊衣兜里摸出了一個饃饃,捂著臉就啃了起來。
或許是渴了,老農啃了一小會兒饃饃,就起身進了飯館。
“一站七”發現老農進飯館的時候瞅都沒瞅他,徑直走到柜臺前要了二兩散裝白酒,就出門去了。
“一站七”心想:這老家伙怎么連花生米也沒有要幾粒就出去了,拿什么就酒呀?
正當“一站七”納悶兒的時候,坐在馬路牙子上的老農在衣兜里又摸索了半天,掏出了一樣東西,喝一口酒,拿東西放嘴里嘬一口,有滋有味兒,讓人看著眼饞。
“一站七”定睛一看,我的媽呀!老農手里居然是一根被嘬得發亮的釘子!
“一站七”覺得今兒遇到的這個主兒真是土得掉渣了!不管他是“雷子”還是真老帽兒,反正上衣兜里鼓鼓囊囊的,令他手癢癢。
一袋煙工夫,老農把那二兩白酒也喝完了,站起身來,打了個酒嗝,連褲子上的土都懶得撣一下,便依里歪斜地往公共汽車站走去,上了另一趟公交車。
不用多說,“一站七”尾隨了過去。
上車后,“一站七”抖了個激靈:真假“雷子”,我試試你不就現了原形嗎?
于是“一站七”上了車之后,就擺出剛出道的“菜鳥”那副樣子,故意拿眼睛左瞄瞄右瞄瞄,專往乘客的衣兜、褲兜瞅。
不料,他這一招不僅沒有奏效,那老農滿嘴酒氣倒是往他這邊靠過來了。居然還是拿鼓鼓囊囊的衣兜往他身上蹭。
俗話說,狗改不了吃屎,貓改不了玩性。“一站七”抬起左手搭了個“架子”,這右手可就伸進了老農的“天窗”。
讓“一站七”萬萬沒有想到的是,老農的手比他還快,居然沒等他抽出手來,就把他的手摁住了,而且滿車里喊:“抓小偷!抓小偷!”
乘客們都既驚恐又好奇地往這邊看,老農一松手,“一站七”的剪刀手剛好從老農的上衣兜里夾出一沓鈔票來!
后來人們定睛一看,全樂了——這哪是什么鈔票呀!這分明是一沓馬糞紙!
“一站七”就是這么栽的跟斗,簡直顏面掃盡,但栽得他心服口服。
不用說您也能猜到,這位老農確實是位偵查員。北京市公交分局為了反扒而專門招錄了一批退伍軍人,這些人哪兒來的都有,這河南口音也是地地道道的,怪不得讓“一站七”看走了眼。
最近幾年,北京市公交扒竊案件審查起訴工作集中由東城區人民檢察院辦理,最多的時候一年有五百多起犯罪案件。說起“一站七”的故事,東城區檢察院專門辦理這類案件的資深檢察官老張告訴筆者:“一站七,這老賊的外號我打小就聽說過,真人沒見著,但這些年我辦理了幾百起公交扒竊案件,真是各色的小偷都過過招。”
檢察官老張是地道的北京人,說起辦理公交扒竊案件的體會,他深有感觸:扒竊案件犯罪嫌疑人很多都像“一站七”那樣的職業扒手,劣跡斑斑,起訴書中指控的犯罪事實可能就是簡簡單單的一起扒竊,法庭上核實前科情況卻得花上小半天時間。
“這還不算什么,更可氣的是扒竊慣犯為了逃避懲罰挖空心思,甚至連自殘的損招也派上了用場。”老張說,“有的慣偷在作案前就采取了拍針、吞刀片等伎倆,即便被抓獲,在被送往看守所羈押前體檢的時候過不了關,公安機關只能對他取保候審,就算是判了刑也得做完手術后才能服刑。”
“這拍針是怎么個拍法?”我問他。
“就是用一寸多的鋼針往自己的左胸拍進去,拍的手法和部位都極為講究,位置在心臟膈膜上一點點兒,死不了,行動也無大礙,還能照樣作案。”
說到這兒,老張突然想起了一個他新近辦理的案件:一名拍針后扒竊被抓正在被取保候審的嫌疑人,可能感覺到這“胸針”確實也是顆危及自己生命健康的“定時炸彈”,便湊了兩萬塊錢現金,準備到六里橋附近的電力醫院做手術。這哥們兒上了公共汽車,還沒到電力醫院,半道上就又被警察逮住了!不是因為別的,是本性難改,一上車心里就癢癢,結果下手偷摸的時候被逮個正著,你說該著不?
不管扒手如何狡猾,總會有一張法網等著他,螳螂捕蟬黃雀在后,“一站七”這樣一等一的高手不也折了嗎?
(未完待續 本文略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