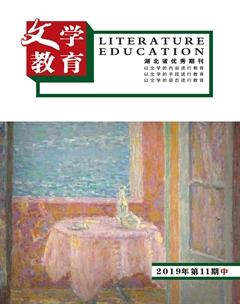漢字的繁簡之爭
趙舒靜
內容摘要:近年來,漢字的繁簡之爭一直是熱門的文化議題,“以簡代繁”派、“復繁去簡”派和“識繁書簡”派各有擁躉。本文認為應尊重語言文字的發展規律和社會時代的需求變遷,兼顧語言作為交流工具和文化承載體的雙重屬性,保全其形態的多種可能性,以寬容的態度傳習繁體字,以實用的態度保留簡體字,留待文字規律自身發揮作用、留待歷史和民眾做出自然選擇才是尊重當下、對未來負責的一種安全態度。
關鍵詞:簡體字 繁體字 繁簡之爭
在一個文化趨向多元的時代,漢字的繁簡之爭再次浮出水面并不是奇怪的現象。雖然漢字由繁復而簡單、由詰曲而徑直、由奇詭而平易的總體變化方向似乎已被學界公認,并且得出漢字形體從來都在發生簡化的定論,但無論廟堂還是民間卻也從來不乏反對之聲,前者如田惠剛在《漢字簡化質疑》中提出的簡化字十多條不妥之處,后者如流行于九零后、零零后年輕人當中無甚科學體系但明顯比簡化字繁復的所謂“火星文”。究竟應該以簡代繁、復繁去簡,還是識繁書簡?各派立場背后是迥異的文字哲學:支持以簡代繁的多將文字單純視作交流的工具,支持復繁去簡的多將文字看成文化的承載體,而支持識繁書簡的則多是基于現實條件的兩者調諧。
本文傾向于支持第三種立場,但并非出于妥協中庸的態度。一方面,語言文字有自身的規律,專斷的人為干涉只能在短期之內起到效果,因為語言自身具有修復和重生能力,歷史上試圖以強力撥轉語言文字發展方向的企圖往往徒勞而返。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所謂“世界語”,它的設計盡量符合種種簡便、普適規律,然而卻終究無法被世界人民接受;再如1977年版的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由于受到個別政治家繼續簡筆畫、縮字量的指示,將漢字變成了過分依賴假借等形式的文字,這樣對漢字表意、區別功能有損害的變化自然無法流行于世;更早的例子如武則天興之所至造下的新字,如今唯一尚能為人偶爾提起的也只剩下一個“曌”字。另一方面,無論將文字視作交流工具還是文化承載體,都無法逃脫它作為語言的一個維度的本質。以海德格爾的語言觀視之,人在言說語言(當然包括書寫文字),反向地,語言也在塑造人(通過建構我們的認知和思維方式)。繁簡兩派論爭當中常舉一例:過去的愛是有心之“愛”;現在的愛則是無心之“愛”。粗看之下近乎荒謬,然而如果聯想漢字簡化的背景——工業化、現代化在中國生根發芽,人們對于快捷便利的生活方式傾注前所未有的熱情,那么對個人情感的忽略、或是親密關系的價值觀改變,的確既體現在現實中,也體現在文字里,且通過文字對集體的意識和無意識產生塑造性的影響。在關于文字的本質尚有爭論的前提下,保留它形態的多種可能性,不能不說是尊重歷史和現在、對未來負責的一種安全態度。
如果秉承文字工具論,如錢玄同所說,“文字本是一種工具,工具應該以實用與否為有力遏制標準。筆畫多的,難寫,費時間,當然是不適用。我們應該謀現在的適用不適用,不必管古人的精意不精意。”①那么漢字的簡化似乎成為必然的趨勢,甚至終點通向羅馬文字也十分合理,因為畢竟漢字存在形態復雜、同音字多、一字多義現象嚴重等種種“缺陷”。去繁就簡,處處合于“經濟”原則。這也是為什么自二十世紀初始,陸費逵、錢玄同、胡適、林語堂等知識分子就致力于推動文字簡化,令更多的國人能夠以較少的精力掌握較多的漢字,借此推動國民文化程度的提升。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國推行的簡化漢字方案,從客觀上也確實對掃除文盲、推進基礎教育起到了不容小覷的作用。類似地,這也解釋了為什么漢字大體上經歷了由甲骨文、金文到篆體、隸書、楷書的變化過程(以書體討論字形變化不算十分嚴謹,但書體能夠體現字形變化)。但如果僅僅基于實用與經濟的考慮,便認為簡必勝于繁,今必強于古,則是忽略了漢字除了工具性功能外的豐厚內涵。
在數千年的歷史中,哪怕在西學東漸乃至西方文化借刀槍火炮進入國門的時代,漢字仍以頑強的姿態存活了下來,甚至成為中國人性格、傳統的一個象征,無言地表明工具性、經濟論并非決定文字優劣、歸屬的唯一原則。漢字的簡化過程的確一直都在進行,但無論如何,漢字的形體仍是一脈相承的方塊字,它具有對前代語言的保持能力,雖經種種變數,與詞源的對應關系仍然有跡可循。美籍華裔學者唐德剛教授曾說漢字“保留了十九世紀以前人類最豐富的記錄,總容量超過人類文明史其他文字所保留的總和”②,并非夸張。
漢字是典型的訴諸視覺的文字,這是表意文字的天然優勢,字形、字音、字意三者在漢字當中緊密結合,所以,漢字本身無可爭辯地承載著歷史文化信息。這就是為什么漢字被稱作中國文化的活化石。現在刊行于世的許多著作都致力于厘清漢字中包含的文化信息,遺憾的是,簡化之后的漢字在還原歷史風貌、提示早先詞源的方面顯得隔膜較深,提示無力。無疑,從年代角度而言越久遠的文字,就越接近詞源,因而濃縮了當時的文化記憶。不過無可辯駁的是,從小篆到隸書,再到楷書,乃至清末出現的現代楷書,字形都有相當的變化,其中含蘊的文化信息也是各個不同。哪怕是被實踐證明失敗的1977年第二次漢字簡化方案,也留下了當時時代的烙印——文革剛剛結束,建設為先,百廢待興,一切以勞動人民為服務對象,字形極簡,字數極少。漢字越簡化,就越向轉注和假借靠攏,離象形、指事越遠,這一趨向似乎與保留漢字考古式的文化內涵是相悖的。這向我們提出了又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如果復繁,復至何時的繁。
在國內一些漢字網上論壇上觀戰,常能發現簡體派對繁體派提出的一個反駁問題:既然要恢復老祖宗的文字,為什么不索性更往前一步,恢復甲骨文?此問初看近乎意氣之下的抬杠,實際上并非完全荒誕。如果說漢字是漢文化的活化石,那么究竟要選擇哪個斷代史的活化石,的確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1964年5月頒布《簡化字總表》后,用“繁體字”來特指原有書體。中國大陸的繁體字基本是以《簡化字總表》和《新華字典》上的繁體字為準。然而這些繁體字都采用了新字形,與古書的繁體字及中國臺灣、港澳地區使用的繁體字并不完全一致。哪怕是臺灣與港澳地區使用的繁體字也存在差異:在臺灣,字體標準是《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次常用國字標準字體表》和《罕用字體表》;而香港和澳門則以《常用字字形表》為準。兩者的差異整體來說并不很多,但仍有一些字的區別較為明顯,例如“裏”與“裡”、“著”與“著”。可見,即便不往時間更縱深處追溯,在地理上繁體字也存在蕪雜的現狀。若論漢字作為意音文字承載文化的功能,那么何時、何地的繁體字承載了最多的文化?對于難以回答的問題,另辟他徑才是可行的辦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實施簡化字方案,秉承的原則是“約定俗成,穩步前進”(葉恭綽在1955年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教育部聯合召開的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上的講話),也就是在社會已經形成的習慣基礎上因勢利導,且是分批進行,并非一次徹底完成,這對于繁體字與簡體字的再度被選擇是有很大借鑒意義的。不可否認,如果識繁寫簡的方針能夠得以實施,必定會出現一定的混亂,然而這仍是在尊重語言文字自身發展、進化規律的前提下發生的情況。類比地說,英語的詞匯、書寫至少分為英式、美式,還不考慮過去的殖民地所分化出的“洋涇浜”英語,但這在國際交流上并未引起巨大的混亂,美國人仍能認識英式詞匯,反之亦然。同樣地,漢字文化圈中的日本也存在多種字體并存的狀況,日常生活中多用戰后發布的新字體(略字),但并未正式宣布廢止未經簡化的舊字體(傳統漢字);在歷史場合、傳統場合或專有名詞中,對舊字體仍然有所保留。對比之下,我國現行的唯簡體字為合法的一刀切雖得之于“標準”,卻未免失之于“唯一”。
現今的中國,在一些特殊領域仍然使用繁體字,例如書法。這本身就體現了繁體字所富含的美學價值。如果更多的人,尤其是兒童與年輕人能認識這一瑰寶,對于漢文化的身份認同以及發揚光大好處是不言而喻的。有值得尊敬的漢字,才能延續中國人敬惜字紙的傳統。文字的產生、變化和發展歸根結底是社會群體行為,一時的立法、規范能起到周有光先生所謂“啟動刺激”之功效,但這種刺激的后效能有多長,究竟還是由文字本身規律、社會時代需求所決定的。與世界上許多古老文明一樣,中國社會基本上經歷了農業化、工業化、信息化的演變過程,每一階段都有與當時文化、經濟狀況契合的漢字書體,而這些漢字書體也多循著文化衰減規律,在時代變遷中漸漸消磨。現在提倡更多的人認識繁體字,并不像在英語國家呼吁恢復古英語、中古英語一樣,因為那與現代英文的詞匯、語法幾乎完全不同;簡體字來源于繁體字,在字形上往往有源可尋,簡化的過程中增強了大眾化、通俗化的特性,同時也由于“一簡對多繁”的簡化方式丟失了許多文化內涵,甚至帶來表意上的混淆。以寬容的態度傳習繁體字,以實用的態度保留簡體字,留待文字規律發揮作用,留待歷史和民眾做出自然的選擇,大概是當下最合理的態度。
參考文獻
[1]蘇培成著,《二十世紀的現代漢字研究》,書海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2]許威漢著,《漢語文字學概要》,上海大學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3]周有光著,《漢字和文化問題》,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
注 釋
①轉引自《二十世紀的現代漢字研究》,蘇培成著,書海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第187頁.
②轉引自《漢語文字學概要》,許威漢著,上海大學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第8頁.
(作者單位: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