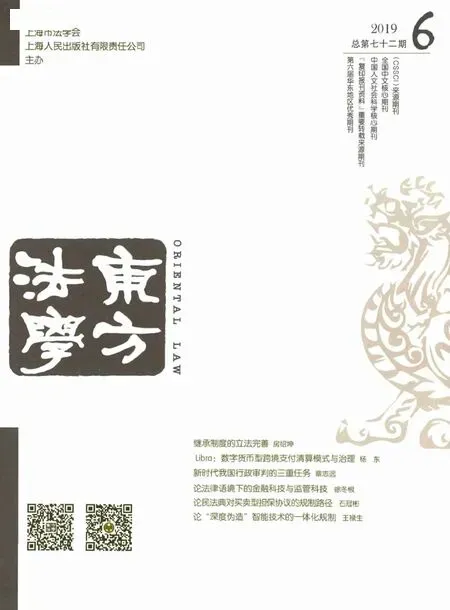警察即時強制權的規范化行使
——以公民權利保護為線索
劉 軍
為了更好地預防或者制止正在發生或即將發生的違法犯罪行為、危險狀態或者不利后果,或者為了保全證據,確保案件查處工作的順利進行,法律通常會賦予警察以即時強制權,根據現場情況對行政相對人的人身、自由、財產等給予一定的強制性限制。這是一種具體行政行為,可以包括盤查、留置、即時搜查、扣押、傳喚等行政強制措施。由于這種強制權具有即時性,需要臨場決定和執行,而且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財產等基本權利。如果不規范行使,則很有可能侵犯公民權利、引起社會對于警察公正執法的質疑。
一、警察即時強制權存在的合理性及其法律性質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義是最強的力量。”他在不同場合講話中多次強調要“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就公安工作而言,規范執法就是最大的正義!要以人民利益為中心,以權利保護為旨歸,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次執法活動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都能感受到被主體性地對待。警察即時強制權是目前公安工作中最容易侵犯人民權益、監督最為薄弱的環節,需要貫徹“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對之進行規范化審視。
公安機關承擔著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治安秩序、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的重任,因此被賦予了各項與履行職責相匹配的權力,尤其是在出現緊急事態、不測危險和突發事件的情形下,必須賦予警察在緊急事態下及時處置的強制權力,以防止和排除當前的緊急事態。這便是警察的即時強制權,即警察機關在維護治安管理的過程中,為制止違法行為、防止證據損毀、避免危害發生、控制危險擴大等情形,依法對公民的人身自由實施暫時性限制,或者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財物實施暫時性控制的行為。典型特征是:不以行政處分的作出為前提,而且無事先告誡環節。由于行政處分(包括告誡和執行方法的確定)與實施強制手段的行為高度集中,缺少時間延續,因而稱為即時強制。即時強制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如果先向行政相對人作出義務命令并期待其自動履行否則再給予強制,這種通常的行政強制有的時候很難實現行政目的。即時強制常常因為時間緊迫,無暇作出行政命令并期待其履行義務,或者其性質通過命令義務難以實現行政目的,又可細分為與實現行政目的有關的制度,如強制隔離、交通管制等,此種屬于即時執行;與行政調查有關的制度,如臨時檢查、盤問等,亦即狹義的即時強制。按照即時強制標的的不同可以分為對人身、財產和場所的強制。即時強制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急迫性。
通常認為即時強制屬于一種權力性的事實行為,完全是臨場決定、即時執行,即使將來提起行政訴訟或者撤銷之訴也沒有太大的法律意義,因為它造成的損害事實已然形成,當事人只能于事后請求損害賠償或者是損失補償。而且《行政強制執行法》的規定針對的是所有的行政強制行為,并沒有突出警察即時強制權的特殊性。警察強制權往往會涉及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如強制傳喚、檢查、搜查、盤問、留置、約束、強行帶離現場、強行驅散等,有的即時強制還可以直接使用武器警械,如果實施不當或者行使不規范,則很可能會侵犯公民基本權利,導致社會對于警察公正執法的質疑,嚴重的還會釀成重大社會事件,成為潛在的社會不安定因素。
沒有人會認為我們的社會不需要警察的保護,世界各國也都規定了警察的行政強制權,而且對于打擊違法犯罪、確保社會秩序和人民財產安全等方面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警察的執法行為必須具有目的正當性、實質合理性和程序規范性,以違法的方式執法損害的不僅僅是個別公民的權利,而且會極大地損害政府的公信力。因此,有必要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高度,在分析警察即時強制權不規范行使的原因基礎上,參照法治發達國家的通常做法,拿出系統性對策,標本兼治,全方位扎緊制度的籠子,規范警察強制權的行使。
二、警察即時強制權不規范行使的原因分析
警察即時強制權不規范行使的原因多種多樣,有警察隊伍中個別人員素質問題和執法水平的問題,也存在個別警察特權思想嚴重、挾私報復的現象,甚至還有個別警察濫用職權、違法亂紀的可能,但是更應當從制度建構的層面思考如何“全方位扎緊制度的籠子”,防止權力走向人民的對立面,以履行職務的名義行不法之事。擇要而言,警察即時強制權不規范行使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警察行政強制權不規范行使的直接原因是缺乏外部監督、行為不具有可檢視性。所謂的行政強制權是指包括盤查、留置、強制醫療等行政強制措施和警告、罰款、拘留、收容教育等行政處罰在內的行政強制權力。相對刑事偵查權受到刑事訴訟法的約束和來自檢察機關、法院的權力制衡而言,我國的警察行政強制權由于具有自主、強大和封閉的特點,很難受到外部的監督和制約,公民權利一旦受到侵犯則更難得到及時的法律救濟。而行政強制權中的行政強制措施尤其是即時行政強制權,相對行政處罰而言,由于極少受到其他權力部門的制約,不但缺少外部監督,內部監督也十分地乏力,而且行政強制措施臨場處置色彩濃厚,無需前置審批程序,警察自由裁量空間大,缺乏最起碼的可檢視性,成為當前公民權利最容易受到侵犯的部分,彰顯了規范警察即時強制權的急迫性。
二是,警察即時強制權不規范行使的根本原因是法律規定模糊、程序粗糙、不具有可操作性。在我國,與警察即時強制權相關的制度散見于《行政強制執行法》《人民警察法》《治安管理處罰法》《戒嚴法》《集會游行示威法》《傳染病防治法》《城市人民警察內務條令》《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等法律法規中。《行政強制執行法》是一部系統規定行政強制行為的種類、方式、實施原則和實施程序,規范行政強制的設定和實施、監督和保障的法律。這部法律區分了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強制執行,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同時,該法也規定了行政強制措施的種類,包括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查封場所、設施或者財物,扣押財物,凍結存款、匯款以及其他行政強制措施(第9條)。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行政強制執行法》第19條賦予了行政機關即時強制權,并概括規定了即時強制的實施程序,“情況緊急,需要當場實施行政強制措施的,行政執法人員應當在二十四小時內向行政機關負責人報告,并補辦批準手續。行政機關負責人認為不應當采取行政強制措施的,應當立即解除”。再加上行政強制的“適當原則”(第5條)和“堅持教育與強制相結合的原則”(第6條),采用非強制手段可以達到行政管理目的的,不得設定和實施行政強制。應該說,即時強制的法律制度框架已經基本建立,初步起到了法律規制的作用。但是《行政強制執行法》并沒有區別對待警察即時強制權的特殊性,而且《人民警察法》《城市人民警察巡邏規定》《公安機關適用繼續盤問規定》等法律法規的具體操作規程存在著啟動盤查、留置、傳喚的規定過于模糊、缺少適用程序、沒有救濟手段等缺陷。比如,《人民警察法》第9條規定對“有違法犯罪嫌疑的人員”經出示證件可以當場進行盤問、檢查,但是對于判斷“違法犯罪嫌疑”的標準卻無只字片語,盤查的程序也語焉不詳。雖然《行政強制執行法》規定了行政強制的“適當原則”(第5條)和“堅持教育與強制相結合的原則”(第6條),但是缺乏具有可操作性的實質性標準。因此,有必要對于警察即時強制權啟動的實質條件和程序規定進行補充立法,增強警察即時強制權規范行使的可操作性,增加公民權利受到侵犯時的救濟條款。
目前世界各國對于警察即時強制權的規范已經從強調程序合法性轉而走向強調兼具程序合法性與實質合理性,而且通過比例性原則從實體上對于警察的行政行為提出程度上的合理性標準,要求警察行政行為也要根據職責要求和執法目的拿捏分寸,以盡量溫和、對公民權利影響盡量小的方式與方法臨場處置。否則,即使程序合法,也可能會因為采取了明顯不合理或者過激的手段而受到投訴或者被提起行政訴訟。補充立法應當對于警察即時強制權乃至整個行政權提出比例性要求,防止警察行政權對于公民權利的過度侵擾。2018年的《人民警察法(草案)》第8條規定了警察權力行使“適度原則”和“最小侵害原則”:“人民警察行使權力應當與已經或者可能造成的危害的性質、程度和范圍相適應;有多種措施可供選擇的,盡可能選擇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合法權益造成最小侵害的措施。”但是相較于大陸法系的比例性原則和必要性原則等仍然存在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和必要,希望在《人民警察法》正式修正出臺之時能夠完善警察即時強制權的實質性標準,同時將人權保障和正當目的等理念納入法律規定之中。
三是,警察即時強制權不規范行使的深層次原因是利益驅動。雖然《警察法》第37條規定了國家保障人民警察的經費,按照事權劃分的原則,分別列入中央和地方的財政預算。但是,基層公安經費緊張卻是不爭的事實,不排除公安機關個別單位、個別干警為了更多地從財政拿到返還的罰沒款或者增加年度預算而進行選擇性執法,對于有利可圖的案件特別上心,動力十足;而對于日常的人民群眾反映強烈但卻沒有經濟利益的案件卻置若罔聞。媒體經常曝光個別地方交警部門為了自身利益而多開罰單甚至出現“搶罰單”的現象,這還僅僅是交通警察,對公民權利的影響主要在財產權上。如果是治安警察、刑事警察也“搶罰單”,受到影響的公民權利可能就不是財產權了,而是人身權和自由權了,甚至也會影響到安全和秩序等公共法益。當警察也在大搞“利益”衡量、選擇性執法的時候,再詳細的法律規定也只能是廢紙一張。濫用職權與玩忽職守都是對權力的僭越,而選擇性執法則同時在這兩個方面違背了法律對于權力的授權與信任。
因此,要充分認識規范警察即時強制權對于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現實重要性,充分認識其作為依法治國系列環節中人民群眾感受最直接、最直觀、最普遍的特點,對警察即時強制權啟動的實質條件和程序條件進行補充立法,增強警察即時強制權規范行使的可操作性、可檢視性、可監督性,以及公民權利受侵犯時的救濟制度保障能力。那么,有沒有明確的原則和標準對于警察即時強制權進行規范呢?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雖然法律傳統迥異,但是都殊途同歸地發展出了比例原則作為規范行政權的“黃金規則”。下文僅以德國和美國為例對比例性原則進行闡釋。
三、德國比例性原則對于警察即時強制權的規范
即時強制是德國行政強制執行制度中的獨特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紀末,由普魯士高等行政法院對“直接強制”所進行的擴張解釋,即“執行行政處分之直接強制”和“無須行政處分并履行法定告誡程序之直接強制”。后來學者弗萊納稱呼后者為“即時強制”,邁耶借助緊急避險、正當防衛以及民法上自助行為等概念,將其發展成為警察自衛權、防止刑事犯罪行為以及警察緊急權三項強制制度。這三類強制行為的共同特征是:強制權的實施無需以行政處分為前提。邁耶的這一理論對于即時強制的后續發展產生了較大影響。
在德國準確地界定警察在國家行政運行中的任務與角色、防止警察權之恣意妄為,避免“警察國家”的影響貽害公民,一直是警察法學重要研究課題。在法治主義理念的統治下,警察權被限制在“危險預防”的范圍內,即對于已經發生或者即將發生的危險在制止的范圍內可以采取警察活動,只有在保護重大法益的情形下,才例外規定警察于危險發生之前的領域也可以采取危險預防措施,包括行政上的危險預防以及犯罪預防,〔1〕Martin H.W.M?llers,W?rterbuch der Polizei,2.Auflage,C.H.Beck Müchen 2010,S.767(Gefahrenvorsorge).其目的是為了防止警察權的濫用和自我授權,易言之,警察的職責在于危險預防,包括行政上的活動和刑事上的措施都是為了預防危險,并且限制在危險預防的范圍內,因此,社會福利并不在警察的職責范圍內,而且,如果危險并不緊急也不需要采取嚴格的預防措施,“只有在必要時,國家才有理由限制個體自由,如此才能保障所有人的自由與安全”。〔2〕Carl Gottlieb Svarez,Vortr?ge über Recht und Staat,Hrsg.von Hermann Conrad und Gerd Kleinheyer,Westdeutscher Verlag·K?ln und Opladen 1960,S.486.如此,警察的職責在于預防危險和打擊犯罪,包括行政和刑事兩個部分,但是,只有在必要的時候,為了國家安全與公共秩序等公共利益,才能對公民權利進行一定程度的限制或調整,以便及早發現和預防犯罪、有效打擊和懲罰犯罪。這便是對公民權利進行限制或調整的正當性基礎,或者“目的正當性”,〔3〕有學者認為目的正當性在傳統的比例性原則中存在缺失的問題,并力圖對比例性原則進行重構,但其實,目的正當性是比例性原則的前提或者背景,沒有目的正當性何來比例審查的問題?兩者的確是肝膽楚越,但是比例性原則的規范結構中不存在目的正當性的論證,因此在正式談及比例性原則之前先行闡釋目的正當性。參見劉權:《目的正當性與比例原則的重構》,《中國法學》2014年第4期,第133頁。即為了公益而對公民權利進行適當的限制或調整。個體總是生活在社會群體之中,個體的權利也存在與其他個體發生沖突的可能性,并且負有尊重他人權利的義務,為了維護共同生活之社會的背景,更好地行使個體權利,有必要對個體權利寓于其中但是又不能為個體所獨享的社會公益進行保護,因此,除非為了公益保護之目的,并且采取的措施與保護目的相契合,否則不得限制公民權利。這便是警察權啟動的實質標準。
法治國的基本思想是保障公民權利,無論是立法、行政還是司法,在干預公民權利之時,應當同時具備形式合法性與實質正當性,并非就只要經過合法程序所產生的結果就是正當的,還應當經過目的正當性和比例性原則的檢測。相比較而言,行政對于公民權的干涉更多,也更難以防范。因此,不僅要求任何涉及公民基本權利的行政行為都應當事先得到法律授權(法律保留原則),制定具有明確性、預見可能性與可信賴性具體的法律進行規范(法的安定性),而且手段與目的之間應當符合比例性原則,確保公民免受行政權的“突襲”和“侵擾”。這其中,比例性原則被公認為是防止行政權擴張和濫用的最有效的、具備可操作性的標準。“合比例的思想首先在警察法領域發展成為具有規范性原則性格的比例原則,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所謂‘國家權力對人民權利的侵害’無疑的是相當清楚且具體地表現在警察法的相關措施中的。因此,在德國,比例原則首先適用于包括行政處分與強制執行在內的警察法領域,而后逐漸發展成行政法領域中的普遍適用的原則。”〔4〕參見蔡宗珍:《公法上之比例原則初論——以德國法的發展為中心》,《政大法學評論》1999年第62期,第83頁。正是比例原則為行政行為確立了剛性標準,提供了審查的標桿。
比例性原則,又被稱作“過度禁止”原則,淵源于19世紀德國的警察法學和行政法學,思想淵源可以追溯到1215年英國自由大憲章中關于犯罪與刑罰衡平的規定,1895年德國奧托·邁耶首次將必要性原則稱為比例原則,認為“被允許的強制不能重于所欲達到的目的”,二次世界大戰后隨著德國基本法的制定,經由聯邦憲法法院的解釋,后來逐漸發展成為一項重要的憲法原則。〔5〕Rupercht v.Krauss,Der Grundsatz der Verh?ltnism??igkeit,Hamburg 1955,pp.1-2.1958年的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關于“藥房案”的判決,〔6〕BVerfGE 7,377-Apotheken-Urteil.成就了經典的“三階理論”,亦稱為“構成原則”,也可以說是比例性原則的規范結構,即手段的妥當性或適應性、必要性和狹義的比例原則,三者在法院對于個案的判斷和思維方法上有著遞進的層次,且具有逐級強化的作用,亦即構成所說的“層次秩序”,經由三個階段的順序判斷為行政行為劃定邊界。我國臺灣地區學者蔡宗珍認為,當國家行使公權力而與公民基本權利發生沖突時,就必須評價某種審查標準來判斷上述公權力的行使是否符合憲法精神,是否合理,于是便有了比例原則,作為保護基本權利而“加諸國家之上的分寸要求”。〔7〕參見前引〔4〕,蔡宗珍文,第83頁。因此,比例性原則需要根據三個階段分別進行檢視,以審查行政行為是否符合比例原則的要求。所謂的“妥當性”(適應性、適合性),是指所采取的手段能夠達到其所追求的公益目的。當行政機關存在“自由裁量”空間時,如何選擇適合實現公益目的的途徑和手段,便成為具體行政行為之前的先行行為,并受到比例原則的檢討,不能達到公益目的、以追求公益目的為幌子甚至與公益目的背道而馳的手段則不符合妥當性的要求。“妥當性”的翻譯更能夠凸顯行政裁量的謹慎、對于公民權利的尊重和對于法律的敬畏,因此比單純地直譯為“適應性”更能反映該階段的本來內涵。所謂的“必要性”,則要求行政機關在眾多同樣能夠達成其所追求公益目的之手段之中,必須選擇對公民權利侵害最小的一種。因此,所謂的必要其實是最小侵害的同義詞,是從對公民權利的侵害無可避免而言,選擇最輕的、最溫和的、不利影響最小的手段。“大炮打蚊子”“殺雞用牛刀”的俗語,所表達的就是典型違反必要性原則的生活事例。之所以如此要求,不僅可以從國家主權和民主主義出發進行論證,更可以認為,如果行政行為“不計后果”則無法達成社會福利最大化之最終目的。因此,要求行政行為所欲達成的公益目的應當大于所損害的公民權利,此即為第三階段的“狹義的比例性原則”的涵義,也有學者據此稱之為“法益相稱性”,〔8〕參見前引〔4〕,蔡宗珍文,第79頁。因為該原則主要針對法益之間的關系而言,更能體現該原則的特征。第三階段的判斷實質是“法益衡量”,只不過在公法領域“法益衡量”的對象為行政行為所追求的“公益”和所損害的“私益”,而且兩者之間不能懸殊太大,否則即使符合妥當性和必要性的要求,行政行為也會因為不相稱而被判定不合理,德國聯邦憲法法院經常使用“可合理忍受”的概念從權利受到影響的公民側面論證狹義的比例原則。亦即,公民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容忍行政行為在追求公益目的時對于公民權利的損害。或者說,在多大程度上忍受這種侵擾可以被認為是合理的。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公民權的范圍就是對行政權尤其是警察權的限制。總而言之,惟有經過妥當性、必要性和相稱性三個階段的、按順序的判斷才能在整體上說明行政行為是合理的,如果經過前一階段的判斷已經得出不合理的結論,其實并無必要再進行下一階段的判斷。
比例原則的適用針對的必須是具有自由裁量空間的行政行為,如果是強制性的行政行為,不存在行政機關自由裁量的可能性,則無需適用比例性原則進行審查。〔9〕當然這里面仍然存在著立法是否符合比例性原則的問題,并成為違憲審查的標準,現時的比例性原則已經成長為一項憲法原則。就警察即時強制權而言,無疑屬于存在自由裁量空間的行政行為,而且其特殊性在于根本無法事前就啟動盤查、留置、搜查等強制行為進行細則規范,甚至只能依靠警察的經驗對是否存在犯罪行為和公共危險作出判斷,只能依靠警察根據現場情況即時作出決定。而且也不能要求警察采取即時強制權必須事前取得司法令狀,這不但是不必要的,而且也是不恰當的,只會導致貽誤控制犯罪的最佳時機,造成公民人身危害、財產損失甚至公共危險。因此,只能通過授予警察以即時強制權根據現場情況進行自由裁量。當然,自由裁量并非完全是“自由”的,而是需要依據比例性原則作出臨場處置。
在德國,比例原則是對“人的尊嚴不可侵犯”和“國家權力尊重和保護人的尊嚴”〔10〕Gerichtsverfassungsgesetz(GVG),§1.之義務的體認和莊嚴承諾,不僅是衡量行政行為是否恰當的實質性規范,還是憲法法院進行違憲審查的實體性標準,是一條憲法性原則,在涉及基本權限制的范圍內對立法進行合憲性審查。其實質是調和社會公益與個體權利之矛盾與沖突,最大限度地擴大社會公益,同時將對于個體自由與權利的妨礙限制在最低限度。可以說,公權力(包括立法、司法和行政行為)對人權的“干預程度”在很大程度上也體現了社會的進步程度和活力大小。
四、美國必要性原則對于警察即時強制權的規范
雖然英美法系更加注重正當程序,通過法定程序的防范行政機關對于公民權利的侵害,然而在具體的案件審判中也會以比例原則對行政行為的必要性進行審查。只不過相比較德國的比例原則提供的是一種“套餐”而言,英美法系采取的是“單點”型的個案審查的模式,在違憲審查中尤其如此。〔11〕參見許宗力:《基本權的保障與限制(下)》,臺灣《月旦法學教室》2013年第14期,第60頁。易言之,在英美法系中也存在比例原則,甚至可以說法治國家下都會要求以比例原則對公共權力進行約束。
談到美國警察的即時強制權不得不談的就是“特里訴俄亥俄州案”,〔12〕392 U.S.1(1968),Terry v.Ohio,on line at:https://www.law.cornell.edu/supremecourt/text/392/1.該案的爭議焦點不在于警察行為的抽象合理性問題,而在于“搜查與逮捕”過程中發現的不利于上訴人證據的可采性問題,但是該判例“就警察的日常執法活動和個人的‘街頭’經歷而言,在最高法院關于第四修正案的判例中,沒有任何一個判例具有比它更大的實踐影響”。〔13〕[美]約書亞·德雷斯勒、艾倫·C.邁克爾斯:《美國刑事訴訟法精解》(第1卷·刑事偵查),吳紅耀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281頁。不但因為該判例厘清了許多的混亂思想和觀點,更重要的是確定了警察即時強制權的啟動標準和執行的必要性原則。擇其要,該判例確定了以下規則:
一是,警察即時強制權也應當受到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的約束。在該判例中,法院區分了為了尋找武器的“拍身搜查”(亦稱“特里搜查”)與全面搜查、調查性的“截停”與逮捕的區別,但是認為以上這些警察行為都屬于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的范圍,〔14〕392 U.S.1(1968),p.8.刻意區分并且將“拍身搜查”與“截停”排除在憲法第四修正案范圍之外的說辭是“咬文嚼字”,〔15〕392 U.S.1(1968),p.16.“除非法律有明確和毫無疑義的規定,人人享有不受他人限制和干涉的人身自由,沒有任何權利比這項權利更加神圣或者被普通法更加細致地保護”,“只要一人懷有‘合理隱私期待’,他便享有不受政府無理侵擾的權利”。〔16〕392 U.S.1(1968),p.9.判例還駁斥了那種認為“截停”與“拍身搜查”,只不過引起了當事人些微的不方便和微不足道的屈辱、為了高效執法根據警察的懷疑可以恰當實施的觀點,認為“這是對公民人格尊嚴的嚴重侵犯,可能造成巨大屈辱并引起強烈憤恨,因此不能如此輕松地一筆帶過”。〔17〕392 U.S.1(1968),p.17.聯邦德國《基本法》在第1條就規定了“人格尊嚴不可侵犯”,那種以損害人格尊嚴為代價而執法的觀點實在是因小失大,著實不可取。
二是,警察即時強制權應當遵守必要性(比例性)原則。法庭在判決中認為,警察應當盡可能地在事前取得搜查和逮捕的司法令狀,但是現在處理的是需要警官在巡邏中根據現場觀察臨場處置的事宜。這些行為在歷史上不曾,在實踐中也不能夠被納入司法令狀程序中,相反,它們是需要在憲法第四修正案關于禁止不合理搜查和逮捕一般條款的行為。〔18〕392 U.S.1(1968),p.20.隨后,法庭比較了需要考慮的“政府利益”之一,即有效地預防犯罪和偵查犯罪,由于警察的盤查行為給特里造成的人身自由的侵擾是否正當的問題,以及減少在執法過程中所受到的安全威脅與個人不可侵犯的尊嚴之間的平衡問題,認為不能無視執法人員保護自身安全的需要,也不能無視因缺少逮捕理由而遭受暴力侵害的無辜者的期待,必須認真評估警察在此時被授權進行武器搜查時個人權利因此而受到侵擾的實質性程度,需要對這些因素進行合理平衡。最后,法庭認為逮捕中附帶的搜查和有限的武器搜查在搜查的目的、屬性和范圍上存在差異。因此,必須將后者限制在搜查武器以防止傷及警察以及附近其他人的必要限度內,并且切實地使等級低于全面搜查,盡管這種搜查對于公民而言仍然是一種嚴重的侵擾。〔19〕392 U.S.1(1968),pp.21-26.因此,警察在截停與盤問等調查過程中需要迅速地作出如何保護其自身和其他人免受可能危險的決定,并采取有限的行動來實現這一目的。法庭最后認定,警察執法記錄證明警官的當時的行為是溫和的。〔20〕392 U.S.1(1968),p.28.
可見,法院在判決書中通過論證對公益與私益進行平衡或者說“法益衡量”,同時注重警察在執法中的安全需要,允許沒有司法令狀的“拍身搜查”,但是目的只能是搜查武器,并限制在防止警察和其他人受到傷害的必要限度之內,為此,即時強制權需要限制在與此目的相匹配的“有限行動”中,否則獲得的證據可能會因為非法證據而在將來的庭審中被排除。雖然法庭并未明確提出比例性原則,也沒有類似德國如此明確的比例性原則的規范構成,但是仍然論證了目的正當性、達到目的之手段的必要性和相稱性。因此,“特里訴俄亥俄州案”為警察行使即時強制權確立了必要性(比例性)原則,這仍然是當前美國警察執法過程中必須遵循的原則。
三是,啟動盤查等即時強制權的標準是“合理懷疑”。警察啟動“截停”并進行“拍身搜查”的標準是,有理由相信其所面對的是一個持槍的危險分子,而不論這是否能夠成為將其逮捕的理由,警察不必絕對確定被搜查者攜帶武器,只要是一個合理謹慎的人足以相信其人身安全或者其他人的安全處在危險之中即可。〔21〕392 U.S.1(1968),p.27.為了論證警察采取即時強制權的必要性,法院還引用了美國聯邦調查局《美國1966年度統一犯罪報告》的內容:1966年全國有57名執法人員在值勤中死亡,自1960年以來的7年內死亡人數達到335人。1966年有23851起針對警察的襲擊事件,其中9113起造成警員受傷。1966年死亡的57名警官中有55人死于槍傷,其中41人被容易秘密攜帶的手槍所傷,剩下的兩起死亡案件中犯罪人使用的是匕首。〔22〕392 U.S.1(1968),n.21.因此,為了保障警察和其他人的安全,有必要賦予警察進行“截停”和“拍身搜查”的權力。
由于“拍身搜查”不同于“逮捕中的附帶搜查”,因此無需以防止犯罪證據毀滅或消失作為搜查的正當性理由,此種情形下唯一的正當化理由是為了保護警察以及附近其他人的安全,也正因為這個理由,搜查行為必須合理地限制在發現槍支、刀具、棍棒以及其他潛在的可能被用于攻擊警察的工具的前提下。〔23〕392 U.S.1(1968),p.29.該案中的警官嚴格將其行為限制在搜查是否有武器以及對武器威脅進行解除的最小必要性的限度之內,同時也沒有進行有關犯罪證據方面的普通搜查,因此,“拍身搜查”所起獲的槍支等證據不能進行非法證據排除。最后,法庭得出肯定結論:這種搜查是合理的,符合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的規定,任何被搜出的武器可以被恰當地作為指證該犯罪行為的證據。〔24〕392 U.S.1(1968),p.31.相比較普通搜查而言,美國聯邦最高法院通過“特里訴俄亥俄州案”實質上放松了對于警察行政權的控制,這也是權衡公益與私益的結果,但同時又進行了目的和手段上的限制,可以說找到了恰當的平衡點。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特里訴俄亥俄州案”中針對警察的即時強制權,即“截停”和“拍身搜查”等行為,進行了有針對性的論證,并最終確立了具有操作性的規則,包括即時強制行為的目的、屬性、啟動標準和可采取的措施以及必要性標準等,與德國的比例原則具有異曲同工之妙。在此意義上可以說,“法治國下的比例性原則是為了保護公民而加諸國家之上的分寸要求”。〔25〕M.Oberle,Der Grundsatz der Verh?ltnism??igkeit des polizeilichen Eingriffs,Zürich 1952,S.41.
五、我國警察即時強制權規范化行使的法律對策
關于警察權,理論上存在著一個由“統治”“管理”向“服務”“治理”〔26〕參見顧建光:《從公共服務到公共治理》,《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第3期,第50頁。的轉變過程。警察本身意味著對于秩序、安全、安寧和自由的維護,沒有即時強制權將難以勝任這些任務,但是如果模糊了服務對象、執法宗旨不明、背離法治要求,警察的強制權將很容易迷失方向。因此,應當倡導警察權繼續朝向“治理”模式的轉變。不能把執法與服務對立起來。執法就是服務,執法就是保護,必須遵循治理理念。警察執法本質上是在公民參與下對于法律的執行,而不是把警察置于公民的對立面;公民的參與表現在立法、司法、執法的全過程,這是社會治理的基本要求;同時只有將保護公民權利作為基本執法理念,才能夠真正地走向法治。因此,對于警察即時強制權的規范也應當從此著手,即行使警察即時強制權要基于治理的理念、符合權力設定目的。
一是,嚴格警察即時強制權啟動與執行的實質性條件。警察即時強制權本質上還是行政權,屬于行政調查權的一種,不但應當符合行政法的基本精神,而且最終還可能會涉及憲法問題,即關于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問題。因此,目前亟待解決的就是引入比例性原則,〔27〕我國行政法理論上對于比例性原則也多有介紹,但是至今尚未成為警察法上的指導理論,而且因為違憲審查制度的缺位,行政權與公民權的關系問題至今難有統一的機制進行解決。為警察執法設立“度”上的標準。
以盤查為例,并不是只要是公安機關內部決定、在任何情形下都可以對所有人任意地進行盤查。啟動盤查、留置等即時性強制措施必須符合實質性條件,即“違法犯罪嫌疑”,而且是達到“合理懷疑”的程度,即一般的理性人有事實根據地認為行為人存在違法犯罪嫌疑。禁止僅憑主觀臆測、行為人個人因素〔28〕如僅僅因為當事人的衣著、外貌、民族、性別、膚色或者曾經受過處罰等而啟動盤查。而啟動盤查,嚴禁毫無根據地啟動盤查;經簡單詢問如果沒有進一步的事實證據,在核實身份后應當立即放行,禁止故意拖延、變相限制人身自由。警察即時強制權的行使應當符合比例原則,即綜合評判嫌疑程度、危險程度、周圍環境等采取符合比例的、必要的阻攔和檢查行動,不得明顯超過比例采取強制措施和有形強制力。如無必要不得搜查,不得以羞辱的語言或者方式對當事人進行盤查,警察執法不但應當合法而且應當合理,目的與手段合乎比例。如果發現行政相對人攜帶武器或者管制刀具等威脅警察自身安全或者群眾安全的情形,可以進行符合武器搜查強度要求的人身搜查,以解除武器威脅。可以區分重罪、輕罪還是輕微違法,根據不同的違法性質而采取不同的即時強制措施,原則上除非必要不得采取更為強烈的強制措施。〔29〕2016年12月1日公安部在網站上公開征求關于《人民警察法》(修訂草案)的意見,載http://www.mps.gov.cn/n2254536/n4904355/c5561673/content.html,2018年6月30日。新增五種情形擬允許使用武器,但是,更加重要的是應當在《人民警察法》中明確規定比例性原則作為一般條款,以明確的標準規范警察執法活動。
當然,不符合強制權啟動的實質性條件,并不影響警察與當事人的“攀談”或者在“當事人同意”下,進行一些適當的調查活動。〔30〕這里涉及盤查究竟是“任意調查”還是“強制調查”的爭論,但即使盤查屬于強制調查,也不妨礙警察對當事人的接近以及與當事人之間的“攀談”。但是,如果當事人反對則應當無條件地允許離開。“任意調查”的概念是對法律保留原則的變通,當事人僅在道義上而并非法律上存有協助調查的義務,因此不能采取強力迫使公民接受調查。但是其啟動和執行也需要符合比例原則,并符合正當性目的。如果當事人反對或者不配合,除非發現新的證據和事實,應當即刻允許當事人離開,這是公民的權利,公民可以保留自己的權利而不配合,此時決不能是因為態度不好而升級強制措施,從而逾越即時強制權的底線。采取即時強制權啟動的實質性條件不但是權力的界限,而且是權利的保障,更是事后救濟和追究法律責任的根據。
另外,對于設卡盤查的條件應當立法予以明確:除非情況緊急或者事態重大、為防止重大損害的發生,未事先經過法定程序審批,不得設卡盤查。即使設卡盤查也應當符合強制權啟動的實質性條件、符合行政權行使的比例原則、符合權力行使的目的,而且審批文件中必須明確設卡盤查的時間和范圍等,并由著裝警察設卡盤查。另外,依據案件和當時的情勢,是否到了必須對所有的人都進行盤查的嚴重程度也要依據比例原則進行具體判斷。
二是,完善警察即時強制權啟動的程序性條件。“警察是侵害公民各項權利的最大惡”,〔31〕黃學賢、崔進文:《警察行政行為的司法控制探討》,《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1年第2期,第152頁。域外國家和地區大多通過令狀制度通過司法權對警察行政強制權進行監督和控制,尤其是對于限制和剝奪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需要進行事前審查,以獲得采取強制措施的令狀,極大地保護了公民權利,防止警察權力的濫用,這也是“法律先于權力、程序優于權利”的根本體現。在我國,警察行政強制權的行使均是內部審批,缺乏外部監督和權力制約,這也是當前侵犯公民權利比較集中、群眾意見反映強烈的部分。建議對警察行政強制權進行司法約束。在我國,目前可以通過向檢察官獲取令狀的方式,對警察的行政強制權進行規范,例如,對于設卡盤查要求事先取得檢察機關的批準;對于繼續盤問需要在12小時之內向檢查機關報批、接受檢察監督等,可以考慮所涉及公民權利的種類、發生的場所、緊急程度等進行立法。
令狀主義以有效防止警察權力濫用、更好地保護公民權利為旨歸;但卻是以降低警察執法效率和社會防衛能力為代價的,在自由、安全和秩序的各種法律所保護的價值上,也會存在保護的優先性問題。因此,令狀主義通常會有例外的規定,對于嚴重影響社會治安的暴力犯罪、社會騷亂、毒品犯罪、有組織犯罪、恐怖主義活動犯罪等在啟動、調查等程序方面可以適當放松。例如,情況緊急或者在巡邏、走訪中發現違法犯罪活動需要及時處置的,可以在事后取得令狀,或者事后立即接受檢察等。
當然,警察即時強制權啟動的程序性要求還來自公安機關的內部審批,在當前法律法規規定盤查、留置、搜查、扣押、傳喚等審批權限前提下,補充規定即時強制權的行使應當在盡可能早的情況下向指揮中心報告,進行登記和備案;在情況不緊急的情況下,還應當事先向指揮中心報備,以便取得指揮中心的指導、配合或增援,同時也是一種內部監督。除了警察即時強制權啟動的程序性條件之外,在實施即時強制的過程中應當具備最基本的程序性條件。例如,應當通知當事人到場,當場告知當事人采取行政強制措施的理由、依據以及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和救濟途徑,聽取當事人的陳述和申辯,制作現場筆錄等。當場或者采取措施后立即通知當事人家屬實施行政強制措施的行政機關、地點和期限;在緊急情況下當場實施行政強制措施的,在返回行政機關后,立即向行政機關負責人報告并補辦批準手續;實施行政強制措施的目的已經達到或者條件已經消失,應當立即解除等。
三是,警察即時強制權的可檢視性要求。警察即時強制權由于其臨場處置性的特點,在實踐中出現了很多的問題,缺乏可供檢視的監督是其重要原因。在當前數字化時代,警察活動經常被外界的各種視頻音頻所記錄,因此,警察在執法的過程中也應當主動記錄、保留和提供可檢視性的文件,這一點不但對于執法活動非常重要,而且也是主動接受監督的重要途徑:第一提供證據,有效地保護警察執行法律;第二接受監督,提高警察執法的公信力。可檢視性要求不是為了讓當事警察自證清白,而是一種職責要求,是執法義務,證明執法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同時也是對案件進行處理的證據之一。可檢視性的文件包括文字記錄、視頻或者音頻記錄、處警報告、審批文件等。2016年6月14日,公安部印發了《公安機關現場執法視音頻記錄工作規定》,可檢視性得到了極大的提高,但是由于這個規定屬于部門規章,仍然存在如何接受監督的問題。可以立法規定檢察機關在何種情形下介入警察執法調查,如何調取現場執法視音頻等,以保證調查結果的公正性和可信度。
建立統一的警察執法投訴中心,對于所有的投訴都要記錄在案,并轉交相關部門進行核查,反饋處理結果。對各種投訴進行詳細的數據統計分析,以便總結警察執法可能存在的問題,對重點部門、重點領域、重點地區、多發行為進行重點督查,有針對性地進行整改。
四是,警察即時強制權違法行使的法律救濟。“無救濟則無權利”,關于警察即時強制權的各種規范性文件,最大的問題在于沒有規定救濟條款。即,如果當事人認為自己的合法權利受到了侵害如何訴請司法保護的問題。與域外國家相比,由于我國實行違法與犯罪截然分開的體系,因此,在國外屬于違警罪和輕罪的大部分違法行為,在我國都是作為治安處罰的對象進行管理和裁決的。這直接造就了我國極具特色的違法犯罪處理機制:第一大量的違法行為直接由公安機關進行內部裁決和復議,除了行政訴訟之外,很難受到司法的審查和救濟,外部監督缺乏;第二公安機關兼具治安警察與司法警察的職責,在違法犯罪案件的發現、偵辦和處理過程中存在一些上下其手、左右逢源的情況。有鑒于此,從長遠來看,區分治安警察與司法警察,設立治安法庭并將治安案件的處罰權移交司法,是限制警察權、救濟公民權利、維持警察執法之社會公信力的不二法門。這也與以審判為中心的司法改革精神相契合,經由中立第三方審核的處罰最起碼實現了程序正義。
五是,賦予公民當場申辯的權利。通常而言,即時強制屬于法定權力性的行政活動,所以除非法律明確規定的情形,行政相對人不能運用民法或者刑法上的正當防衛或者緊急避險等理由拒絕接受警察機關行使職權的行政管理活動;但是,警察即時強制權又屬于侵害行政,一旦發生侵害后果將無法完全消除,因此警察即時強制權在實施過程中均應當符合比例性原則和必要性原則。在緊急事態已經得到控制的前提下,從人權保障的角度出發,應當場認真聽取公民的陳述和申辯,對于明顯不恰當的即時強制措施應即刻解除或者變更,防止損害后果的進一步擴大。這也是貫徹以人民為中心思想,規范警察即時強制權的內在要求。
六是,完善警察執法責任追究機制。再好的法律也需要人來執行,法治思想淡薄、特權思想嚴重、部門利益糾葛等都是嚴重影響執法規范化和執法公信力的重要因素。因此,除了進行法治思想教育之外,還需強化責任追究機制。警察即時強制權的不規范化行使問題,有的是出在對法律條文的理解上,有的則出于對法律條文的曲解上,前者是執法的水平問題,可以通過教育培訓不斷提高,后者則是違法執法的問題,需要通過紀律處分、追究法律責任等予以懲戒以儆效尤,直至開除公職以純潔警察隊伍。惟有從正反兩個方面加強對執法民警的教育與管控,才有可能不斷提高警察執法水平、維護公民權利。還可以采取“負面清單”的方式,由公安機關以規范性文件的方式分類、分層、分領域地列舉違法執勤的方式和表現,不但是極好的教育方式,更可以有針對性地對警察執法進行規范。
需要指出的是,紀律處分和法律責任的追究還應當促進警察職權的積極履行,嚴格依法履職。應當在立法上注重“正面清單”的列舉,強調警察即時強制權在緊急事態下及時處置的效能,不得拒絕或者拖延履行法定職責,在符合比例性原則和必要性原則的前提下,加強對于警察履行職責的積極要求。加強警察執法手段的多樣化和細致化立法,確保警察執法手段和制止強力能夠與突發事態的嚴重性程度成階梯性匹配,確保警察即時強制權的依法實施。
“整個行政法其實都可以看作是憲法的分支,因為它直接從法治國、議會主權、司法獨立等憲法原則中產生,而且它對于確定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之間的平衡貢獻良多。”〔32〕William.Wade and Christopher.Forsyth,Administrative Law,Clarendon Press,1994,p.6.法治國家,行政法的制定與執行、行政行為的出發點與落腳點皆以公益為目的,然而公益并非獨立于私益的權利或者利益。行政權作為公益的代理人其行政行為最終目的仍然是為了維護公民權利與利益,這不僅涉及“法律保留”或者法律授權的問題,還涉及行政行為之目的正當性以及進退取舍之尺度。因此,警察即時強制權的規范化行使也應當以保護公民權利為旨歸、基準和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