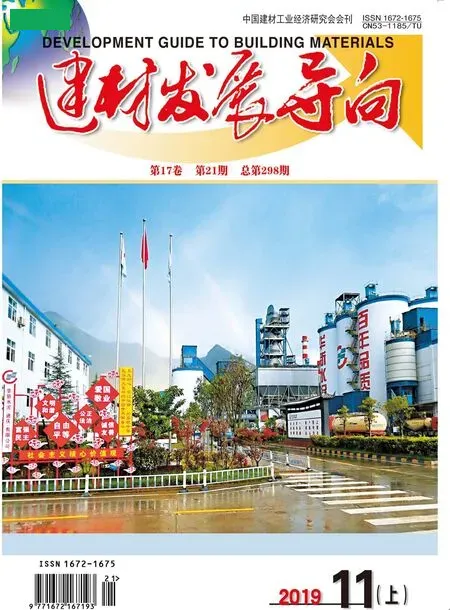鄉村振興視角下我國鄉村空間規劃研究進展
楊曉艷
(大同市規劃設計院,山西 大同 037000)
自2018年十九屆三中全會決定開展國家機構改革,組建自然資源部以整合城鄉規劃、土地利用規劃和主體功能區規劃等職責,形成統一的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并監督實施以來,圍繞國土空間規劃的一系列改革在持續進行。同年9月自然資源部三定方案(定職能、定機構、定編制) 出臺,使得國土空間規劃體系的構建有了組織運行的保障。2018年11月《關于統一規劃體系更好發揮國家發展規劃戰略導向作用的意見》印發,標志著在國家層面正式確立了國家發展規劃和國家級專項規劃、國土空間規劃、區域規劃的協同關系。2019年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審議通過《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建立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并監督實施的若干意見》并于5月正式印發,標志著我國正式確立了“五級三類”的新時代國土空間規劃體系,并將其作為生態文明體制改革下國土空間開發保護制度的核心抓手之一。
1 城鄉區域規劃追求的目標
城市化是伴隨工業資本主義發展而席卷人類社會的歷史趨勢。通常認為,城市化是一個大量人口不斷集中、形成城市的過程。人口的聚集帶來了城市數目增多、城市人口、用地規模擴大,城市人口在總人口中的比重不斷提高。與城鎮化進程相伴生的是廣大鄉村地區的衰敗,這是不容回避的事實。近現代以來,面對鄉村的破壞與衰敗,一些知識精英在各地開展鄉村建設運動,進行地方自治現代化與社會改良。但筆者認為,鄉村建設與城市建設實際上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鄉村設計和都市設計雖不同,但兩者應在一條聯絡線上,各項計劃要彼此聯成一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逐步進入快速發展的軌道。快速城鎮化進程受到全球資本流動與積累的驅動,城市不動產“動產化”,農村土地“城鎮化”,農村成為城市建設用地的來源,實際上形成了資本邏輯下的“空間生產”。資本邏輯下的大規模快速城鎮化,取得了巨大社會經濟成就,同時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問題,包括:住房難、看病難、上學難、就業難等城市社會問題、農村衰敗、鄉土文化消逝等農村社會問題,以及土壤、水、空氣污染等環境問題。這些問題集中涌現且相互關聯,堪稱“城鎮化危機”。
2 突出鄉村規劃的自身特色
改革開放后,我國鄉村地位和作用已發生了深刻變化和戰略調整,隨著鄉村振興成為事關歷史全局的國家戰略,鄉村規劃也開始步入新時代。2018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審議《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要求真正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擺在優先位置,各地區各部門要樹立城鄉融合、一體設計、多規合一理念,抓緊編制鄉村振興地方規劃、專項規劃或方案,做到鄉村振興事事有規可循、層層有人負責。國家對鄉村振興要求與戰略部署,將成為今后及相當一段時期內編制鄉村規劃的根本動力。
城鄉關系歷史變遷表明,鄉村作為一種空間存在的形態,自古以來,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即從古代的著民之所,到近40年來大規模快速城鎮化與工業化時代土地之源。如今鄉村空間已經發展成為一種社會存在與互動的形式,未來鄉村規劃的基本方向是城鄉共生、社會公平、空間共享,鄉村規劃要基于新型城鄉關系,凸顯鄉村空間的經濟、社會與生態價值。
3 展望
根據前文對鄉村振興提出前后鄉村空間規劃研究的梳理與總結,為給鄉村社會、經濟、政治、生態和文化等方面全面振興提供合理的空間規劃,提出了以下幾點研究展望:
首先,確立農業產業核心地位,形成以農業為核心的第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空間規劃。產業興旺是鄉村振興的基礎,農業是鄉村社會經濟發展的基礎。當前國內學者關注于鄉村旅游業規劃研究,出現過度強調農業旅游化而忽視農業在工業、科技和文化等其他價值的現象。此外,鄉村振興比新農村建設和美麗鄉村建設有著更高的產業融合發展要求,旨在通過延長農業價值鏈,形成以農業為核心的農業加工業、旅游業等第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因此,鄉村產業空間規劃是基于明確的農業產業核心地位,統籌農業及其延伸的第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空間需求,形成有利于第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空間規劃。
其次,統籌“三生+三產”空間規劃,用“一張圖”滿足振興鄉村的空間發展要求。鄉村空間由鄉村聚落空間、生態空間、基礎設施網絡空間、產業與經濟空間、社會組織空間、鄉土文化空間等物質空間和非物質空間構成。即鄉村空間包括生活空間、生態空間和生產空間,也包括第一產業空間、第二產業空間和第三產業空間,每一種空間都可以形成對應的空間規劃圖,并且每種空間規劃圖存在差異,若差異太大則容易造成規劃沖突等問題。
4 結語
新時期的國土空間規劃必然是一個系統規劃,橫向到邊涉及廣袤的城市—鄉村—自然空間,縱向到底統籌從國家、省、市、縣直到鄉村的國土空間中的人與土地、“山水林田湖草”和各類其他資源要素的開發保護關系,其基礎邏輯如何是當前需要預先進行探索和論證的重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