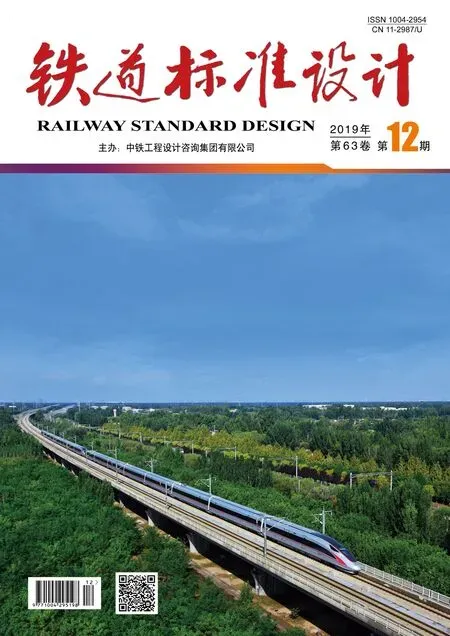軟弱地層盾構隧道側穿房屋基礎沉降特性分析
魯茜茜,蹇蘊奇,王先明,王士民
(西南交通大學交通隧道工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成都 610031)
1 概述
近年來,盾構法憑借自身獨特優點成為城市地鐵隧道修建的主流工法[1]。在城市地鐵修建過程中,盾構隧道不可避免要下穿房屋建筑等上部結構,而盾構隧道施工產生的地層變形可能會造成房屋的差異沉降[2],導致房屋出現不同程度的外觀、功能以及結構損傷,尤其是含水率高、壓縮性強、抗剪強度低的軟弱地層,地層承載能力及自穩能力差,盾構穿越房屋群施工擾動對地表既有建筑物的影響更大,施工安全控制更為困難。
目前國內外學者在盾構施工對地表既有建筑物影響方面已開展了大量研究。 Skempton等[3]通過對98個工程案例的分析總結,得出盾構施工地表所允許的總沉降值和差異沉降值;盾構施工無地表建筑物時,地面沉降分析經驗公式最為經典的是Peck公式,Franzius[4]、韓煊等[5]在此基礎上,考慮既有建筑結構對地面沉降的約束作用,對Peck公式進行相應修正;J. B. Burland[6]通過對盾構施工周圍沿線既有建筑物的環境風險進行分析,給出了計算地表沉降的方法,并對盾構施工造成既有建筑物的損傷情況進行了分類; Storer J. Boone[7]將基礎視為柔性基礎,考慮結構性質以及地層的應變,從既有建筑物的剪切變形和主張拉應變對其損傷程度進行了評價;夏軍武[8]、丁智[9]采用彈塑性理論建立了能夠體現土體與建筑物間協同作用的力學理論模型,分析了盾構施工對鄰近既有建筑物變形及內力分布的影響規律;陳自海等[10]結合實例監測,采用數值模擬方法研究了軟弱地層條件下注漿壓力、漿液彈性模量、土艙壓力等施工參數對地表沉降的影響規律;張亞洲等[11]依托南京緯三路過江通道,利用FLAC3D有限元軟件分析了盾構施工對大堤穩定性影響,并探討了不同注漿效果、堤岸坡度以及隧道埋深對其穩定性的影響;閆國棟等[12]針對不同圍巖及不同埋深下盾構隧道穿越既有房屋情況,采用FLAC3D軟件分析了地表沉降及房屋變形規律;李方明等[13]利用有限元軟件PLAXIS,對地鐵車站地下連續墻施工對鄰近房屋的影響開展研究,研究表明軟弱地層變形具有一定的滯后性;董繼濤等[14]利用數值計算分析了軟弱圍巖條件下盾構近距離穿越密集房屋群施工對房屋安全的影響,并提出了相應的施工控制措施;劉國棟等[15]依托廣州軌道交通14號線,提出水平定向鉆孔與地面注漿相結合的地層加固技術;鞠鑫[16]依托廈門地鐵某區間段,采用雙孔平行隧道地表沉降計算公式、數值模擬及現場監測 3 種方法,揭示雙線地鐵隧道盾構施工引起的地表沉降分布規律和地表動態變形特性。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可為軟弱地層盾構隧道側穿房屋群的沉降控制提供借鑒,但由于地層、上部建(構)筑物以及盾構隧道與建(構)筑物空間位置的差異,既有研究成果尚不能對相關近接下穿工程提供定量指導。此外,針對軟弱地層盾構側穿房屋群導致房屋差異沉降方面的研究尚少,因此,以廣州軌道交通21號線金坑站—鎮龍南站區間土壓平衡盾構下穿均和村房屋群為研究背景,利用有限元軟件ANSYS對軟弱地層盾構側穿房屋群不同施工順序進行數值模擬,從房屋沉降控制角度確定了最佳施工順序,并分析了盾構側穿房屋群施工的影響范圍及沉降規律。
2 依托工程概況
廣州軌道交通21號線金坑站—鎮龍南站區間隧道采用盾構法施工,其中1號中間風井—2號中間風井盾構區間位于廣州市蘿崗區均和村,西起1號中間風井西端頭,沿廣汕公路南北側輔道由西向東行進,下穿大量密集農房后,進入2號中間風井。現選取位于軟弱地層的均和村房屋群作為研究對象,隧道埋深在10.9~16.2 m,管片外徑6 m,管片幅寬1.5 m,管片厚度為0.3 m。區間房屋主要為3層~5層的磚混結構,少量的框架結構,房屋基礎主要為天然基礎和明挖擴大基礎,房屋與隧道平面關系如圖1所示。

圖1 房屋與隧道平面關系示意
根據地質勘探資料顯示,均和村房屋群主要穿越全風化花崗片麻巖和強風化花崗片麻巖,在軟弱地層條件下修建地鐵盾構隧道,通常易引起較大的地層位移及地表既有建筑物的差異沉降,嚴重時可能導致隧道上方既有建筑物發生不可逆損傷,影響其安全及正常使用。
3 盾構側穿房屋沉降特性分析
根據金坑站—鎮龍南站區間工程地質及地表房屋分布情況,選取位于均和村軟弱地層條件下,區間里程為DK31+675~DK31+755的房屋群A、B、C作為研究對象,各房屋群所在區域如圖1所示。
3.1 計算模型
由于房屋群A、B、C縱向跨度80 m,橫向跨度31 m,實踐表明,隧道開挖后的應力和應變,其實際影響僅存在與隧道周圍距隧道中心點3~5倍開挖寬度內[17],因此所建三維數值計算有限元模型尺寸可定為:120 m(橫向X)×50 m(豎向Y)×180 m(縱向Z),如圖2所示。根據實際施工情況,隧道埋深取為12 m,盾構開挖直徑6.4 m,管片外徑6 m,管片幅寬1.5 m,厚度為0.3 m,注漿層厚度0.2 m。在模型X方向施加水平位移約束,在模型底部Y方向施加豎向位移約束,Z方向施加縱向位移約束,模型上部為自由邊界。

圖2 模型地層分布
3.2 計算參數
計算過程中,模型土體采用彈塑性分析,管片、注漿層及房屋基礎則視為彈性體,進行彈性分析,模型中地層、房屋基礎、管片及注漿層均采用Solid45實體單元進行模擬。地層參數均依據《廣州軌道交通21號線金坑—鎮龍南區間詳細勘察階段巖土工程勘察設計參數建議值表》取值,如表1所示。

表1 地層材料參數
管片襯砌采用C50鋼筋混凝土材料,彈性模量為34.5 GPa[18],考慮到接頭對管片襯砌結構的影響,采用剛度折減方法模擬,其橫向和縱向折減系數分別取為0.80和0.01[19],具體物理力學參數見表2。
3.3 計算過程控制
管片幅寬為1.5 m,計算中每一個開挖步長度取兩環管片幅寬,即3 m,每條線開挖步為60步,雙線共120步。采用單元的殺死與激活來模擬隧道的開挖,在開挖掌子面施加均布荷載模擬土倉壓力對掌子面的平衡作用,通過對單元材料賦不同參數模擬管片拼裝、同步注漿以及漿液硬化。具體模擬過程如下: (1)地層自重固結沉降;(2)開挖兩環管片土體,將地層荷載釋放25%;(3)拼裝管片并脫出盾尾,釋放剩余的75%地層荷載;(4)管片脫環后6環范圍內注漿層為未固化狀態,超出6環管片范圍后注漿層變為固化狀態。
3.4 房屋結構模擬
盾構施工過程中,建筑物和地層之間的關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建筑物基礎具有一定的剛度,建筑物隨基礎的變形而變形,需考慮兩者之間變形協調;另一方面建筑物自重通過基礎向地層深處擴散,對受擾動之后的地層應力重分布產生影響[20]。考慮到上述兩個方面,房屋結構基礎采取具有一定剛度和重度的板塊進行模擬,將鄰近隧道房屋結構的自重簡化為豎向的均布荷載施加在板上。根據GB50009—2012《建筑結構荷載規范》,考慮到施工的安全性,本文房屋群產生的均布荷載值取150 kPa[21]。
3.5 房屋沉降監測點布置
對廣州軌道交通21號線所穿越的房屋群A、B、C進行監測點設置,分析各監測點在不同開挖步下的沉降,房屋群A、B、C各取4個監測點,具體布置如圖3所示。
3.6 盾構施工順序比選
由于本區段隧道左右線與上部房屋群的相互位置關系并不呈對稱分布,左右線受房屋群荷載有所不同,施工過程中,隧道左右線不同開挖順序將會對上部房屋群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本節首先對盾構隧道左右線不同開挖順序下,上部房屋群的響應規律進行對比分析,找出最優隧道開挖順序。
3.6.1 先左線后右線
先開挖左線,待左線施作完成再施作右線。房屋群A、B、C在左線貫通和雙線貫通下,房屋基礎沉降云圖如圖4所示。
由圖4(a)可知,當左線貫通時,土體受隧道開挖擾動產生沉降,房屋基礎最大沉降為7.78 mm,最大沉降值位于左線隧道拱頂上方附近區域。由圖4(b)可知當雙線貫通時,最大沉降值向雙線隧道中心偏移,房屋基礎最大沉降值有所增加,達到8.45 mm,增長幅度僅為8.61%。
在此順序下,雙線隧道貫通后,房屋群A、B、C的最大沉降以及最大差異沉降如表3所示,均未超過沉降控制值20 mm。

表3 先左線后右線房屋沉降 mm
3.6.2 先右線后左線
先開挖右線,待右線施作完成再施作左線。房屋群A、B、C在右線貫通和雙線貫通下,房屋基礎沉降云圖如圖5所示。

圖5 房屋基礎沉降云圖
由圖5(a)可知,當右線貫通時,大部分房屋基礎沉降較小,臨近右線隧道房屋基礎產生沉降較大,最大達到10.50 mm。由圖5(b)可知,當雙線貫通時,最大沉降向左線隧道偏移,房屋基礎最大沉降值有所增加,達到13.35 mm,增長幅度達到27.14%。相比先左線后右線的施工順序,此順序下單線貫通和雙線貫通房屋基礎沉降最大值都有所增加,增長幅度分別達到34.96%和57.99%。
開挖過程中,房屋群A、B、C產生的最大沉降以及最大差異沉降如表4所示。相比表3,此順序下,各房屋群最大沉降以及最大差異沉降都有所增加,這是由于先開挖右線,土體的卸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受房屋荷載作用顯著的一側即左線隧道自穩能力,增加了其施工風險。

表4 先右線后左線房屋最大沉降值 mm
結合房屋基礎沉降云圖以及沉降極值,從沉降控制的角度,本研究區段雙線隧道側穿房屋群應優先開挖受房屋荷載影響顯著的左線隧道。
3.7 房屋基礎沉降特性分析
依托穿越均和村房屋群前的有限元分析結果,此區段采取先左線后右線的施工順序,提取左線先行隧道施工有限元分析中各監測點的沉降變形數據,對軟弱地層盾構隧道側穿房屋基礎的沉降特性進行系統分析。
(1)累積沉降
先左線后右線的施工順序下,開挖過程中各房屋監測點沉降曲線如圖6~圖8所示。

圖6 房屋群A監測點沉降曲線

圖7 房屋群B監測點沉降曲線

圖8 房屋群C監測點沉降曲線
由圖6~圖8可知,由于房屋荷載對左線隧道作用顯著,左線隧道開挖完成,偏壓側監測點完成其大部分沉降,在右線開挖過程中沉降增加幅度不大,只有監測點A-3、B-2、B-3在右線開挖過程中沉降會進一步增大。同時各監測點位移沉降存在時空差異,但變化趨勢基本一致。以房屋群A為例,監測點A-2基本位于隧道左線中心軸線處,而監測點A-3則位于隧道左右線中央位置附近,因此, A-2和A-3受隧道開挖擾動大,最大沉降量分別達到12.88 mm和12.59 mm,其中A-2點受隧道左線開挖影響明顯強于右線開挖,而A-3點的沉降受隧道左右線開挖影響較為接近。相比之下,監測點A-1、A-4距離隧道中心軸線遠,受開挖影響小,最大沉降分別為0.89 mm和3.18 mm,即隨著距隧道中線距離的增加,房屋沉降值逐漸減小。
從圖6~圖8可以看出,在盾構掘進過程中,盾構刀盤距監測點前約3倍洞徑,監測點累計沉降小,不超過2 mm。在此之后,監測點開始加速沉降,在盾構穿越監測點10 m左右達到最大,在穿越監測點后約6倍洞徑距離后沉降趨于穩定。
表5為房屋群部分監測點在隧道左線貫通時的最大沉降量占雙線隧道貫通總沉降比例,結合圖3和表5,監測點A-2、C-2、C-3位于左線隧道正上方,其中, C-3位于左線隧道中心軸線左側, A-2和C-2均位于左線隧道中線軸線右側。左線隧道貫通時監測點C-3沉降占其總沉降的比例為95.13%, C-2與A-2相比距離左線隧道中線軸線更近,因此,左線隧道貫通時C-2沉降量相對其總沉降量占比大于A-2,兩者分別為90.33%和89.36%;監測點B-3位于右線隧道外輪廓邊緣,受右線隧道影響相對較大,左線隧道貫通時其沉降量相對其總沉降量占比僅為24.92%;監測點A-3及B-2位于左右線隧道中間偏向右線位置,且B-2距離左線隧道更近,受左線隧道開挖影響更大,左線隧道貫通時其沉降量相對其總沉降量占比也比A-3大,為52.38%。
(2)差異沉降
在隧道掘進過程中,房屋群各監測點累積沉降時空特性并不同步,導致監測點存在差異沉降。通過圖6~圖8可知,各監測點之間的差異沉降同累積沉降變化趨勢相同,都在監測點-3D~6D(D為洞徑)范圍內加速變化,表6為監測點間最大的差異沉降。房屋群A、C被左線隧道側穿,最大差異沉降均在10 mm以上;相比之下,房屋群B被雙線隧道正穿,監測點差異沉降均小于房屋群A、C監測點差異沉降值。

表5 左線貫通最大沉降占雙線貫通沉降比例

表6 監測點差異沉降 mm
4 實測數據分析
依托穿越均和村房屋群前的有限元分析結果,此區段采取先左線后右線的施工順序,并在盾構穿越房屋群基礎前10環左右逐漸放慢掘進速度,在正穿監測點正下方時加大注漿量,來控制既有建筑物變形。根據軟弱地層盾構開挖縱向影響范圍(-3D~6D,D為隧道洞徑),將房屋監測點實測數據分析范圍定為:盾構機距監測點前50環(75 m)作為分析起點,盾構機通過房屋監測點40環(60 m)作為分析終點。
考慮到監測點分布的空間差異,選擇B-3、B-4以及C-2三個監測點的實測數據進行分析,覆蓋了旁穿以及正穿這兩種情況。其中左線隧道開挖后房屋監測點沉降實測數據如圖9所示。

圖9 部分監測點實際沉降值
由圖9可知,當左線刀盤距離房屋中心距離過遠時,各監測點產生微弱沉降,其中刀盤在距離監測點75 m時,各監測點產生的累積沉降變形不足1.0 mm;在刀盤距離監測點20 m左右時,隧道的開挖對各監測點產生較為明顯擾動,各監測點開始加速沉降,使得刀盤到達B-3、B-4、C-2正下方時沉降分別達到4.76,6.11 mm和7.45 mm。在刀盤通過房屋基礎后,土體應力二次釋放,使得地表監測點沉降再次增大,在通過監測點10 m左右達到最大;隨后監測點沉降速度有所減緩,最終在刀盤通過房屋后30 m左右時趨于穩定。
對比圖7、圖8及圖9,可以發現,數值分析與現場實測數據變化趨勢吻合度較高。在數值模擬和現場實測數據中,當盾構通過監測斷面后,均存在一個較為明顯的沉降回彈現象,但現場實測數據中監測點沉降范圍較數值模擬偏大,主要分布在盾構通過監測斷面10~20 m范圍內,且回彈量值較數值模擬結果大。究其原因,沉降值回彈主要源于同步注漿漿液固化和盾構通過后的卸荷作用,而數值模擬僅考慮了漿液固化,未考慮盾構機自重在軟弱地層對地層變形的影響,導致實際施工過程中沉降回彈量偏大。
由于各監測點空間位置差異,所受開挖影響程度有所不同。監測點C-2位移左線隧道正上方,因此,左線隧道通過導致其沉降變化幅度最大,其次是監測點B-4,監測點B-3受左線隧道開挖影響最小。上述3個監測點最大沉降值如表7所示,均未超過房屋沉降控制值20 mm,且略大于數值計算監測點最大沉降值。但鑒于有限元分析考慮的是在完全理想彈塑性條件下進行隧道開挖,而實際施工過程中,地層存在各種不確定因素,表明控制掘進速度和注漿量在一定程度上可降低既有建筑物變形,保證施工安全進行。

表7 實際沉降值與計算沉降對比 mm
5 結論
以廣州地鐵21號線金坑站—鎮龍南站區間盾構穿越密集房屋群為工程依托,采用數值模擬方法對雙線隧道不同開挖順序下側穿房屋群的沉降擾動規律進行研究,并結合現場實測數據進行了分析。主要取得以下結論。
(1)軟弱地層盾構隧道側穿房屋群基礎,應優先開挖受房屋荷載作用顯著的一側,有利于控制房屋基礎變形。
(2)軟弱地層盾構隧道側穿房屋群,在穿越監測點前3倍洞徑至穿越監測點后6倍洞徑范圍內產生的沉降為主要沉降,在盾構通過監測點10 m左右位置,沉降達到最大值。
(3)距離盾構隧道中心軸線越近,受開挖影響越大,房屋累積沉降越大,先行盾構隧道貫通時,其正上方房屋群監測點的最大沉降量占總沉降量比例達到90 %左右,而位于雙線隧道之間靠近先行隧道的房屋群監測點,其最大沉降量占總沉降量比例在50 %左右。
(4)偏離隧道中心軸線房屋群的差異沉降量明顯大于隧道中心軸線上方的房屋差異沉降量。
(5)受盾構同步注漿固化和盾構通過后的卸荷作用影響,房屋群基礎在盾構通過監測斷面后10 m左右的位置存在沉降回彈現象,現場實測沉降回彈量值大于數值模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