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戲曲劇本曲詞的結撰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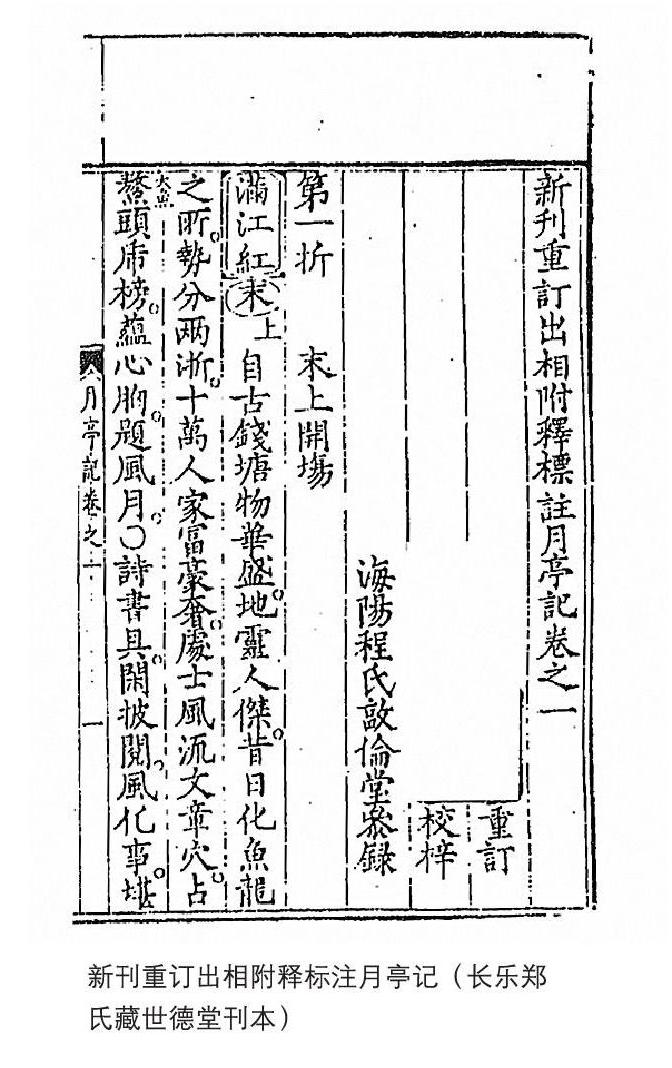


【摘要】 中國戲曲是融曲唱與話白、抒情與敘述于一體的綜合性表演藝術。從形式上看,戲曲劇本上以曲詞為核心,場上以聲唱為亮點,戲曲以融“戲”于“曲唱”、用“曲唱”來演“戲”為表現形式。曲詞的創作方式及呈現形態,可以依譜填詞、依腔填詞,創作符合曲牌要求的句式長短不齊的“詞”式體曲詞;也可以文行腔,即依照戲曲聲唱的特點,遵循聲腔調子,采用七字句或十字句的“詩”式體結撰曲詞。在戲曲中,曲詞既可以傳唱即時的情境;也可以成為形式工具,進行敘述,鋪述經歷過的情、事,推動戲曲情節的展開。精心構造,完成即時性的情感發抒與歷時性的情節展開,是曲詞結撰必須考慮的問題。
【關鍵詞】 戲曲劇本;曲詞;抒情;敘述;代言
[中圖分類號]J80? [文獻標識碼]A
戲曲之所以稱之為“戲曲”,在于戲曲乃是圍繞著“曲唱”來“為戲”。在“唱念做打”四者之中,“唱”居于中心位置,“念、做、打”都是圍繞著“唱”展開的。換句話說,“曲唱”凝聚著戲曲之為“戲曲”的精神命脈。假如取消了“曲唱”,“念、做、打”就會立即失去依傍,戲曲也就不復存在了。這便是從“戲曲”獨自成體以來,曲詞結撰一直是戲曲劇本創作之中心與重心的緣由。曲詞的創作方式及呈現形態,可以依譜填詞、依腔填詞,創作符合曲牌要求的句式長短不齊的“詞”式體曲詞;也可以文行腔,即依照戲曲聲唱的特點,遵循聲腔調子,采用七字句或十字句的“詩”式體結撰曲詞。在戲曲藝術中,曲詞既可以傳唱即時的情境;也可以成為形式工具,進行敘述,鋪述經歷過的情、事,推動戲曲情節的展開。曲詞既可以短小精悍面目呈現,給人以震撼;也可前呼后應,鋪敘事件,完成結撰鴻篇巨制的任務。捕捉情感閃光點,精心構造意境,完成即時性的情感發抒與歷時性的情節展開,是戲曲曲詞結撰中必須考慮的問題。當然,“結撰”是任何文體都必須考慮的問題。由于詩文詞曲是戲曲曲詞重要的藝術資源,故而戲曲曲詞的結撰,對詩詞結撰之法多有借鑒。
一、戲曲曲詞的結撰之道與詩文結撰之法
劉勰《文心雕龍·定勢》篇言道:“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即體成勢也。”[1]406“因情立體,即體成勢”,是結撰任何一種體式之文都必須遵守的基本規律。在這里,“情”為創作勃發之機;“體”乃為順暢“言志”“抒情”“寫物”“載道”而尋找到的最恰當的表現形式;“勢”則是表現形式內部對任何一位選擇這一表現形式去表現的作家都適用的“規范”,以及作家在“合規范”中表現出的獨創性。“因情立體,即體成勢”,是劉勰從當時總稱之為“文”的詩、騷、賦、樂府、五言古詩七言歌行的創作經驗中,總結出來的創作規律。近體律絕是古體詩的格律化,詞是俗曲雅歌的衍化,戲曲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對詩、詞、歌、賦等藝術經驗廣有吸收,故而這一規律,對于后起的文體例如近體詩、詞、戲曲創作同樣有效。戲曲劇本的結撰,固然有不同于詩、騷、歌、賦的自身特點;但戲曲劇本的結撰之道,無出“因情立體,即體成勢”的范圍。戲曲藝術追求的,是以一連串相互沖突的事件為線索,在聲情并茂的“唱念做打”的演敘中,展示人物的心路歷程、命運遭遇。這就是戲曲劇本創作中的“情”(情事)。戲曲人物無時無刻不處在規定情境之中,何處宜“念”,何處宜“唱”,何處宜“諢”,何處應對唱,何處該獨抒,何處應濃筆重采渲染,何處該三言兩語交代,總是由規定情境來決定,“不勞擬議”。猶如詩文創作,因“情”因“景”,起承轉合,總是緣情而發,“不勞擬議”一樣。[2]52這就是戲曲劇本創作中的“因情立體”。戲曲表演以“唱、念、做、打”為基本手段。在戲曲中,“唱”有章法,“念”有規矩,“做”有程式,“諢”有尺度。“念”合“規矩”,“唱”循“章法”,“做”遵程式,“諢”守“尺度”,才能獲得欣賞;否則,無人問津。就像律詩有“律”有“格”。在律詩創作中,遵“律”循“格”,情思才能按“意中之神理”,如云中之龍,藝術地宛轉屈伸一樣。[2]44,48這就是戲曲劇本創作中的“即體成勢”。“因情立體,即體成勢”,有“大規”,有“細則”。“大規”如《熔裁》篇所云:“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于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于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馀于終,則撮辭以舉要。”[1]425情、事、辭是“草創鴻筆”時必須仔細斟酌的事項。“情”——情志情思,必須掌控全局;“事”——承載情志情思的“事實與典故”,必須與情志情思若合符節;“辭”——表達情志情思的語言,必須干凈凝煉傳神。劉勰說:“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先”,說明“設情位體”“酌事取類”“撮辭舉要”等“三準”,是在“鴻筆”的“草創”階段,即在輸入進文字媒介之前,就應該預先構想妥當的。此即隋人劉善經《論體》里說的:“凡作文之道,構思為先,不可偏執。”[3]4和劉勰論列的“文筆”二十體相比,戲曲的體制更“鴻”,故而戲曲劇本創作更應該如此。這就是李漁《閑情偶寄·詞曲部》把“結構”放在劇本創作“第一”位,吳梅《顧曲麈談》強調“填詞者引商刻羽之先,拈韻抽筆之始,須先講全部綱領,布置妥帖”[4]49——“袖手于前始能疾書于后”的根由所在。“細則”如《章句》篇所言:“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尋詩人擬喻,雖斷章取義,然章句在篇,如繭之抽緒,原始要終,體必鱗次。啟行之辭,逆萌中篇之意;絕筆之言,追媵前句之旨。故能外文綺交,內義脈注,跗萼相銜,首尾一體。”[1]440命詩作文,如繭中抽絲,織絲成錦。“聯字分疆”如“繭中抽絲”,“抽絲”有方法技巧,不講技巧,治絲益棼;“總義包體”如“織絲成錦”,“織錦”有工藝規則,不講工藝規則,織成的錦就不成邊幅。傳統詩文理論中,把命詩作文在不能不講的技巧規則,稱之為“法”“體制”,并稱:“為文而不(用)法,是猶用師而不以律矣。古之論文,必先體制而后工致。譬諸梓人之作室也……”[5]571詩、文各有其獲得公共認可的“章法體制”,詩有“式”文有“則”。皎然之《詩式》,就是講古詩近體的“章法”的,陳揆的《文則》,就是講各種文體的“體制”的。命詩作文,不講“章法”,信口亂道,猶如“用師而不以律”,即指揮作戰不講戰法,必敗無疑。命詩作文時,有尊重詩文之“體制”的自覺,才有可能實現“外文綺交,內義脈注”的創作理想。就像“梓人之作室”,即泥水匠蓋房子:先須選好地址,設計好圖樣,然后再按要求選材,按工藝施工,才有可能蓋成理想中的房子一樣。此即李漁《閑情偶寄·詞曲部》在“結構第一”之后,詳論“立主腦”“密針線”“審虛實”“戒浮泛”“忌填塞”的根由所在。當然,詩、詞、歌、賦和戲曲創作屬于精神勞動,其復雜性并非泥水匠蓋房子那樣的物質勞動可比。詩“式”文“則”,都只是個“大體規范”,運用之妙,存乎一心。猶如兵法運用須隨“形”順“勢”,靈活應對一樣。創作中循規蹈矩,尺模寸守,不敢越雷池一步,無疑于扼殺文學創作的生命。不過,那是應該在另一個層面討論的問題。與當下討論的文學創作應該遵守文學創作的規律,并不矛盾。
三、板腔體曲詞結構之法
板腔體曲詞,是后于曲牌體曲詞出現的。從事物發展總是“后來居上”上分析,板腔體曲詞的出現,應該和曲牌體曲詞更多地滿足著“大傳統”的“文人雅致”,而不便于“小傳統”里伶工們演唱有關。這一問題,此處不便討論。這里想指出的是:板腔體曲詞以“齊字句”為表現載體,猶如曲牌體曲詞以錯綜不齊之“長短句”為表現載體,均是戲曲劇本的表現載體。而有關研究顯示,明刊《青陽時調詞林一枝》第三卷所收的《琵琶記·趙五娘描畫·真容》,這部以曲牌體唱詞為主的劇本中,已經夾雜著齊言句式的唱詞(1)。這種狀況的出現,可能是出于《琵琶記》作者的特別設計。他有意讓趙五娘裝扮做賣唱女入府賣唱,當然要按賣唱女之本色演唱,不能用曲牌體。也恰恰說明,齊言句式的唱詞形式,在民間已經流傳開來。其實,在元代,“講詞話”,就是農村社會的通俗演劇形式。[11]齊言句式成為了板腔體曲詞的顯著標志。孟繁樹認為,板腔體戲曲曲詞所采用的齊言對偶句式,以及上下句在音樂結構上的呼應,是從當時的說唱藝術中延伸出來的。[12]61從現在河南墜子、京津大鼓詞的句式和板腔體戲曲曲詞的某種近似性上逆推,此說可以采信。當然,依本論文作者對中國戲曲史的總體理解,中國戲劇的發生和發展,和中國戲曲積極向各種藝術樣式借鑒藝術手段密切相關。[13]
不過,所謂的齊言句式,只是從整體言,在具體的創作中,則可以根據具體情況,增加相應的襯字或詞語(2),而不改變樂句的結構(3)。板腔體戲曲曲詞的齊言句式,在演唱時允許伶工根據行腔需要加一些襯字,以渲染情感抒發的跌宕起伏。[14]有時,在情感抒發的某一關節點上,為增強表現的力度,也會有意識地“拉長”齊字句式,追求一種“異類調節”之美。以秦腔《蘇武廟》中的老生唱段為例:
楊繼業:(唱苦音尖板)兩狼山打一仗天搖地動,(轉塌板)拼性命和敵兵對壘交鋒。我楊家扶宋王忠心耿耿,一個個為國家不避吉兇。金沙灘只殺得星稀月冷,血成河尸堆山實實慘情。楊大郎替宋王宴前喪命,楊二郎拔劍刎也把命傾。楊三郎被馬踏尸不完整,四八郎兩個兒下落不明。楊五郎五臺山去把佛誦,七郎兒雁門關前去搬兵。單丟下楊六郎倒也驍勇,提銀槍跨戰馬疆場立功。我楊家八個兒子一個一個如龍似虎東擋西殺南征北戰兩軍陣前萬馬軍中不惜命,是忠良喪疆場雖死猶榮。[15]54,55
“我楊家……雖死猶榮”,書作“我楊家八個兒子不惜命,是忠良喪疆場雖死猶榮”,由于有前文的鋪墊,在旁人看來,可謂文完意足。但劇作者卻覺得意猶未盡,在“八個兒子”之后,“不惜命”之前,加上長長一串“一個一個/如龍似虎/東擋西殺/南征北戰/兩軍陣前/萬馬軍中”,才覺得圓滿舒出了心中塊壘。如今《蘇武廟》每唱到“我楊家八個兒子——一個一個/如龍似虎/東擋西殺/南征北戰/兩軍陣前/萬馬軍中——不惜命,是忠良喪疆場雖死猶榮”,定獲滿堂彩。這說明劇作者的良苦的藝術用心沒有白費。應該指出的是,句子雖然“拉長”了,但“拉長”那部分,依然保持著板腔體曲詞齊言對偶句式,不過是對偶更凝練,節奏更緊湊而已。
板腔體齊言句式帶來的不僅是曲詞創作方法的變化,也導致了戲曲抒情寫意塑造人物渲染場面的一些變化。從唱本轉換到戲曲表演,則唱本的“段落”也就自然地向戲曲的“場次”演進。[12]193這也證實了中國戲曲劇本創作體式上的演進,和中國戲曲的任何一種發展一樣,都是在多種藝術的滋潤下實現的。
注釋:
(1)詳細論述為:“在明刊《青陽時調詞林一枝》第三卷所收的《琵琶記·趙五娘描畫·真容》里,不作“行孝曲兒”,徑稱為“唱詞兒”及“琵琶口詞”。并有“琵琶詞”一段,是自訴性質,形式完全和后來的彈詞一樣,計八十句,一韻到底。這是關于“琵琶詞”的很明確的資料。曲牌名稱徑作【琵琶詞】和【貨郎兒】也是一致的”。詳見嚴敦易《元明清戲曲論集》,鄭州:中州書畫社,1982年,第73頁注②。
(2)王昆吾認為敦煌曲詞中:“凡襯字,大多出于歌唱需要,而不是出于文法需要……襯字大多出現在歌辭末句或樂句轉換處,表現對為歌唱重點部分的一種裝飾;許多襯字,還用來增加感情色彩……襯字是由于歌唱時的聲情變化而產生的”。詳見王昆吾《隋唐五代燕樂雜言歌辭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第101頁。
(3)李玫研究了音樂結構與文辭句式的互動關系,認為:“襯字、詞的增加并不必然改變樂句結構”。詳見李玫《七言句式與音樂結構的對應關系》,《文藝研究》,2014年第12期。
參考文獻:
[1]劉勰.增訂文心雕龍[M].黃叔琳注,李詳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05.
[2]王夫之.姜齋詩話箋注[M].戴鴻森,箋注.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3]周祖詵.隋唐五代文論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6.
[4]王衛民.吳梅戲曲論文集[M].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3.
[5]陶秋英.宋金元文論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6]張炎,沈義父.詞源注 樂府指迷箋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7]李漁.閑情偶寄[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8]劉熙載.藝概注稿[M].北京:中華書局,2009.
[9]王驥德.曲律注釋[M].陳多,葉長海,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0]俞為民,孫蓉蓉.歷代曲話匯編:新編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明代編(第一集)[M].合肥:黃山書社,2009.
[11]伊維德.我們讀到的是“元”雜劇嗎——雜劇在明代宮廷的嬗變[J].宋耕,譯.文藝研究,2001(3).
[12]孟繁樹.中國板式變化體戲曲源流研究[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2.
[13]王銘.媒介視角下的中國傳統戲劇存在形態與特色守護[J].社會科學論壇,2015(2).
[14]王銘.戲曲藝術曲白關系辨析[J].四川戲劇,2017(4).
[15]《秦腔唱段集錦》(第2集)[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