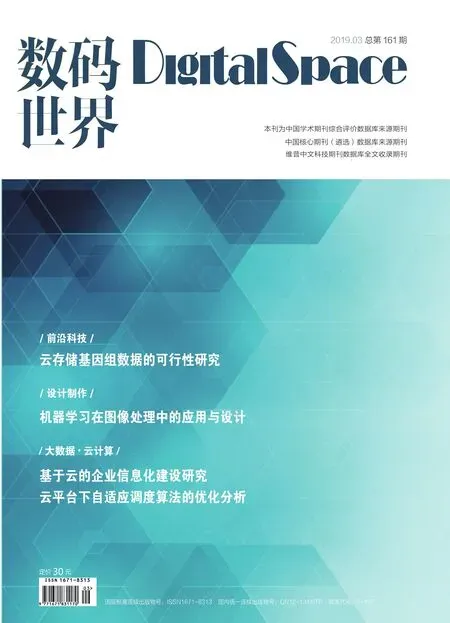娛樂(lè)時(shí)代的電子游戲社會(huì)功能探究
孫淑萍 檀馨 湘潭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
電子游戲已經(jīng)融入大眾日常生活,與文學(xué)、音樂(lè)和電影一樣,早已成為文化娛樂(lè)產(chǎn)業(yè)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所具有的自愿參與,虛擬社交、及時(shí)反饋等特性更是廣為大眾接受和喜愛(ài),但對(duì)電子游戲文化與社會(huì)特質(zhì)的研究卻遠(yuǎn)不及其他娛樂(lè)文化。游戲作為一種新興文化形態(tài)與傳播媒介,具有的娛樂(lè)、教育、文化傳播和社交等社會(huì)功能理應(yīng)在現(xiàn)今得到重視,并且從對(duì)這些功能的梳理中理性思考游戲所獨(dú)有的社會(huì)價(jià)值。
1 電子游戲的娛樂(lè)功能
文學(xué)憑借書(shū)紙來(lái)構(gòu)建出屬于每個(gè)人獨(dú)有的想象畫(huà)面,音樂(lè)通過(guò)字符和譜曲創(chuàng)造情緒和意境,電影技術(shù)的發(fā)展則為大家呈現(xiàn)出了完全具象的一切場(chǎng)景,這些娛樂(lè)方式向大眾提供有距離感的觀賞體驗(yàn),讓他們較為客觀的去思考和自我探索。電子游戲的出現(xiàn)卻打破了這種固有的娛樂(lè)模式,及時(shí)反饋所帶來(lái)的互動(dòng)效果和非線性的敘事特性使玩家產(chǎn)生特有的主觀沉浸感。“游戲的共同參與者是游戲的組成部分”,游戲體驗(yàn)使玩家與游戲相互融合,讓每個(gè)人都擁有屬于自己的獨(dú)特、自我的游戲經(jīng)歷。
電子游戲的虛擬性使玩家可以無(wú)負(fù)擔(dān)的追求自我,而好的游戲更是能讓人置身于特殊環(huán)境下解構(gòu)自我并思索自我與社會(huì)的異同,以索尼發(fā)行的互動(dòng)式電影游戲《底特律:成為人類(lèi)》為例,玩家在游戲中扮演三個(gè)擁有人類(lèi)意識(shí)的異常仿生人,片段式的體驗(yàn)他們?nèi)松械闹卮笄榫埃簬ьI(lǐng)遭遇家暴的小女孩出逃的女機(jī)器人,替人類(lèi)服務(wù)追殺異常同類(lèi)的警察機(jī)器人,被人類(lèi)陷害報(bào)廢后又重生的反抗首領(lǐng)機(jī)器人。在游戲中你會(huì)代入理解機(jī)器人遭受的屈辱和痛苦,也能感受人類(lèi)與機(jī)器人之間復(fù)雜的關(guān)系情感,更是可以體驗(yàn)現(xiàn)實(shí)中絕不會(huì)出現(xiàn)的倫理困境——是站在人類(lèi)的一方還是機(jī)器人。娛樂(lè)本身就是對(duì)人類(lèi)精神需求的滿(mǎn)足,除了技術(shù)本身可以帶來(lái)極致的視聽(tīng)體驗(yàn)外,游戲文本的特殊性也引導(dǎo)著玩家的游戲體驗(yàn),玩家在自主選擇中領(lǐng)會(huì)更深層次的思想。文本帶來(lái)的劇情式體驗(yàn)讓人深思,其他類(lèi)別的游戲也能從各方面提供自己的娛樂(lè)價(jià)值。娛樂(lè)功能依然是如今游戲的首要功能,與此同時(shí)產(chǎn)生的游戲沉迷依然是不可避免的社會(huì)問(wèn)題,隨著主流語(yǔ)言的更替,游戲不再被妖魔化,我們可以更為理性的去探索游戲與時(shí)間的平衡,讓游戲的虛擬融入生活,使之成為人生的延伸。
2 電子游戲的教育功能
游戲的社會(huì)功能中教育是最受人關(guān)注且被廣泛接受的,電子游戲本身具有的現(xiàn)實(shí)模擬性使得其可以與各類(lèi)學(xué)科的知識(shí)體系融合,設(shè)計(jì)出難易得當(dāng),激發(fā)學(xué)習(xí)興趣的教育游戲,“游戲中還專(zhuān)門(mén)有一個(gè)子類(lèi)別叫做教育游戲,又稱(chēng)嚴(yán)肅游戲,指那些以教授知識(shí)技巧、提供專(zhuān)業(yè)訓(xùn)練和模擬為主要內(nèi)容的游戲。”政府部門(mén)開(kāi)發(fā)戰(zhàn)場(chǎng)模擬類(lèi)游戲應(yīng)用于軍事訓(xùn)練,金融從業(yè)者開(kāi)發(fā)投資或股票類(lèi)游戲應(yīng)用于學(xué)生或員工教育,心理診療中也開(kāi)發(fā)應(yīng)用了許多游戲應(yīng)用于測(cè)試和對(duì)病人進(jìn)行治療,游戲的虛擬性在此展現(xiàn)出了自己極大地優(yōu)勢(shì)。游戲從教育視角下真正成為與現(xiàn)實(shí)世界接軌的“有益行為”。
尚俊杰教授認(rèn)為游戲的核心教育價(jià)值可以概括為游戲動(dòng)機(jī),游戲思維和游戲精神。首先,游戲的基本特性之一即為自愿參與,游戲化的課程設(shè)計(jì)使學(xué)生不再被動(dòng)的接收知識(shí),而是自發(fā)的產(chǎn)生好奇與挑戰(zhàn)意識(shí),在游戲化中將長(zhǎng)遠(yuǎn)的目標(biāo)劃分成了可預(yù)見(jiàn)的節(jié)點(diǎn),更能激發(fā)出學(xué)生的學(xué)習(xí)動(dòng)機(jī)。
其次,游戲思維即游戲化思維的概念不僅可以應(yīng)用在教育中,在《游戲改變世界》一書(shū)中,作者提出了將生活游戲化的概念,使游戲化思維滲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從而改變自我心態(tài),能更好的去學(xué)習(xí)新事物,接受更多的挑戰(zhàn)。“仔細(xì)分析游戲化的核心,實(shí)際上還是發(fā)揮了游戲有助于激發(fā)動(dòng)機(jī)的特點(diǎn),只不過(guò)這里激發(fā)的不是表面上的休閑娛樂(lè)、逃避、發(fā)泄等動(dòng)機(jī),更多的是馬龍(Malone)提到的挑戰(zhàn)、好奇、競(jìng)爭(zhēng)等深層動(dòng)機(jī)。”游戲化思維使人改變自己的心態(tài)和思考方式,同時(shí)對(duì)困難采取分步解決的方法,降低個(gè)人的心理預(yù)期,更為輕松的面對(duì)人生。
游戲精神可以說(shuō)是人類(lèi)自由精神的體現(xiàn),在美國(guó)政府成立的創(chuàng)新游戲化學(xué)校Quest to Learn中,學(xué)生可以完全跟隨自己的意志去選擇自己感興趣的課程,而老師則只是以引導(dǎo)者的方式讓他們自主學(xué)習(xí),根據(jù)2016年的一篇報(bào)道“根據(jù)Quest的統(tǒng)計(jì)數(shù)據(jù),60%的首屆畢業(yè)生進(jìn)入了四年制大學(xué),29%進(jìn)入了兩年制大學(xué)。”游戲精神使人能夠更為積極的追求本質(zhì)上的自由,同時(shí)允許學(xué)習(xí)者自由地選擇想學(xué)的內(nèi)容,在quest學(xué)校的學(xué)習(xí)中,更為注重學(xué)習(xí)者的學(xué)習(xí)過(guò)程,而對(duì)最后的考試成績(jī)等并不過(guò)于看重。教育的核心應(yīng)該根據(jù)每個(gè)個(gè)體的天賦和興趣,充分激發(fā)游戲教育的挑戰(zhàn)、好奇和幻想等深層動(dòng)機(jī)。
3 電子游戲的文化傳播功能
電子游戲的虛擬和架空性消解了不同文化間的差異,其通過(guò)自身的角色與背景設(shè)定將各色玩家構(gòu)建在了同一個(gè)游戲文化體系里,同時(shí)在針對(duì)不同地區(qū)時(shí)采用針對(duì)性的設(shè)計(jì)及玩法修飾,通過(guò)這些方式實(shí)現(xiàn)對(duì)游戲自身的傳播。劇情向游戲則實(shí)現(xiàn)了對(duì)特定歷史或文化的多層面?zhèn)鞑ァT谒沟俜疑挠螒騻鞑W(xué)說(shuō)中“傳播就是一種體現(xiàn)受眾高度自主性和主觀性的游戲”,這恰好迎合了游戲自主參與的特點(diǎn),游戲的傳播是玩家自主選擇的結(jié)果,是玩家對(duì)自我好奇的滿(mǎn)足。游戲?qū)ξ幕姆?hào)概括也是一種對(duì)意識(shí)形態(tài)的傳播,例如象征著英國(guó)的雨傘標(biāo)志,這些抽象的聯(lián)想思維透過(guò)符號(hào)呈現(xiàn)在游戲中,也體現(xiàn)出設(shè)計(jì)者以及玩家心理的固化印象,使游戲圖像的理解更加便捷。
4 電子游戲的社交功能
社交互動(dòng)是人們生活的本質(zhì)需求,電子游戲?qū)ΜF(xiàn)實(shí)社交也具有一定的推助意義,工作和學(xué)習(xí)的壓力使人缺少時(shí)間和條件與朋友在現(xiàn)實(shí)中相聚,而電子游戲使得人與人之間游戲內(nèi)外的關(guān)系傳導(dǎo)易于達(dá)成,滿(mǎn)足了玩家在游戲內(nèi)外都能產(chǎn)生高度互動(dòng)的社交文化需要。同時(shí)用戶(hù)在虛擬社交中也能結(jié)識(shí)興趣喜好更為相通的好友,玩家在長(zhǎng)期的游戲經(jīng)歷中形成了自己獨(dú)有的類(lèi)型偏好和整體認(rèn)知,從而在游戲中結(jié)識(shí)的好友大概率可以進(jìn)行更加良好的溝通與社交。《魔獸世界》的玩家社區(qū)也是游戲社交的標(biāo)志性體現(xiàn),玩家在電子游戲中找到了虛擬社會(huì)下的集體認(rèn)同感,基于同樣的愛(ài)好背景,無(wú)所不談,互相幫助。
當(dāng)前社會(huì)對(duì)游戲的認(rèn)知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與滯后性,游戲發(fā)展至今,它的豐富性和復(fù)雜性早已今非昔比,作為一種可包容目前所有藝術(shù)形式的文化形式,其對(duì)多主題與多領(lǐng)域的廣泛影響使得對(duì)游戲?qū)W的研究與傳播學(xué)一樣應(yīng)立足于交叉學(xué)科的視野之上,才能正確發(fā)現(xiàn)它的社會(huì)價(jià)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