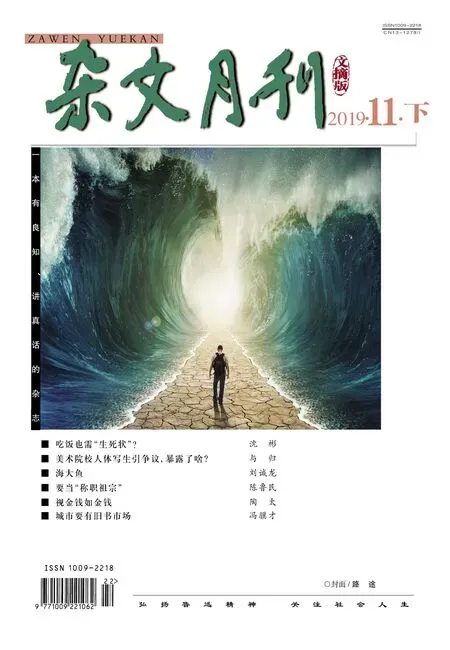雜加文,便出味
●劉誠龍

對文學定義千千萬,對文學比喻有萬萬千,我喜歡的是,文學是精神食糧。這說法確無經國之大業(yè)有氣派,但我喜歡:米麥是物質食糧,不吃,身體會餓死的;文學是精神食糧,不吃,腦子會餓死的。說來很壯人氣是吧?也讓人氣餒,米麥糧食是農民做出來的,做文學糧食的,莫非也是農民?升初中升高中,升到知識分子水平,還是一個農民。就活計言,種田園與種版面,本來沒區(qū)別。
據說雜文是文學之一種,那么,雜文是什么糧?如何食?這不是首要問題。我想的一個問題是,雜文究竟者何?曾有謂,雜文是投槍是匕首,這個有點嚇人,終日荷戟,那副頭上長角樣子,人見人怕;或謂,雜文是銀針是手術刀,這個也是雜文家高自期許:來來來,你有病,天不知,我知,我來給你打一針。你真把你當士大夫啊。
我覺得雜文是精神食糧,這個定義好,藥補不如食補嘛,雜文不是給人開藥方,而是給人補營養(yǎng),食療是自然而然增加對這個社會各種病毒的免疫力。不過問題還是來了,文學樣式蠻蠻多,誰是主糧,誰是雜糧?打開作協(xié)表格,雜文是不入菜單的,可見其不是主菜,也非大菜,四菜一湯都沒排上。那是冷盤?雜文冷是冷,不是桌上頭盤啊。
我以為雜文是拌飯菜,您那里叫什么,我不曉得,我這還叫送飯菜。大盤小盤,大碗小碗,吃了個肚兒圓,卻還沒吃飯,看到滿桌油膩膩的,吃不下,便喊一聲老板:來碗送飯菜。店小二應聲而來,或一碟酸豆角,或一碟蘿卜皮,或一瓶霉豆腐,或一小碗老干媽炒豬肉。
這不是小看雜文,這是看到了雜文大功用,精神主食糧,諸菜不夠用場了,雜文端了上來,雜文來壓軸,雜文好爭氣啊。不論什么菜系,都是講究色香味形的,雜文居文學滿漢全席,其勝出者何?
雜文以味勝。雜文當然要講究文采,也就是色;雜文當然要講究意義,也就是香;雜文要講究起承轉合,也就是形。這些是各類文本都有的,那么雜文如何獨存?我以為就是我們所說的雜文味。有人說,雜文是思想文本,我覺得這個有點高抬了。不是誰都可以說是思想者思想家的。雜文,頂多是思考文本。
材料各有不同,烹法各有擅長。鄙人而言,常在史書間剁點肝啊割點肉啊,炒盤小雜碎。從小說里借點故事敘述,從散文那里弄點文采點綴,從詩歌那里學點意義表達,從現(xiàn)實那里扒點新鮮食療,從小品文那里剽點幽默技術,加些甜點,加些酸氣,加點苦料,加點湖南辣椒,同烹,雜文便出口味了。
要言之是:雜文味,雜加文,便出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