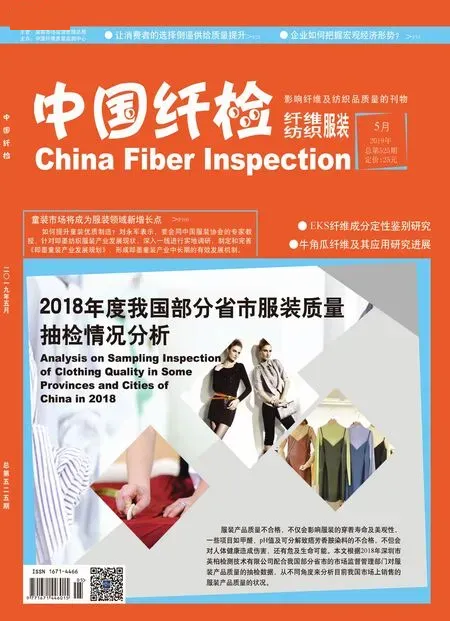廢舊紡織品化學回收處理技術
文/吳世容
1 引言
在我國,廢舊紡織品大多被當作垃圾進行填埋或者焚燒等簡單處理。大部分紡織品很難降解,填埋會長期占用大量的土地資源,合成纖維,比如聚酯纖維、錦綸、腈綸等不易降解,掩埋后污染土壤環境;低溫燃燒容易產生二噁英,高溫焚燒會產生氮氧化物等大氣污染物。BIR機構(國際性回收再生組織)2008年在瑞典哥本哈根大學進行研究得出結論:每使用1kg廢舊紡織物,就可降低3.6kg二氧化碳排放量,節約水6000L,減少使用0.3kg化肥和0.2kg農藥[1]。因此,大量回收使用廢舊紡織物,與原生材料的加工生產相比,明顯減少了對二氧化碳的排放,也有效緩解了原料緊張壓力。
化學回收利用技術是指采用化學方法將廢舊紡織品中材料降解或分解,重新聚合成高分子,并用以制備再生纖維,或利用降解產物小分子用于非紡織材料用途。化學回收利用是對廢舊紡織品回收的最佳方式,不僅可以使得紡織原料徹底利用,而且對于價格昂貴紡織原料能夠較好地重復利用,經化學回收的原料與新料所制造的纖維性能差別較小,部分化纖類產品可實現全方位原料替代。但是化學回收法所需的工藝技術較高,成本相對較高適用于批量生產,對于所回收的廢舊紡織品所含原料要求較為嚴格。
本文分不同材料進行描述,介紹其化學回收技術發展概況,尤其側重工業化解決方案比較成熟的技術。粘纖、莫代爾纖維、萊賽爾纖維可生物降解。天然纖維成分較為復雜,大部分不適合用化學方法回收利用,多半作為復合功能材料的初始原料,工業化價值較小。
2 不同纖維材料的化學回收技術
2.1 聚酯纖維
聚酯的回收技術研發在上世紀50年代就已經起步,并在80年代開始步入工業化運營階段。美國Du Pont公司、德國Hoechst公司、日本帝人公司,相繼開發出聚酯纖維化學回收處理技術。解聚聚酯纖維的方法有糖酵解、胺解、甲醇分解、堿性水解、離子溶液法,回收產物可用于再生聚酯的生產。其中糖解和醇解是較成熟的降解方法。
醇解和水解使聚酯解聚成對苯二甲酸二甲酯(DMT)、乙二醇(EG)、對苯二甲酸(TPA)等單體或含幾個對苯二甲酸單元的對苯二甲酸乙二醇酯(BHET)低聚物,然后再將單體或低聚物重新聚合成聚酯,醇解分為乙二醇醇解和甲醇醇解。乙二醇醇解由美國杜邦公司于20世紀60年代開發,由于是部分降解而不是徹底降解,因而成本相對較低。反應得到的高純度BHET可直接用于生產纖維級聚酯。但乙二醇醇解法要求回收對象100%為PET均聚物。甲醇醇解原理是廢PET與甲醇反應得到DMT和乙二醇,DMT可轉化為對苯二甲酸或直接用作PET原料。甲醇醇解的化學反應是DMT與EG酯交換反應生成PET的逆反應。解聚工藝簡單,但分離不同共聚單體難度較大[2]。
近年來出現了超臨界甲醇醇解法。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開發了四氫呋喃共聚法,向廢聚酯中加入四氫呋喃,采用特定的催化劑使之形成共聚體,這種共聚體由高分子的軟硬鏈組成,是一種很好的工程塑料。日本KobeSteel公司推出了超臨界水水解法,這種技術采用超臨界水將廢聚酯水解成TPA和乙二醇[3]。
2.2 棉
回收的廢棉可以作為粘膠纖維的生產原料,經化學處理也可制成吸附性功能材料,商業化領域已經實現了以棉纖維為原料的紙張和生物乙醇的生產。1979年,美國一家造紙公司用廢舊紡織品生產出了優質的造幣用紙。JEPLAN公司開發了一種將棉花轉化為生物乙醇的技術,目前,這種技術在愛媛縣今治市的一家工廠里被采用,不過通過這種方法生產每升乙醇的成本并不便宜,遠高于常規工藝[4]。
棉纖維中纖維素含量占90%以上,是制造再生纖維的主要原料。因此以廢舊棉制品為原料,經制漿、堿化、黃化等工序后再溶于稀堿液中制成粘膠,再生粘膠纖維有良好的耐堿性和尺寸穩定性,其濕強也比經濕法紡絲而制成的普通粘膠纖維高很多。采用 NMMO 有機溶劑溶解和干濕法紡絲工藝制成的 Lyocell纖維對環境無污染,具有良好的親水性、吸濕性和懸垂性等。目前,科學家們正致力于研究借助高效環保的溶劑分離棉等廢舊紡織品中纖維素分子的方法。目前有幾種溶解纖維素的方法,比如Ioncell-F法,它使用了新型離子型溶劑[5]。
外媒介紹一種溶媒淤漿法對纖維大分子進行改性,使纖維素分子結構發生變化,形成纖維素衍生材料,可用于生產水溶性羧甲基纖維素(CMC)[6]。
比較典型的廢棉紡織品回收制成功能材料的方法,包括以下步驟:(1)將廢舊棉紡織品依次經KH-550溶液、氯化銨溶液、氯化鋅溶液浸漬處理;(2)將步驟(1)中所得到的混合物進行預氧化處理;(3)將混合物隔絕空氣升溫至400℃~900℃進行碳化處理,轉變為多孔功能碳纖維簇;(4)將步驟(2)中副產物收集和溶劑循環利用的凈化系統[7]。利用該方法制備的碳纖維簇不僅纖維間不連續,具有大量的空洞,纖維表面也具有不規則的孔,因此可作為功能材料的載體,如吸附抗菌離子可制得抗菌添加材料,用于制備各種抗菌制品;也可作為紡織染料廢水的吸附材料,廣泛應用于其他水處理和氣體過濾等領域。
2.3 羊毛
利用酸堿酶將羊毛角蛋白降解為氨基酸、多肽、角蛋白大分子,可以廣泛應用于食品、醫藥、紡織等工業領域[8]。
2.4 腈綸
酸堿催化水解處理腈綸,使氰基轉變成酰胺基或羧基,必要時進一步與其他高分子材料進行復配制成膠黏劑,用高分子材料改性制成多孔吸附材料[9]。
2.5 氨綸
醇解法回收聚氨酯纖維提供了一種操作簡單、回收率高、工藝流程短的方法。聚氨酯纖維降解產物經分離提純后可與異氰酸酯和擴鏈劑反應,得到的聚氨酯產品可用作涂料、薄膜、泡沫纖維等[10]。
2.6 復合材料
對于多種纖維混紡難分離的材料,經過簡單的化學處理,也可以有多重用途, 比如建筑材料、增強材料等。
澳大利亞Veena Sahajwalla教授收集廢棄紡織品,去除了金屬附件,然后將這些棉、羊毛、聚酯、尼龍以及其他織物一起粉碎,變為一堆纖維,再加入偶聯劑,使不同纖維粘在一起。最后,在高溫下壓縮纖維形成實心面板,做出防火防水的新型材料[11]。
再加工纖維可作為增強輔助材料與其他物質制備復合材料。如將以廢舊地毯為原料加工得到的再加工纖維作為混凝土的增強纖維,改善了力學性能,降低了成本[12];將堿處理的廢棄劍麻纖維與脲醛樹脂經乙酰化處理得到的復合材料,其彎曲強度、耐磨性、熱分解溫度、吸水性及電絕緣性都超過了脲醛樹脂/木粉復合材料[13]。
3 問題和對策
3.1 分類回收體系
化學回收工藝普遍針對性強,根據不同的成本、材料,目標產物有不同的選擇。為實現資源再利用效率最大化,需要全社會提供高效的回收分類體系。依靠完善的法律體系,建立由國家、公共團體、企業和社區分別承擔責任的廢棄物處理體制,不斷推動循環經濟發展,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考慮到我國區域發展差距巨大的現實,應針對不同地區的客觀經濟需求和技術能力,量力而行。物理回收、化學回收、焚燒利用三種手段結合起來,為市場提供多樣化選擇。一線城市可以優先推行廢棄紡織品回收分類體系,規范回收主體。
3.2 生產成本
我國紡織品化學回收處理技術起步晚,發展慢,與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存在顯著差距。
生產成本長期居高不下,使得化學回收處理技術始終局限于聚酯纖維這一類回收工藝成熟的工業項目。回收產品與原生材料相比價格較高,市場接受度不高。究其原因,一是我國紡織品化學回收處理技術發展較慢,國內這一領域的技術開發市場轉化率低,有效技術供給不足;二是 企業缺乏大規模回收篩選能力,無法在生產環節降低單位生產成本;三是產品質量參差不齊,細分產品開發不足,造成下游企業利用困難。
這就需要以企業為主體,發揮技術應用的導向價值,嚴格保護專利技術開發所有人的各項權利,開發高效可循環生產工藝,提高廢棄紡織品利用轉化效率;建立嚴格統一的回收產品質量標準,形成可持續發展全產業鏈循環,惠及下游生產企業;在人口和產業規劃合理的前提下,扶持大規模工業回收項目,支持同類企業兼并和技術重組,提高回收產品生產規模。
3.3 消費者接受度
由于價格和安全性方面的考慮,消費者在選擇再生材料生產的各類產品時,普遍存在顧慮。在安全保障這塊,需要國家標準實現全面覆蓋,行業監管勢在必行,普及相關專業知識,耐心培植消費群體;對于價格,通過回收材料和原生材料混合使用,降低企業生產負擔, 打通回收行業和紡織品生產企業的行業壁壘,降低交流成本。關鍵還是加強研發,提升產業規模,使最終產品能具有較強的市場競爭力。當下,回收企業選擇成分單一、回收簡單、價值較高、消費者認可度高的廢棄紡織品作原材料不失為可行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