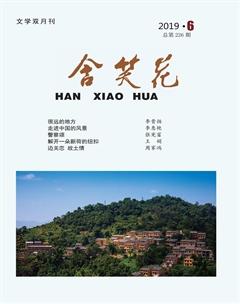燈
程杰
燈,預示著光明和希望。
一個仲春的傍晚,西邊的一抹霞光漸漸走遠,昏黃提前迎來黑夜,母親下意識地打開了燈,兒子正舞弄著一堆挖機玩具。
屋外,萬物無聲,靜得恐怖。夜空調整著姿態,開始布陣風雷雨電。突然,一道狹長的電光劃破黑暗,隨著一聲雷鳴敲碎夜的寧靜,兒子驚慌著竄入我的懷里,噼里啪啦,叮叮當當,燈熄了,母親走到窗戶邊,看看窗外,肯定地說:“小碩,停電了”,隨即從電視柜抽屜里拿出應急燈打開,屋里恢復了明亮,兒子又繼續舞弄著玩具。
黃昏,黑夜;閃電,雷鳴;母親,兒子,應急燈,漸漸地組成一幅幅以燈為焦點的畫面,迅速形成一條思緒的河穿越時空隧道沖開了我塵封已久的記憶之門。
那是一個春天的傍晚,生產隊春播集體搶公分,父親和母親為了搶到更多公分換取糧票布票,他們送糞到離村很遠的土地準備春播,母親背著一籃糞,父親負責趕馱糞的馬。天黑了父母還沒有回來,哥哥點上油燈,突然電閃雷鳴,風雨交加,冰雹直敲得屋頂瓦片叮當炸響,哥哥將大門和小門迅速關好并上了門栓,但是雨混合著風會拐彎似的從門縫竄進屋里,燈熄了,哥哥一邊安慰我和三姐不要怕,一邊去摸火柴把燈點亮。風雨又一陣肆虐,燈又熄了,熄了點,點了熄,火柴擦完了。我和三姐年齡最小,尋著閃電瞬間的光亮站到門縫旁不停地呼喚著父親母親,哭得很傷心。哥哥摸著在火塘里復火,火塘里閃爍的幾點誓要燎原的星火暫時驅趕走部分黑暗,驅走了我和三姐心中的驚恐。
還記得我讀小學時,煤油完了媽媽就會從柴堆里翻出明子點燃,用手舉著照亮我讀書寫字。晚上出門,就用竹篾片(或者耐燃的木頭)捆成捆,點燃一端做火把前行照明。當然,用得最多的是煤油燈。一般是用一個瓶子,將蓋子打開,然后用一塊鐵皮切成圓形,再整型成蓋子,中心打個孔,用草紙或者棉紙棉花棉布扭成適當粗細的繩做成燈芯,將燈芯一端伸出瓶蓋三分之一厘米左右,另一端放入瓶內,瓶內盛滿煤油,煤油燈就做成了。晚上,父親和母親就是在這種燈下操持著家務:推磨、舂碓、砍豬食、鍘馬草、剝包谷……也是這煤油燈陪伴我走過青春歲月,秉燭夜讀,挑燈夜戰……
某個街天,父親趕街回來,從馬籮筐里拿出一件新玩意,父親告訴我說這是馬燈。馬燈很高,由兩根鋁柱連接著燈頂罩,四周四根鐵線交叉固定著柱形擋風玻璃罩,燈底座是油箱,玻璃罩住的油箱中心有個高凸的燈芯護口。里面的燈芯酷似一根根花蕊,到了燈芯護口處,散開的燈芯又宛如一朵待放的牡丹。燈芯護口延伸處支撐著一根鐵條,用以翹起玻璃罩子點燃燈芯,玻璃罩外離燈芯護口不遠處有個燈芯長短調節開關,玻璃罩外的油箱上部有個盛油口。父親擰開盛油口開關,拿出油漏斗,擰開盛油壺,叫我扶住漏斗,緩慢地為馬燈盛油,油盛好后擰緊油箱盛油口蓋,等了一會兒,父親摁下鐵條將玻璃罩升高,擦燃火柴點燃燈芯,馬燈照亮了整個屋里,哥哥將手里的煤油燈放在灶臺上,提著馬燈到屋外走了一圈,似乎要向風兒宣告今后你們呼嘯寒風能奈我何。從此,我們一家進入了嶄新的馬燈照明時代。無論是溫柔的靜夜,還是粗暴的晚上,一家人乘著改革開放的春風,繼續努力奮斗著,推磨、舂碓、挑水、送糞、讀書、寫字……
思緒的潮水繼續涌動。燈一定會讓夜不再因為狂風而孤獨,不再因為黑暗而盲動,不再因為驚雷而無助,不再因為閃電而恐懼。
突然,“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手機音樂響起,兒子遞來手機喊道:“爸爸,媽媽打電話”。妻子告訴我,她在教室輔導,剛才風太大,樓頂晾的衣服恐怕被吹跑了。我拉開門,迎著清新空氣來到樓頂,雨停了,校園一片寧靜的明亮,夜空幾團灰白色的云還在貼著學校對門的山脊向東南方緩緩游動。辦公樓和教學樓的燈光與民居燈光交相輝映,輝映得園丁樓頂的晾衣繩、太陽能、水塔融合為一幅和諧的素照。
明亮的教室里,教師時不時走下講臺,看,那不是初三年級陳老師嗎?他正在給學生作輔導。有的教室時不時會傳來一陣陣掌聲,彰顯出因為有燈的夜才特有的求知力量。辦公室里,靜謐的燈光映照著黨總支書記正在策劃精準扶貧和義務教育均衡發展。民居樓窗透出的燈光與路燈下三三兩兩的行人無不預示著世道的平安與祥和。街道路燈和民居燈光錯落有致,相映成趣,排列成一條蜿蜒盤旋的光龍,巧妙地組成了斧頭和鐮刀的圖案。街道上川流不息的小汽車、摩托車的溫柔笛鳴和明亮燈光仿佛在傾訴人民生活漸趨富裕的豪邁衷腸。
看,一輛救護車正快速駛向醫院,它特有的聲光闡釋著自己的使命——守護一方百姓生命健康!那邊,一輛警車駛來,閃爍的警燈和前照燈似乎在誓言要掃盡人間黑惡勢力——保衛一方百姓安寧幸福!周圍的山色沁著層層墨綠,遠方的山嶺透出堅實而磅礴的力量。
我在沉思中“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的手機音樂再次響起,又是妻子的電話,說她已經到家。我回到家,看到母親和兒子都已沐浴在溫馨的床燈里安然入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