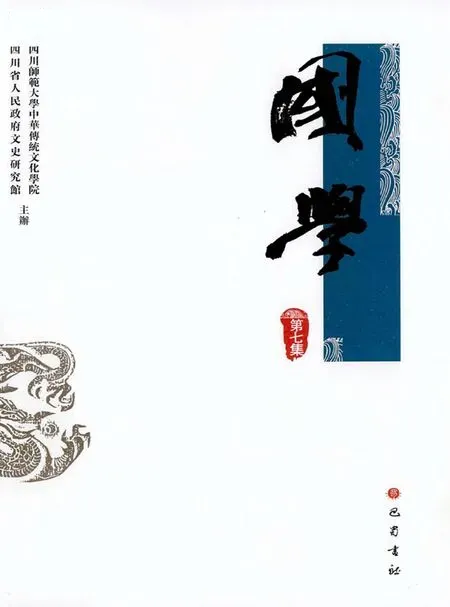跟隨方國(guó)瑜先生學(xué)習(xí)古籍整理與研究
鄭志惠
方國(guó)瑜(1903—1983),字瑞臣,雲(yún)南麗江人,納西族。著名歷史學(xué)家、教育家、雲(yún)南大學(xué)教授、雲(yún)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全國(guó)人大民委委員等。1923 至1936年初在北京師範(fàn)大學(xué)、北京大學(xué)求學(xué)和工作期間,完成了《廣韻聲匯》《困學(xué)齋雜著五種》(包括《隋唐聲韻考》《廣韻聲讀表》《慎子考》《慎子疏證》《論學(xué)存稿》) 《説文聲彙考》《釋名聲彙》等傳統(tǒng)文字音韻學(xué)著作的寫(xiě)作以及《納西象形文字譜》初稿。從1933年到麗江調(diào)査麼些文字,1934 到南京“輯録雲(yún)南地方史資料”,開(kāi)始專攻科目?jī)A嚮雲(yún)南史地之學(xué)起,至20世紀(jì)80年代,他寫(xiě)下了《滇西邊區(qū)考察記》《抗日戰(zhàn)爭(zhēng)滇西戰(zhàn)事篇》《雲(yún)南民族輯録》《雲(yún)南民族史講義》《中國(guó)西南歷史地理考釋》《雲(yún)南史料目録概説》《彝族史稿》《滇史論叢》《方國(guó)瑜文集》,主編《雲(yún)南史料叢刊》《雲(yún)南地方史講義》,與歷史系其他教師合作編繪《中國(guó)歷史地圖集》西南部分、編寫(xiě)《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史講義》等傳世之作。著名史學(xué)家徐中舒稱他是“南中泰斗,滇史巨擘”。
方國(guó)瑜先生不僅是雲(yún)南地方史、中國(guó)民族史的學(xué)科巨擘,更重要的是一位獨(dú)具魅力的老師,學(xué)術(shù)研究的無(wú)私奉獻(xiàn)者。他在雲(yún)南大學(xué)執(zhí)教近50年,謙虛謹(jǐn)慎,平易近人;奬掖後生,扶持青年,誨人不倦,為後學(xué)師表。回想1980年3月我大學(xué)畢業(yè)留校,至1983年12月24日先生去世,短短近三年,先生對(duì)我的耳提面命,記憶猶新,其後伴著先生著作繼續(xù)學(xué)習(xí)古籍整理與研究,是他將我引進(jìn)了古籍整理與研究的隊(duì)伍;是他為雲(yún)南歷史研究建造一座“磚瓦廠”的宏願(yuàn),影響著我一直堅(jiān)守在古籍整理這條“冷板凳”上,踏實(shí)工作,無(wú)怨無(wú)悔;是他“不淹沒(méi)前人,要超過(guò)前人”的精神,激勵(lì)著我認(rèn)真思考學(xué)術(shù)研究問(wèn)題,明白古籍整理與歷史研究的意義。總之,我的成長(zhǎng)離不開(kāi)方先生對(duì)我的培養(yǎng)與影響。
一、注重培養(yǎng)從事古籍整理堅(jiān)定信念
1.資料員工作的重要與意義
記得1980年3月4日,是我第一次到方先生家,第一次近距離聆聽(tīng)他的談話。先生的一席談話,影響了我一生,成為鞭策我前進(jìn)的動(dòng)力。那天是歷史系總支副書(shū)記劉西芳老師帶我到方先生家,徵求是否願(yuàn)意接受我到地方史研究室作資料員。方先生説培養(yǎng)年輕人他很高興,問(wèn)我:“你喜歡資料工作嗎? 學(xué)過(guò)目録學(xué)嗎? 資料工作很重要,也很艱苦,要抄書(shū),但不要怕。抄書(shū)對(duì)於打基礎(chǔ)很好,抄一遍,頂讀十遍。要學(xué)習(xí)顧炎武一天抄書(shū)一萬(wàn)字,樹(shù)大、根深、葉茂。今年學(xué)校衹準(zhǔn)留資料員,但我要把你當(dāng)助教培養(yǎng),今後要在資料、教學(xué)、科研上做出成績(jī)來(lái)。不要怕,無(wú)論做什麼工作,衹要有信心、耐心、細(xì)心、恒心、雄心這‘五心’,就會(huì)做出成績(jī)來(lái)。現(xiàn)在徐文德、木芹二位老師與我正在編纂的《雲(yún)南史料叢刊》,就是為雲(yún)南歷史研究提供資料的磚瓦廠,你今後就好好跟著木芹、徐文德二位老師學(xué)習(xí),參加這項(xiàng)工作。”那一刻,對(duì)於十分惶恐的我,還沒(méi)弄明白資料員該幹什麼、自己該怎麼做,面對(duì)名師的指點(diǎn),真不知説什麼好,但他的一席話給我信心和決心,“樹(shù)大、根深、葉茂”成為我後來(lái)學(xué)習(xí)、工作的動(dòng)力與座右銘。
2.樹(shù)立知識(shí)公有、為雲(yún)南歷史研究建“磚瓦廠”的資料公有思想
方先生認(rèn)為史料對(duì)於歷史研究十分重要,它猶如建築高樓大廈的磚瓦,猶如工農(nóng)業(yè)生産的基礎(chǔ)建設(shè)一樣重要,“工業(yè)基礎(chǔ)是勘探地質(zhì),農(nóng)業(yè)是治山水,如果沒(méi)有高質(zhì)量的基本建設(shè),就不可能奪得高産”①方國(guó)瑜:《雲(yún)南史料目録概説》,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4年。,而資料工作是一項(xiàng)十分繁重的農(nóng)田基本建設(shè)基礎(chǔ)工作。中國(guó)是人類歷史發(fā)展文脈唯一沒(méi)有中斷的國(guó)家,所保存的古籍也是全世界任何一個(gè)國(guó)家都無(wú)法比擬的,據(jù)2009年統(tǒng)計(jì),中國(guó)現(xiàn)存漢文古籍近20 萬(wàn)種②中國(guó)古籍總目編纂委員會(huì)編:《中國(guó)古籍總目》,北京:中華書(shū)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如何從浩瀚的書(shū)海中將有關(guān)雲(yún)南歷史資料發(fā)掘出來(lái),並運(yùn)用目録、版本、校勘等學(xué)科知識(shí)選録、整理,按一定的科學(xué)方式編排起來(lái),供讀者研究使用,這在一般人的眼裏是費(fèi)力不討好,“智者不為”的事,是一種為他人作嫁衣的工作。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如果每一位學(xué)者都花很多的時(shí)間去從浩瀚的書(shū)海中收集自己所需的文獻(xiàn)資料,勢(shì)必延緩他最閃光的學(xué)術(shù)思想的形成,尤其是“舊社會(huì)個(gè)人觀念重,每個(gè)人都做基礎(chǔ)工作,問(wèn)題研究好了,把基礎(chǔ)的稿子毀掉,拿出來(lái)的成果,衹要‘綉罷鴛鴦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成瞭風(fēng)氣”③方國(guó)瑜:《雲(yún)南史料目録了概説》,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4年。。方先生指出這一問(wèn)題的嚴(yán)重性:“這是造成中國(guó)學(xué)術(shù)所以發(fā)展緩慢的一大原因。”①方國(guó)瑜:《雲(yún)南史料目録概説》,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4年。因此方先生要打破知識(shí)私有的惡習(xí)。他説:“社會(huì)主義時(shí)代,要徹底批判這種惡劣作風(fēng),要多搞基礎(chǔ)工作,為大家用。”②同上。他認(rèn)為“所有知識(shí)都是屬於社會(huì)的,來(lái)自社會(huì),歸於社會(huì),非個(gè)人所得而私有。”③方國(guó)瑜:《雲(yún)南史料目録概説·弁言》,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4年。在整理雲(yún)南歷史資料方面,前人也做出過(guò)一些成績(jī)。如師範(fàn)《滇系》、王崧《雲(yún)南備征志》、秦光玉《續(xù)雲(yún)南備征志》、趙藩等《雲(yún)南叢書(shū)》等,可惜收録有關(guān)雲(yún)南歷史資料未為完備,或未完工。“像這樣網(wǎng)羅史料,匯編成書(shū),少數(shù)人出力,多數(shù)人應(yīng)用,對(duì)於研究雲(yún)南歷史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④方國(guó)瑜主編:《雲(yún)南史料叢刊》卷1 《前言》,昆明:雲(yún)南大學(xué)出版社,1998年。他要為雲(yún)南歷史研究建造一個(gè)磚瓦廠,因此他主編了《雲(yún)南史料叢刊》。也正是他的這種“少數(shù)人出力,多數(shù)人應(yīng)用”知識(shí)公有思想,深深地影響著我,成為我在這浮躁的社會(huì)氛圍中安於清平、不計(jì)得失、默默奉獻(xiàn)、做好工作的靜心丸,培養(yǎng)了我甘於坐“冷板凳”的工作作風(fēng)。
3.古籍整理者必須具備嚴(yán)謹(jǐn)?shù)膶W(xué)風(fēng)
古籍整理最需要的是嚴(yán)謹(jǐn)?shù)膶W(xué)風(fēng),稍不留意,就會(huì)出錯(cuò)。方先生在他生命旅途的最後時(shí)間裏對(duì)《雲(yún)南史料叢刊》編纂傾注了大量的精力,我也從中獲益匪淺。方先生每周都會(huì)到雲(yún)大老圖書(shū)館306 雲(yún)南地方史研究室來(lái)檢查我們的工作,我和徐文德、木芹老師都要將自己一周的工作嚮他匯報(bào),尤其是我,必須將所寫(xiě)的閲後記讀給他聽(tīng),有讀錯(cuò)或評(píng)價(jià)不當(dāng)?shù)牡胤剑较壬鷳{著驚人的記憶,都一一指出。如我寫(xiě)整理董慶善撰《雲(yún)龍記》一書(shū)後記時(shí),認(rèn)為《章實(shí)齋叢書(shū)·節(jié)鈔王知州雲(yún)龍記略》本更好,方先生批評(píng)我:“不是這樣説,不是這樣説。書(shū)沒(méi)讀遍,不要隨便下結(jié)論。”經(jīng)考證,王鳳文在雲(yún)龍做知州,得到此書(shū),對(duì)董氏之書(shū)稍加文字修改,讀起來(lái)文從字順而已,就改作“王鳳文《雲(yún)龍紀(jì)往》”,而章學(xué)誠(chéng)又將王本收入他自己的叢書(shū)中,加“節(jié)鈔”二字,並改“往”為“略”,就變成了章氏的整理本,其實(shí)他並沒(méi)有刪除王書(shū)的內(nèi)容,二人都是鈔襲,怎麼能説章本好呢?
方先生的每一個(gè)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都是在詳盡佔(zhàn)有資料,認(rèn)真考證分析史料的基礎(chǔ)上提出來(lái)的,對(duì)學(xué)生的不同觀點(diǎn),不是強(qiáng)制打壓,而是與之探討,幫助分析,以期形成最佳觀點(diǎn)。如關(guān)於南詔的社會(huì)性質(zhì),方先生的觀點(diǎn)與學(xué)術(shù)界相同,認(rèn)為是奴隸制。當(dāng)木芹老師最初提出“南詔前期(8世紀(jì)南詔統(tǒng)一洱海地區(qū)) 其社會(huì)最基礎(chǔ)為農(nóng)村公社”⑤(唐) 樊綽撰,嚮達(dá)原校,木芹補(bǔ)注:《雲(yún)南志補(bǔ)注》,昆明:雲(yún)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同時(shí)還保留著原始社會(huì)的痕跡(最為明顯的是平時(shí)為民,戰(zhàn)時(shí)為軍的鄉(xiāng)兵制等)”⑥同上。,即使是後期也不是奴隸制,而是“封建領(lǐng)主制在南詔社會(huì)中逐漸居於主導(dǎo)地位”①(唐) 樊綽撰,嚮達(dá)原校,木芹補(bǔ)注:《雲(yún)南志補(bǔ)注》,昆明:雲(yún)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時(shí),方先生不贊成,兩人差不多用了大半年的時(shí)間討論,最終方先生終於同意了木芹老師的觀點(diǎn)。
從以上兩件事中,可看出方先生嚴(yán)謹(jǐn)?shù)膶W(xué)風(fēng),而這種嚴(yán)謹(jǐn)?shù)膶W(xué)風(fēng)也在潛移默化中影響著他的每一位學(xué)生。
4.古籍整理者必須堅(jiān)持“不淹沒(méi)前人,要超過(guò)前人”的精神
古籍整理是一項(xiàng)傳承、弘揚(yáng)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溝通歷史與現(xiàn)實(shí)的文獻(xiàn)整理工作,是“一項(xiàng)十分重要的關(guān)係子孫後代的工作”。我們今天看到歷史文獻(xiàn)整理成果不外乎匯編、校注、注釋等形式,這是一種在儘量保持古籍原貌的基礎(chǔ)上,重新加以編撰、翻譯注釋,形成一種適合於今人利用、閲讀的新版本,是很難超越前人的。在古籍整理中如何把握學(xué)術(shù)繼承與創(chuàng)新的關(guān)係,實(shí)在是一門高深的學(xué)問(wèn),而方先生提出“不淹沒(méi)前人,要超過(guò)前人”的思想,將繼承與創(chuàng)新有機(jī)地融為一體,為古籍整理工作作出了榜樣。他説:“我們一方面不淹沒(méi)前人,另方面又要?jiǎng)龠^(guò)前人;衹有不淹沒(méi)前人,纔能勝過(guò)前人。”②方國(guó)瑜:《雲(yún)南史料目録概説·弁言》,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4年。要?jiǎng)龠^(guò)前人,必須對(duì)前人的成果作實(shí)事求是的評(píng)價(jià),須在收集研究史料中注意“三不”,即“前人不對(duì)的,你改過(guò)來(lái);前人不夠的,你作補(bǔ)充;前人不曾説到的,你提出來(lái),使之更上一層樓”③《雲(yún)南史料叢刊編纂緣起》,昆明:雲(yún)南大學(xué)歷史系地方史研究編印,1965年。。他為《雲(yún)南史料叢刊》製定的編纂原則是“搜集資料,求其完備”“得此一部,衆(zhòng)本咸在”“信得過(guò),用得上”④方國(guó)瑜主編:《雲(yún)南史料叢刊》卷1 《前言》,昆明:雲(yún)南大學(xué)出版社,1998年。。從收録史料的數(shù)量來(lái)説,《從刊》也是最多的,全書(shū)所收史籍400 餘種(篇、部),文物資料考説200 餘篇,其中收録碑文、墓志銘近60 篇,包括校勘記、注釋和方先生所作解題及徐文德、木芹等先生所作的後記,總字?jǐn)?shù)達(dá)1300 萬(wàn)字。這是以前任何一部有關(guān)雲(yún)南史料的書(shū)籍未曾達(dá)到的數(shù)字,遠(yuǎn)超被譽(yù)為“滇中掌故之尤著者”的清代王崧《雲(yún)南備征志》收録史籍(64 種,60 萬(wàn)字) 的數(shù)量。《雲(yún)南史料叢刊》不僅是對(duì)前人彙編史料的一種補(bǔ)充和完善,同時(shí)也是一種超越。他開(kāi)創(chuàng)前有概説,後有後記的新體例:“概説”是方國(guó)瑜教授對(duì)該篇史料源流、價(jià)值、真僞等考辦,“結(jié)合史事,發(fā)抒意見(jiàn)”;“後記”則是纂録整理者對(duì)各史籍的版本流傳、鑒別和選擇作出説明,也補(bǔ)充了些“概説”中未提到的意見(jiàn),評(píng)論長(zhǎng)短得失,既為研究者提供參考,又為初學(xué)者指引門徑。兩者互有照應(yīng),相得益彰,起到“辨章學(xué)術(shù),考鏡源流”的作用。對(duì)史料所進(jìn)行的全面、系統(tǒng)的考證,使《雲(yún)南史料叢刊》成了融資料性、學(xué)術(shù)性、思想性為一體的巨著,真正成為“不淹沒(méi)前人,但要超過(guò)前人”的雲(yún)南古籍整理成果。
二、古籍整理與研究必須具備的基本專業(yè)知識(shí)與能力
整理歷史文獻(xiàn)的傳統(tǒng)方法,可用“類、考、釋、纂”四個(gè)字來(lái)概括,具體來(lái)説,就是對(duì)歷史文獻(xiàn)進(jìn)行分類、考證、注釋、編纂四大系統(tǒng)的工作。所謂分類,即對(duì)歷史文獻(xiàn)進(jìn)行“辨章學(xué)術(shù),考鏡源流”的目録分類與檢索利用;所謂考證,即對(duì)歷史文獻(xiàn)的實(shí)證,包括版本、校勘、考據(jù)、辨僞、輯佚、補(bǔ)遺等文獻(xiàn)工作的內(nèi)容與方法;所謂注釋,包括對(duì)歷史文獻(xiàn)的斷句、音韻、訓(xùn)詁、注疏等;所謂編纂,也就是今天所説的匯編,包括叢書(shū)、類書(shū)、資料匯編、長(zhǎng)編等。衹有掌握這四大系統(tǒng)的基礎(chǔ)理論知識(shí),纔能較好地完成古籍文獻(xiàn)的整理研究工作。
從西漢劉嚮劉歆父子第一次大規(guī)模整理中國(guó)圖書(shū)開(kāi)始,目録、版本、校勘等內(nèi)容皆統(tǒng)一在校讎學(xué)之中,也稱之為傳統(tǒng)的目録學(xué),是從事文獻(xiàn)整理和研究的最基本、最重要的方法。
1.具有目録學(xué)專業(yè)知識(shí)
目録學(xué)是讀書(shū)治學(xué)的門徑。清代歷史學(xué)、經(jīng)學(xué)、文獻(xiàn)學(xué)大家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説:“目録之學(xué),學(xué)中第一緊要事,必由此問(wèn)途,方能得其門而入。”在卷二説:“不通《漢書(shū)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shū),藝文志者,學(xué)問(wèn)之眉目,著述之門戶也。”有了眉目,即有了頭緒,有了條理,纔有進(jìn)入門戶的條件。張之洞《書(shū)目答問(wèn)》第一條又説:“讀書(shū)不知要領(lǐng),勞而無(wú)功;知某書(shū)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為什麼學(xué)者們?nèi)绱藦?qiáng)調(diào)目録呢? 就因?yàn)樗谴蜷_(kāi)知識(shí)、提供史料寶庫(kù)的鑰匙。因此,在我第一次見(jiàn)方先生時(shí),他就問(wèn)我學(xué)過(guò)目録學(xué)沒(méi)有,我回答説沒(méi)學(xué)過(guò),他説,目録學(xué)對(duì)歷史研究很重要,是讀書(shū)治學(xué)的門徑,一定要補(bǔ)上。在我後來(lái)的學(xué)習(xí)工作中纔領(lǐng)會(huì)方先生要我補(bǔ)目録學(xué)的重要性。
學(xué)習(xí)雲(yún)南文獻(xiàn)整理,首先必須瞭解雲(yún)南有些什麼歷史書(shū)籍,如何在浩如煙海的群書(shū)中找出雲(yún)南史料,這些史料之間的關(guān)係如何,真僞如何,都需要有人指點(diǎn)。木芹教授給我找了一位最好的老師,就是讓我學(xué)習(xí)方先生的《雲(yún)南史料目録概説》。
《雲(yún)南史料目録概説》是“以讀書(shū)要求為主,結(jié)合各家,求其完備”①方國(guó)瑜:《雲(yún)南史料目録概説·略例》,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4年。的雲(yún)南史地專科目録,是方國(guó)瑜先生留心“記載滇事之書(shū)”近50年的結(jié)晶,為治雲(yún)南史地之學(xué)提供了讀書(shū)門徑。全書(shū)十卷,分文獻(xiàn)資料和文物資料兩大類。前五卷著録漢代至清代記載雲(yún)南史事之書(shū)或?qū)F獙9?jié)581 條,後五卷充分吸收和利用了考古發(fā)掘與民族調(diào)查的成果,著録漢至清時(shí)期雲(yún)南文物240 通。如你想知道漢晉時(shí)期雲(yún)南有些什麼書(shū),翻開(kāi)《概説》第一卷,收録傳記之屬有《史記·西南夷列傳》等10 餘種書(shū),地理志之屬有《漢書(shū)·地理志》《水經(jīng)注》西南諸水等11 種(篇) 書(shū),地方志之屬有楊終《哀牢傳》《華陽(yáng)國(guó)志·南中志》等6種(篇),辭章及雜載之屬有《喻巴蜀檄》《廣志》(摘專條) 等6 種(篇、條),漢晉之作共計(jì)30 餘種(篇、條)。
目録學(xué)是“辨章學(xué)術(shù),考鏡源流”的學(xué)問(wèn)。如何將雜亂無(wú)序的群書(shū)編制成便於檢索的目録書(shū),核心是分類。鄭樵《通志·校讎略》卷七十一“編次必謹(jǐn)類例”説:“學(xué)之不專者,為書(shū)之不明也。書(shū)之不明者,為類例之不分也”;又説“類例既分,學(xué)術(shù)自明,以其先後本末具在”。方先生認(rèn)為:“所謂‘書(shū)’ 即史料,‘類例’ 即目録”①方國(guó)瑜:《雲(yún)南史料目録概説·弁言》,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4年。。在目録編排中,他根據(jù)史料的多寡立目分類,通過(guò)類例來(lái)反映雲(yún)南的學(xué)術(shù)情況。如文獻(xiàn)部分,漢晉、唐宋、元時(shí)期各類僅立二級(jí)目録,明、清時(shí)期史料內(nèi)容豐富,增設(shè)三級(jí)乃至四級(jí)目録。以地理志的著録為例,漢晉、唐宋僅有“地方史志”“地方風(fēng)土志”二級(jí)目録,地方志書(shū)是保存地方歷史文獻(xiàn)的主要資料庫(kù),明清兩代地方志書(shū)的編撰迅速發(fā)展,明代九次修省志,流傳至今五部;清代有康熙、乾隆、道光、光緒、續(xù)光緒五部官修通志,明清兩代所修地方志流傳至今者有200 餘種,明代二級(jí)“地理志之屬”下設(shè)有“總志”“省志”“郡邑志”“專志”四個(gè)三級(jí)目録。至清代,除有與明代相同的四個(gè)三級(jí)目録外,在“省志”下細(xì)分“官修省志”“私人修省志”兩個(gè)四級(jí)目録。又在“專志”下設(shè)“賦役志”“山川志”“礦産志”“民族志”“武備志”“學(xué)校志”六個(gè)四級(jí)目録。從漢晉時(shí)期的“地方史志之屬”二級(jí)目録到清代“地理志之屬”二級(jí)目録下有三級(jí)、四級(jí)目録的設(shè)立,清楚地反映了雲(yún)南方志學(xué)的發(fā)展綫索,説明方志學(xué)在清代的迅速發(fā)展與成熟。“如此條分縷析,將史料按不同層次有機(jī)地組織起來(lái),不僅具有綱舉目張、執(zhí)簡(jiǎn)御繁的作用,而且能收到‘辨章學(xué)術(shù)、考鏡源流’ 的效果。”②張振利:《試論方國(guó)瑜對(duì)中國(guó)目録學(xué)的貢就》,載《雲(yún)南大學(xué)本科優(yōu)秀畢業(yè)論文》,昆明:雲(yún)南大學(xué)出版社,2009年。
2.版本的知識(shí)
“版本”一詞,出現(xiàn)於雕版印刷盛行的宋代,主要是為了區(qū)分手鈔本與雕版刊印的書(shū)籍的不同,將雕版刊印的書(shū)籍稱為版本,後泛指同一書(shū)籍在不同歷史時(shí)期所流傳下來(lái)的不同樣式的各種本子。版本學(xué)是研究各種版本的用紙、墨色、字體、刀法、藏章印記、款式題跋、行款版式、封面裝幀、文字內(nèi)容等,以辦明版本的真僞,分清版本精粗優(yōu)劣的學(xué)問(wèn)。掌握版本學(xué)知識(shí),可避免誤讀古書(shū),鑒別判定古籍的文物價(jià)值和使用價(jià)值,為校勘、輯佚、辨僞等學(xué)科的理論研究和具體實(shí)踐提供可信的底本。如我在前面提到的董慶善作的《雲(yún)龍記》一書(shū),經(jīng)方先生考證王鳳文《雲(yún)龍紀(jì)往》、章學(xué)誠(chéng)《節(jié)鈔王知州雲(yún)龍記略》是僞書(shū),雲(yún)龍縣教育科1957年油印的董本,纔是最接近原書(shū)的本子。
3.校勘的知識(shí)
所謂校勘,是糾正古籍在流傳的過(guò)程中産生訛、脫、衍、倒的字、句錯(cuò)誤。所謂訛,即誤。誤是指文字字形失真,即古諺所説:“書(shū)三寫(xiě),魚(yú)成魯,虛成虎。”形近、音近引起字訛的現(xiàn)象比較普遍。如師—帥、穴—內(nèi)、比—北、確—榷、舅—舊等。脫,是指古書(shū)在傳鈔、傳刻過(guò)程中漏字或漏句。衍,指古書(shū)在傳鈔、傳刻過(guò)程中多寫(xiě)了字句。倒,又稱錯(cuò)簡(jiǎn),指古書(shū)在傳鈔、傳刻過(guò)程中,字句、篇章順序顛倒錯(cuò)亂。
校勘的方法,一般先廣泛搜集各種本子和相關(guān)資料,並辨析他們之間的淵源關(guān)係;對(duì)校各本,列出異文,發(fā)現(xiàn)疑誤;分別疑誤的類型,進(jìn)行分析,舉出根據(jù),説明理由,校改謬誤;撰寫(xiě)敘例,寫(xiě)出校記,清楚準(zhǔn)確表達(dá)校勘成果。校勘的目的是“擇善而從,版式歸一”,形成最接近歷史文獻(xiàn)原貌的最佳版本。方先生主編的《雲(yún)南史料叢刊》,就充分運(yùn)用了校勘的方法。
4.綜合研究分析史料能力
方先生針對(duì)漢文文獻(xiàn)中有關(guān)雲(yún)南歷史文獻(xiàn)“一少、二不確、三多歪曲”的實(shí)際情況,提出了用馬列主義辯證法和唯物主義歷史觀分析研究邊疆民族地區(qū)歷史文獻(xiàn)的理論和方法,將傳統(tǒng)的考據(jù)學(xué)、辨僞學(xué)提高到一個(gè)嶄新的階段。方先生精闢的闡述:“……批判地研究史料,要從説明史料來(lái)源入手,明確史事之時(shí)間、空間、環(huán)境與撰人之活動(dòng),而後確定史料之歷史意義,闡明歷史實(shí)際。其來(lái)源過(guò)程,有在史料本身已説明,亦有未具,則當(dāng)多作考究。”①方國(guó)瑜:《雲(yún)南史料目録概説·略例》,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4年。因此,方國(guó)瑜先生研究雲(yún)南歷史文獻(xiàn)主要從以下四方面入手。
第一,通過(guò)考訂作者的生平事跡、作者的時(shí)代、作者的學(xué)術(shù)等問(wèn)題,考證史料來(lái)源,以確定一書(shū)的價(jià)值。如考訂《史記·西南夷列傳》,依據(jù)《史記》中司馬遷的《自序》《河渠書(shū)》《南越尉佗傳》《漢書(shū)·武帝紀(jì)》等資料肯定元鼎六年司馬遷為中郎將,並為經(jīng)略西南,親至西南調(diào)查研究寫(xiě)成的《史記·西南夷列傳》是一部“信而有徵,非尋常可比”的重要資料。對(duì)於樊綽《雲(yún)南志》的史料價(jià)值,前人有不同意見(jiàn):胡渭《禹貢錐指》以樊綽沒(méi)有親自到過(guò)雲(yún)南而貶低其書(shū)的價(jià)值。馬長(zhǎng)壽《南詔國(guó)內(nèi)的部族組成和奴隸制度·前言》認(rèn)為樊綽親自到過(guò)雲(yún)南,對(duì)南詔的軍事、政治上的報(bào)導(dǎo),是他親耳所聞,親目所見(jiàn)“真是第一手的可靠資料”。方先生以其嚴(yán)密有據(jù)的考證指出:“樊綽《雲(yún)南志》十卷中之大部分材料,為親歷目睹之記録。”②方國(guó)瑜:《雲(yún)南史料目録概説》,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4年。樊綽主要採(cǎi)録袁滋的《雲(yún)南記》,而《雲(yún)南記》又採(cǎi)用了南詔文臣編纂之地方志與檔案資料。所以這部書(shū)大體保有第一手的記録,但樊綽並沒(méi)有親自到過(guò)雲(yún)南。
第二,通過(guò)版本和它書(shū)記載,考證史料來(lái)源,鑒別史料的真僞。方先生認(rèn)為古籍流傳“在長(zhǎng)時(shí)期中,輾轉(zhuǎn)傳鈔、翻刻,以及注解、評(píng)論,見(jiàn)於各家著録之傳本,知其大概。”①方國(guó)瑜:《雲(yún)南史料目録概説·略例》,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4年。如明代學(xué)者楊慎自述《滇載記》是自譯白文《白古通》《玄峰年運(yùn)志》,“稍為刪正,令其可讀”。萬(wàn)曆《雲(yún)南通志》也説是楊慎翻譯《白古通》等書(shū)而著《滇載記》。實(shí)際上《白古通》《玄峰年運(yùn)志》諸書(shū)早有漢文譯本,衹是語(yǔ)言不夠流暢通達(dá),經(jīng)楊慎修改潤(rùn)色而已,就謊稱是他翻譯的。所以方先生批評(píng)楊慎有“喜歡造假”的惡習(xí),戳穿其“自述史料來(lái)源及其所作僞説以欺世人”的騙局。
第三,用“洞察史料之社會(huì)性、階級(jí)性”的方法,分析研究歷史文獻(xiàn),以闡明歷史真相。雲(yún)南地處西南邊陲,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發(fā)展不平衡,且少數(shù)民族雜居,長(zhǎng)期遭受反動(dòng)階級(jí)“內(nèi)王外霸”的大民族主義政策統(tǒng)治,以及各部族統(tǒng)治者之地方民族主義,時(shí)有爭(zhēng)端,造成雲(yún)南歷史現(xiàn)象錯(cuò)綜複雜,而“所得歷史資料既奇缺,且大都誣衊”。為闡明歷史真相,方先生強(qiáng)調(diào)研究史料“更重要者,則為洞察史料之社會(huì)性、階級(jí)性”,“結(jié)合歷史事實(shí),作適當(dāng)分析,提出問(wèn)題,纔有助於研究歷史”②同上。。因而對(duì)封建文臣儒士把雲(yún)南説成是“別種殊域”的“化外”之地的記載,方先生持批判態(tài)度,一一指出;對(duì)企圖分裂中國(guó),分割雲(yún)南的外國(guó)漢學(xué)家,則給予有力駁斥。如《宋史》把大理列入“外國(guó)傳”,南宋儒生臆造“宋揮玉斧”的典故,方先生依據(jù)昌慤《議買大理馬》、楊佐《買馬記》、郭松年《大理行記》及《建炎以來(lái)繫年要録》《朝野雜記》《玉海》《文獻(xiàn)通考》諸書(shū)言大理馬事,從分析南宋所處的形勢(shì)、經(jīng)濟(jì)狀況入手,闡明南宋時(shí)西南與內(nèi)地加強(qiáng)聯(lián)繫,是歷史發(fā)展之必然,以販賣大理馬一事可以知之,宋太祖劃大渡河為界並非事實(shí)。且強(qiáng)調(diào)指出,宋王朝勢(shì)力微弱,不能致力經(jīng)營(yíng)雲(yún)南,但宋王朝不等於中國(guó),不能把大理排斥在中國(guó)之外。大理三百年的歷史,與全國(guó)歷史緊密聯(lián)繫,為中國(guó)整體一部分。再如出版於1904年法國(guó)伯希和所作《交廣印度兩道考》,把雲(yún)南劃為“中國(guó)官?gòu)d勢(shì)力所不及”③方國(guó)瑜:《中國(guó)西南歷史地理考釋》,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7年。的地區(qū),以南詔為專用之地名,置於中國(guó)之外,把南詔、大理説成是中國(guó)之外的獨(dú)立國(guó)家。方國(guó)瑜先生據(jù)1958年中國(guó)科學(xué)院考古所發(fā)掘唐代長(zhǎng)安城大明宮故址出土之“雲(yún)南安撫使印”封泥④方國(guó)瑜:《雲(yún)南史料目録概説》,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4年。以及《舊唐書(shū)》《新唐書(shū)》《唐會(huì)要》等文獻(xiàn)記載貞元年間唐朝設(shè)雲(yún)南安撫使統(tǒng)領(lǐng)南詔的歷史事實(shí)駁斥説:“漢朝以益州郡為政區(qū)名號(hào),唐朝以雲(yún)南安撫使司為政區(qū)名號(hào),而滇王與南詔則為世襲世職,不得為地名也。”⑤同上。“ ‘雲(yún)南王’ 為地方官職,與其他地方官職之政權(quán)在形式上有差別,而同為國(guó)家版圖之內(nèi)。”①方國(guó)瑜:《雲(yún)南史料目録概説》,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4年。“伯希和自負(fù)熟悉雲(yún)南歷史,其書(shū)為帝國(guó)主義所賞識(shí),我國(guó)學(xué)人亦有推崇者。其惡劣影響至今未完全揭穿,其謬論之基點(diǎn)即‘以南詔之名,名其全國(guó)’ 之謬説,毫無(wú)根據(jù),且違反歷史實(shí)際,不可不辦明之。”②同上。從這些論述中,説明方先生並非僅僅著眼於著録雲(yún)南史料目録,而更通過(guò)著録研究,進(jìn)而揭示歷史的真相,回答歷史和現(xiàn)實(shí)提出的問(wèn)題,維護(hù)祖國(guó)統(tǒng)一與民族團(tuán)結(jié)。
第四,説書(shū)與論史的結(jié)合,確定歷史文獻(xiàn)的史料價(jià)值。方國(guó)瑜先生在著録雲(yún)南史料目録時(shí),不僅注意對(duì)史料的來(lái)源、流傳認(rèn)真考核,去粗取精,去僞存真,而且確定史料的歷史價(jià)值,注重結(jié)合歷史事實(shí)進(jìn)行評(píng)述,以求闡明歷史真相及發(fā)展規(guī)律。如概説《元史·賽典赤傳》,不僅歷敘賽典赤個(gè)人身世,而且考校有關(guān)建立雲(yún)南行省的大事,諸如“建立統(tǒng)治機(jī)構(gòu)”“建立社會(huì)制度與發(fā)展生産”“傳授儒學(xué)開(kāi)科取士”,指出元代在雲(yún)南按田畝、人丁徵賦稅,為前代所未有,説明雲(yún)南部分地區(qū)已是地主所有制,或由大土地所有制嚮地主所有制過(guò)渡,清查田畝,定賦稅,保證私人佔(zhàn)有土地為生産資料所有制一大變革。書(shū)中幾乎每一篇“概説”都結(jié)合歷史事實(shí)進(jìn)行評(píng)述,使《雲(yún)南史料目録概説》成為既是一部有關(guān)雲(yún)南史料的專題著録,又是一部對(duì)雲(yún)南歷史發(fā)展的若干問(wèn)題進(jìn)行論述的學(xué)術(shù)專著。在雲(yún)南歷史文獻(xiàn)學(xué)和歷史學(xué)上都做出了開(kāi)創(chuàng)性的貢獻(xiàn)。提供了整理邊疆民族地區(qū)古籍的原則與方法。
綜合分析史料的能力,就是通過(guò)各種古籍整理研究的方法,對(duì)古籍進(jìn)行一種綜合性的全方位考證,對(duì)歷史文獻(xiàn)的去僞存真,這就是古籍整理研究的重要原則,即恢復(fù)或保持古籍的原貌,不能隨意篡改。
三、古籍整理與歷史研究重在闡述“中國(guó)歷史發(fā)展整體性”
1.“中國(guó)歷史發(fā)展整體性”理論的提出
方國(guó)瑜“ ‘中國(guó)歷史發(fā)展整體性’ 理論來(lái)源於他長(zhǎng)期研究祖國(guó)西南邊疆及中國(guó)少數(shù)民族史的‘邊疆視角’。”③潘先林:《家國(guó)情懷書(shū)生本色方國(guó)瑜先生的中國(guó)邊疆學(xué)研究》,載《西南古籍研究》,昆明:雲(yún)南大學(xué)出版社,2016年。對(duì)封建史家“異內(nèi)外”的“春秋大意”“夷夏大防”思想的深刻認(rèn)識(shí),對(duì)居心叵測(cè)外國(guó)漢學(xué)家企圖分割雲(yún)南、分裂中國(guó)野心的高度警惕,醖釀了他“中國(guó)歷史發(fā)展整體性”理論。1944年他在《雲(yún)南政治發(fā)展之大勢(shì)》一文中首次指出:“今日之雲(yún)南,為中國(guó)之一部分,自有歷史以來(lái)之雲(yún)南,即為中國(guó)之一部分,故雲(yún)南之歷史為中國(guó)歷史之一部分。”①方國(guó)瑜:《雲(yún)南政治發(fā)展之大勢(shì)》,載《邊政公論》,1944年第3 卷第2 期。方國(guó)瑜:《雲(yún)南史料目録概説·弁言》,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4年。1963年4月,在雲(yún)南大學(xué)校慶40 周年之際作了《論中國(guó)歷史發(fā)展的整體性》的學(xué)術(shù)報(bào)告②方國(guó)瑜著、林超民編:《方國(guó)瑜文集》第1 輯,昆明:雲(yún)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全面系統(tǒng)地闡述了這一思想,整體思想的核心,一是“歷代王朝史與中國(guó)史應(yīng)當(dāng)有所區(qū)別”③同上。“王朝的疆域,並不等於中國(guó)的疆域;王朝的興亡,並不等於中國(guó)的興亡。”④同上。“中國(guó)歷史,既是生活在這塊土地上各民族人民的歷史,就應(yīng)該包括他們的全體歷史,不能‘變更伸縮’。中國(guó)歷史是有其整體性的,在整體之內(nèi),不管出現(xiàn)幾個(gè)政權(quán),不管政權(quán)如何不統(tǒng)一,並沒(méi)有破裂了整體,應(yīng)當(dāng)以中國(guó)整體為歷史的範(fàn)圍,不能以歷代王朝疆域?yàn)闅v史的範(fàn)圍。”⑤同上。“統(tǒng)一的概念,主要就政權(quán)而言。……政權(quán)的統(tǒng)一與不統(tǒng)一,衹能是整體之內(nèi)的問(wèn)題,而不是整體割裂的問(wèn)題。”⑥同上。二是“中國(guó)歷史上不在王朝版圖之內(nèi)的民族關(guān)係,應(yīng)該放在中國(guó)歷史之內(nèi)來(lái)處理,不能以異國(guó)的關(guān)係來(lái)處理。”⑦同上。因?yàn)椤扒貪h以來(lái)中國(guó)形成比較穩(wěn)定的多民族國(guó)家,以漢族為主幹,漢族與其他各族聯(lián)繫為一個(gè)整體”⑧同上。“中國(guó)歷史之所以形成整體發(fā)展,是由於有它的核心起著主幹作用。這個(gè)核心就是早在中原地區(qū)形成的諸夏族,後來(lái)發(fā)展成為漢族的人們共同體。……以漢族為主流的文化的發(fā)展和傳播,形成中國(guó)體系的文化,在中國(guó)整體之內(nèi),起著主幹作用”⑨同上。“這種以漢族為主幹的與全國(guó)各地各族的聯(lián)繫,由點(diǎn)而綫而面,成為中國(guó)整體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這一聯(lián)繫的面,就是中國(guó)的領(lǐng)域,也就是中國(guó)歷史的範(fàn)圍。”⑩同上。
2.西南歷史發(fā)展是中國(guó)歷史發(fā)展整體的一部分
方先生在考釋西南歷史地理時(shí),將西南歷史地理看作中國(guó)整體的一部分,主張研究西南史地:“必須把它提到全國(guó)範(fàn)圍之內(nèi)來(lái)考慮,因?yàn)樽怨乓詠?lái),這個(gè)地區(qū)是偉大祖國(guó)版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政區(qū)設(shè)置的地名以及幾次大的改變,都是與全國(guó)整體性是息息相關(guān)的;如果離開(kāi)全國(guó)形勢(shì),孤立地談?wù)撨@個(gè)問(wèn)題,必然談不清楚,也不會(huì)得出正確的結(jié)論。”?方國(guó)瑜:《雲(yún)南政治發(fā)展之大勢(shì)》,載《邊政公論》,1944年第3 卷第2 期。方國(guó)瑜:《雲(yún)南史料目録概説·弁言》,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4年。“西南地區(qū),為統(tǒng)一多民族的偉大祖國(guó)組成部分,自有歷史以來(lái),生息在這地區(qū)的各族人民,……共同創(chuàng)造了偉大祖國(guó)的歷史。西南地區(qū)之所以成為祖國(guó)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並不是由於歷代帝王的好勤遠(yuǎn)略,乃是各族勞動(dòng)人民緊密聯(lián)結(jié)共同發(fā)展的結(jié)果。”?方國(guó)瑜:《中國(guó)西南歷史地理考釋·略例》,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7年。那些視南詔、大理為“獨(dú)立發(fā)展”的國(guó)家,或“忽必烈滅大理,雲(yún)南開(kāi)始成為內(nèi)域”①方國(guó)瑜:《中國(guó)西南歷史地理考釋·略例》,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7年。,乃至1956年編印的中國(guó)歷史地圖,違反歷史事實(shí)地將“元代以前各圖幅,把西南地區(qū)的全部或局部劃出國(guó)界外,即明清圖也不免有這種情況”②同上。等等,都是“所謂春秋大義形成王朝本位的概念,以王朝政治活動(dòng)來(lái)限制中國(guó)疆域,為王朝服務(wù)的歷史資料,不符合歷史事實(shí)”③同上。。“這是遵循反動(dòng)統(tǒng)治者之衹有王朝,不知有中國(guó)的謬論”④同上。,必須“嚴(yán)格批判”。
方先生對(duì)西南歷史研究不局限於文獻(xiàn)的字面解釋,更多的是從歷史的角度分析其深層含義。他説:“歷史上的地名,是歷史活動(dòng)的空間符號(hào),離開(kāi)歷史則地名沒(méi)有意義,不從歷史活動(dòng)來(lái)考釋地名,則未必能準(zhǔn)確。”⑤方國(guó)瑜:《雲(yún)南史料目録概説·弁言》,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4年。“秦統(tǒng)一中國(guó),經(jīng)略此諸地,開(kāi)道置吏,並非偶然也。”⑥方國(guó)瑜:《中國(guó)西南歷史地理考釋》,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7年。“南朝雖未能切實(shí)統(tǒng)治其地,仍不斷任命寧州刺史……至唐天寶初年之爨守隅,王朝任命爨氏為刺史、為都督,亦凡二百年。”⑦同上。南詔、大理“雖衹加封號(hào),為西川節(jié)度兼雲(yún)南安撫司,不設(shè)直接統(tǒng)治的州、縣政權(quán)機(jī)構(gòu),仍是邊州性質(zhì)的一部分”⑧方國(guó)瑜著、林超民編:《方國(guó)瑜文集》第1 輯,昆明:雲(yún)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屬中國(guó)版圖,為中國(guó)史的一部分。元明清的“土司政權(quán)的存在,並不以民族特徵為基礎(chǔ),而是以社會(huì)特徵為基礎(chǔ)的。並改土歸流也不是以帝王的主觀願(yuàn)望所決定,而是以社會(huì)發(fā)展階段決定的”。“在社會(huì)發(fā)展不平衡的地區(qū),建立政權(quán)有不同的形式(土官或流官),而國(guó)家的完全主權(quán)的沒(méi)有差別的,在統(tǒng)一的國(guó)家之內(nèi),並沒(méi)有‘半獨(dú)立性’ 的政權(quán)存在。又在多民族的國(guó)家之內(nèi),並不以政權(quán)的改變而否定民族區(qū)別。這些歷史事實(shí),是不容歪曲的。”⑨方國(guó)瑜:《中國(guó)西南歷史地理考釋》,北京:中華書(shū)局,1987年。方先生以確鑿的歷史事實(shí),令人信服地證明:西南各民族人民自秦漢以來(lái),就是統(tǒng)一多民族國(guó)家的一個(gè)組成部分,西南歷史的發(fā)展,統(tǒng)一在中國(guó)歷史發(fā)展的整體之中。
3.古籍整理與歷史研究中的家國(guó)情懷
為什麼當(dāng)西南邊疆危機(jī)時(shí),方先生毅然轉(zhuǎn)入西南史地研究,並提出“中國(guó)歷史發(fā)展整體性”的理論? 這與他從小接受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的熏陶密不可分。鄉(xiāng)土文化中“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有名不負(fù)此生”的思想與儒家經(jīng)典著作中“修身、齊家、治國(guó)、平天下”“達(dá)則兼濟(jì)天下,窮則獨(dú)善其身”等儒家文化精髓已深深融入了他的生命之中,報(bào)效國(guó)家、回饋鄉(xiāng)梓的使命在他的人生旅程中愈來(lái)愈清晰。同時(shí),方國(guó)瑜先生醉心於雲(yún)南歷史文獻(xiàn)的分析研究,從中獲得千百年地方文化根脈的涵養(yǎng),獲得“睹喬木而思故家,考文獻(xiàn)而愛(ài)鄉(xiāng)邦”的知識(shí)補(bǔ)充與思想源泉。當(dāng)國(guó)家、民族遇到危機(jī)時(shí),知識(shí)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責(zé)任意識(shí)直接上升為國(guó)家意識(shí)。正如林超民教授所説:“中國(guó)歷史發(fā)展的整體性學(xué)説的提出,體現(xiàn)了一個(gè)學(xué)者真摯、赤誠(chéng)、廣闊的愛(ài)國(guó)主義情懷,體現(xiàn)了他不是為學(xué)術(shù)而學(xué)術(shù),而是為國(guó)家的統(tǒng)一、民族的進(jìn)步、社會(huì)的發(fā)展、為政府解決祖國(guó)邊疆民族問(wèn)題孜孜不倦工作的精神。”①林超民:《整體性:方國(guó)瑜的理論貢獻(xiàn)》,載《雲(yún)南民族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社會(huì)科學(xué)版) 30 卷第5 期,2013年9月。納西族木芹教授認(rèn)為:“先生的史地之學(xué)源於極強(qiáng)的國(guó)家情結(jié)……納西族從來(lái)就有維護(hù)國(guó)家統(tǒng)一之心。”②木芹口述,張昌山、木霽弘撰文:《回憶方國(guó)瑜先生(上)》,《雲(yún)南日?qǐng)?bào)》(文史哲),2012年2月24日。潘先林教授認(rèn)為:“國(guó)家情結(jié)是方國(guó)瑜先生西南邊疆研究的基石,他的論著始終以濃烈的家國(guó)情懷著稱於世。我們衹有對(duì)此有深刻的認(rèn)識(shí)與體察,纔能與方國(guó)瑜先生産生共鳴,纔能更好地學(xué)習(xí)和閲讀他的論著,從而在更高的起點(diǎn)上推動(dòng)中國(guó)邊疆學(xué)搆築的嚮前發(fā)展。”③潘先林:《家國(guó)情懷書(shū)生本色方國(guó)瑜先生的中國(guó)邊疆學(xué)研究》,載《西南古籍研究》,昆明:雲(yún)南大學(xué)出版社,2016年。我們可以説衹有熱愛(ài)家鄉(xiāng)、熱愛(ài)祖國(guó),纔可能産生以天下為己任的責(zé)任意識(shí),纔可以在歷史研究與整理古籍工作中體現(xiàn)自己的家國(guó)情懷,而家國(guó)情懷正是整理古籍與歷史研究工作者所追求的最高學(xué)術(shù)價(jià)值與思想境界。
結(jié) 語(yǔ)
回想跟隨方先生學(xué)習(xí)古籍整理與研究的里程,我的每個(gè)成長(zhǎng)都離不開(kāi)方先生對(duì)我的培養(yǎng)與影響,離不開(kāi)木芹、徐文德、林超民老師對(duì)我的幫助與指導(dǎo)。今天在這裏無(wú)論講從事古籍整理的堅(jiān)定信念,古籍整理與研究必備專業(yè)能力,還是講“中國(guó)歷史發(fā)展整體性”理論,都不能把方先生文獻(xiàn)學(xué)及歷史研究的治學(xué)理論説清楚、講透徹、説完全,但方先生的一切都深深地影響著我,我一直是這樣想的,先生們甘於坐冷板凳,從不計(jì)較自己得失,在古籍整理崗位上無(wú)私奉獻(xiàn),我有幸成為他們中的一員,也就照著他們這樣做,我雖沒(méi)有創(chuàng)新,但也從來(lái)沒(méi)有覺(jué)得喫虧,衹覺(jué)得自己在古籍整理這個(gè)崗位,就應(yīng)該這樣做。正是積極努力安心做自己的工作,把工作做好了,工作也就成就了我的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