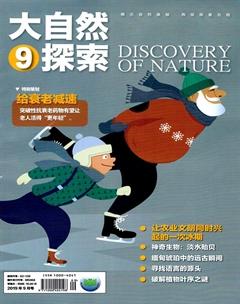緬甸琥珀中的遠古瞬間
邵峰
緬甸的琥珀開采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主要產區位于緬甸北部克欽邦的胡康河谷,但直到1836年英國探險家哈內來到胡康河谷前,很少有其他國家的收藏家了解這里的琥珀資源。1894年,德國化學家艾姆在分析了胡康河谷的琥珀后發現,其化學構成和波羅的海琥珀有所不同。又因為其硬度比其他產區的琥珀更高,所以艾姆將緬甸琥珀命名為“緬甸石”。
20世紀30年代,迫于全球戰亂局面,緬甸琥珀礦大批關閉,對琥珀的研究也一度中止。20世紀70年代,蘇聯科學家開始前往緬甸收購琥珀并用于研究。在隨后的20多年里,琥珀研究熱逐漸興起。1999年,胡康河谷的琥珀商業開采活動恢復。2000年,一家加拿大礦業公司在緬甸進行大規模琥珀開采活動,挖掘出的琥珀化石主要銷往美國,其中不少被科研機構購買。接下來,從緬甸琥珀中發現新品種生物的研究成果陸續被發表。

2011年,科學家對胡康河谷琥珀周圍沉積物進行鈾鉛定年分析,鑒定出這里的琥珀形成于距今9900萬年前(白堊紀,當時恐龍還未滅絕),推翻了1934年奇伯關于胡康河谷琥珀形成于4000萬年前(始新世)的觀點。
在全世界七個主要的白堊紀琥珀沉積區中,胡康河谷出產的生物內含物琥珀數量最大,多樣性最高。原因主要是胡康河谷在9900萬年前是濕潤的熱帶雨林環境,生物多樣性極高。那里的環境非常適合已經滅絕的貝殼杉生長。貝殼杉和同為南洋杉科的其他品種一樣,樹脂分泌十分旺盛,因此有利于形成內含物琥珀。

遠古蜥蜴
2006年,科學家從一塊波羅的海琥珀中包裹的蜥蜴標本身上,發現了從未見過的趾結構和類似今天蜥蜴腳趾內側的肉墊。2016年,11塊來自緬甸、形成年代更久遠的蜥蜴琥珀化石正式對外公布。其中一種蜥蜴一開始被認為是一種古老變色龍,不過后來被劃分到兩棲動物類。雖然這些遠古蜥蜴長度都在幾厘米,不過,在計算機斷層微型掃描的幫助下,科學家還是看到了它們腳趾上和今天蜥蜴一樣輔助攀爬的肉墊。其中一件蜥蜴標本的舌向外伸出,它的舌尖狹長,不同于已知任何一種蜥蜴或蛇的舌部構造。

兩條古蛇
緬甸的熱帶森林是蛇類的理想棲息環境。雖然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沒有關于蛇琥珀發現的報道,但科學家相信,蛇珀出現只是時間問題。果然,2016年蛇珀終于露面,而且同年里發現了兩枚蛇珀。
這兩塊蛇珀中包裹的蛇都是幼體:一條保存了完整骨骼,被中國地質大學的邢立達副教授命名為“緬甸曉蛇”;另一條只殘留了一半軀體,歸屬尚不明確。那條完整的蛇標本有約97塊椎骨,其尺寸和今天的紅尾管蛇等蛇類的幼體相近。通過和生活在古代南方超級大陸——岡瓦納大陸的蛇的化石進行骨結構比較,兩者之間存在多處相似。然而,緬甸在白堊紀時位于另一塊名為勞倫大陸的北方超級大陸。這說明緬甸曉蛇起源于南半球,然后才逐漸分布到北半球,并維持了數千萬年前的原始形態。

花朵制造種子
一枚緬甸琥珀封存了被子植物受精的瞬間。2014年,科學家在一枚緬甸琥珀中發現了由18朵小花(每朵直徑僅為1毫米)組成的花序。當樹脂淌過這株植物時,其中一朵小花受精的瞬間被凝固下來。在這朵小花的柱頭上,花粉粒已經萌發出花粉管并插入柱頭。接下來,花粉粒中
的兩枚精子將順著花粉管進入子房,分別和胚珠中的卵細胞和極核受精。這是目前人類發現的最古老的花粉管進入柱頭的化石證據。
花是植物的生殖器官,結構更復雜的花能讓植物通過蟲媒更精準地傳播花粉,而不是借助風力漫無目的地四處散播。被子植物的“開花革命”也讓它們成功地覆蓋絕大部分陸地。

昆蟲和蘇鐵的初次合作
依靠昆蟲授粉可能不是被子植物的首創。很長時間以來,科學家都認為,松柏和銀杏等現代裸子植物幾乎只靠風傳播種子。2018年,一枚琥珀告訴了科學家一個不同的演化故事。
在一枚9900萬年前形成的緬甸琥珀化石中保存著一只甲蟲。南京科學院的科學家注意到了在它身旁的一些小球。三維掃描成像結果顯示,小球其實是蘇鐵的花粉。但花粉并沒有位于甲蟲身上,而是散落在其附近。通過顯微鏡觀察,科學家從這只長約2毫米的甲蟲頭部發現了極長的下顎須——傳粉昆蟲的標志性特化口器。從先前的化石證據看,從至少2.5億年前起,甲蟲和蘇鐵植物就形影不離了。科學家估計,蘇鐵從至少1.67億年前就開始依賴昆蟲傳粉。被子植物第一次出現是在約1.3億年前。可見,裸子植物從很早之前就和昆蟲開始了協同進化,傳粉可能并不是被子植物首創。

長金屬角的“吸血螞蟻”
2016年,科學家從緬甸琥珀中發現“來自地獄的螞蟻”。這種已經滅絕的遠古螞蟻有長矛般向上方突出的下顎,其中一些的下顎正上方還長有一個角狀結構。在這種螞蟻的口器附近長有和現代陷阱顎蟻一樣的纖毛。陷阱顎蟻的下顎周圍長有感應觸毛,一旦觸發,它們鋒利的下顎會飛快閉合。科學家猜測,如果有獵物觸發了“地獄螞蟻”的纖毛,它們就會立刻抬起長長的下顎,將獵物抵在下顎上方的尖角上并刺穿獵物。整個過程如同行刑般殘忍。
計算機斷層掃描結果揭示了更加驚人的細節:螞蟻下顎上方的角質尖角還含有微量鐵,這可能是為了加固尖角的強度,避免尖角被下顎反復撞擊而折斷。一些現代昆蟲依然會用鋅、鐵、鎂等金屬加固下顎以提高耐磨度。
科學家還發現:“地獄螞蟻”不但長有金屬強化過的角,它們可能還“吸血”。當它們的下顎向上頂起時,昆蟲的“血液”——血淋巴會順著下顎流淌,最后流進“地獄螞蟻”的口中。

菊石外殼
9900萬年前的一塊緬甸琥珀讓人們看到了白堊紀海灘上的生物“快照飛海蝸牛、等足類動物、螨蟲、甲蟲、真蠅、黃蜂、蜘蛛、千足蟲和菊石。通常樹脂只能包裹位于樹上或樹下土地中的生物,作為海洋生物的菊石(章魚等腕足動物的祖先)是怎么被包裹進樹脂里而形成琥珀的呢?
菊石最早出現于4億多年前,它們曾經和恐龍一同生活在當時的地球上,并在6500萬年前和恐龍一同滅絕。科學家對這塊菊石的形成過程做了如下猜測:緬甸海邊的一株貝殼杉被大風折斷,擱淺在沙灘上。隨著潮起潮落,斷樹在海灘的沙子中來回挪動。在這過程中,沙子中被菊石廢棄的外殼連同其他生物一起被裹進樹脂中,最后被海底沉積物掩埋,形成琥珀。

恐龍的尾巴
2016年,在緬甸密支那的一個琥珀市場上,著名古生物學家邢立達從一個琥珀攤位上撿起一塊有內含物的琥珀仔細觀察起來。他努力辨別著琥珀中的古生物殘體。攤主說這是一塊植物殘體,但他認為是鳥羽,不過他摸不準。在同行的幫助下,這塊琥珀中的內含物被證實是一頭恐龍尾巴的一部分。
恐龍尾巴殘體中羽毛、肌肉、皮膚和骨骼清晰可見。化學分析顯示恐龍尾中含有亞鐵離子,說明尾巴在被樹脂包裹時還殘留有血跡。和被壓扁的巖石化石不同,琥珀能讓科學家看到9900萬年前恐龍羽毛的三維排列樣式。在此基礎上,人們就能知道這種恐龍的羽毛是用于飛行還是滑翔。

反鳥快速發育的羽毛
2017年,一塊包含了一只幾乎完整雛鳥的琥珀化石首次向外界公開。到目前為止,緬甸琥珀中發現的所有鳥類都屬于已經滅絕的反鳥亞綱,它們是今天所有鳥類(今鳥亞綱)的“親戚”。反鳥有類似現代鳥類的飛羽,這表示它們的飛行能力應該不輸現代鳥類。不過反鳥依然保留著原始的齒和翼爪,也沒有發展出現代鳥類的鳥喙。
雖然琥珀只能保留下內含物的表面印模,但透過這塊透明的琥珀,人們看到了雛鳥雙腿上的鱗片和爪,根根分開的羽毛甚至保留了一些色素。雛鳥的皮膚、肌肉和其他細節也一覽無余。這個雛鳥化石標本僅3.5厘米長,如果是現代鳥類,應該只長出絨毛,但反鳥雛鳥的羽毛已經完全發育。如果不是這只雛鳥不幸被樹脂困住形成琥珀,我們可能永遠不知道反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能長出完整羽毛。
在過去二十幾年里,幾乎所有的重要琥珀化石發現都來自緬甸,這也使得緬甸成為琥珀研究的熱點地區。截至2018年底,科學家從緬甸琥珀中總計發現并命名1192個動植物新種。但是近幾年來,科學家獲取緬甸琥珀的難度越來越大。在緬甸的琥珀產區克欽邦,武裝沖突時常發生,這讓前往克欽邦的科學家時刻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動植物內含物琥珀近年來價格一路上漲,高昂的琥珀售價讓許多科研機構無法承受。更讓人遺憾的是,許多內含物琥珀被私人收藏者高價收走,無法被用于科研用途。
雖然琥珀中的動植物內含物已經炭化,但其三維結構幾乎并未改變,因此科學家能通過掃描還原內含物的三維結構。而且,即便是最小的表面結構都能通過掃描技術重新呈現在屏幕上。這也是作為化石的琥珀最獨特的價值。琥珀研究熱還在持續,緬甸北部將為古生物學家提供更多“遠古的瞬間”。
(責任編輯王川)
可以從琥珀中提取遺傳物質嗎?
20世紀80年代,科學家從一塊形成于約4000萬年前的琥珀中包裹的蒼蠅體內,發現了線粒體、核糖體、細胞核等細胞器。為什么細胞器能夠經歷數千萬年而保存完好呢?科學家猜測:樹脂中的糖分子奪走了蒼蠅組織內的水,引發胞內脫水,因此細胞器才得以完好保存。既然細胞核中包含有遺傳物質,能不能從琥珀中提取到完整的DNA呢?
科學家已經從琥珀中包含的植物木質部中成功提取出了木質素和黑色素,但這些大分子都已經嚴重降解。相比前面兩種分子,DNA分子在生物死亡后的降解速度更快。科學家曾經對一塊全新世恐鳥骨骼中的DNA進行研究,發現DNA的半衰期只有521年。也就是說,每過521年,DNA中1/2的化學鍵會被破壞。因此,DNA在經歷了數百萬年后基本不可能被保存下來。
20世紀90年代初,曾經有多個研究宣稱成功從琥珀中提取出昆蟲DNA。這又是怎么回事?很可惜,這些研究沒有一個可以重復得出相同結果。目前科學界一致認為這幾次實驗提取到的DNA來自現代細菌和真菌的DNA,而不是來自琥珀中的昆蟲。細菌和真菌無處不在,它們有些以琥珀為食,有些依靠琥珀裂縫中的殘渣為食。這樣看來,通過琥珀復活已經滅絕的古生物幾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