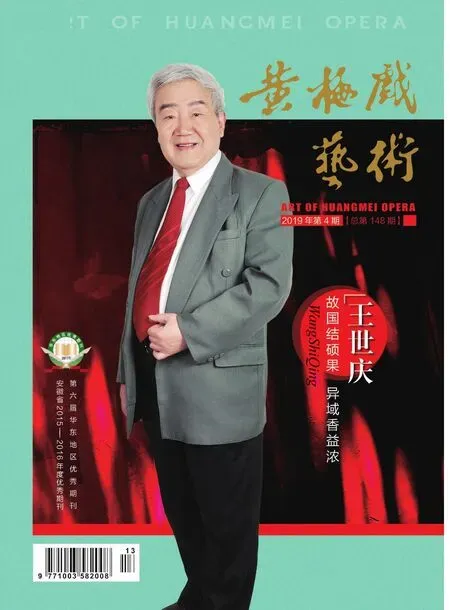黃梅戲《雷雨》中打擊樂的創編與運用
□ 解英瀚
話劇《雷雨》由曹禺創作,以1925年前后的中國社會為背景,描寫了一個帶有濃厚封建色彩的資產階級家庭的悲劇。劇中以兩個家庭、八個人物、三十年的恩怨為主線,不論是家庭秘密還是身世秘密,所有的矛盾都在雷雨之夜爆發。在敘述家庭矛盾糾葛、怒斥封建家庭腐朽頑固的同時,反映了更為深層的社會及時代問題。
黃梅戲《雷雨》,由話劇《雷雨》改編而成,但其打破了原來四幕話劇的格局,分為“雷雨兆”、“雷雨前”、“雷雨至”、“雷雨中”、“雷雨急”五場,主要場景基本集中在周家。這種更為明確的點題式布局,使觀眾在觀看演出時隨主題的切換而感受到劇情向高潮的擠壓式推進,增強了藝術的感染力。原著中,四鳳和周沖都是觸電身亡,帶有偶然性。改編后,四鳳是跳河自殺,周沖誤落井中,主動尋死更加凸顯了四鳳因雙重打擊而萬念俱灰,進一步增加了作品的悲劇色彩。黃梅戲《雷雨》中的周萍是一個劃時代的人物形象,“他”的出現打破了黃梅戲向來以旦角為中心的格局。雖然戲還是那部戲,故事還是那個故事,但編導們創造性地將劇中大少爺周萍擢升為一號人物,突出表現了這位陷于混亂倫理關系中的富家子弟的內心苦悶和靈魂掙扎,凸顯并放大了他懺悔原罪、向往光明的一面。
在這部戲中,打擊樂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是由時任安徽省黃梅戲劇院副院長、樂團指揮(兼司鼓)的江松陽老師創編的。本人作為樂團打擊樂的一員有幸參與到了其中,劇中開場打擊樂的核心合奏段落讓人至今難忘。
黃梅戲《雷雨》的作曲是著名黃梅戲作曲家、黃梅戲音樂泰斗、“戲曲音樂終身成就獎”第一人的時白林老師。時白林老師認為:藝術重在創新,切忌重復自己。“沒有創新的人,不會有出息。”時白林老師回憶說:“當初,我們把《天仙配》搬上銀幕時,采用了當時國際上非常流行的歌舞故事片形式,而非傳統的舞臺戲曲模式。不僅安徽人愛看,全國的觀眾乃至一些國際友人也都愛看。這就是創新帶來的成功。”
黃梅戲《雷雨》音樂創作時,時白林老師每創作完成一段曲譜,都會在第一時間和導演、演員、指揮以及主創團隊精心討論,對每一個細節進行研究,力求做到精益求精。其中開幕時男女主角周萍和四鳳首次亮相的音樂表現尤為重要,為此主創團隊通過無數次研究,最后決定用打擊樂來表現,并且用傳統的戲曲打擊樂為主進行合奏。
戲曲打擊樂也稱為武場。黃梅戲《雷雨》中的打擊樂也是延用京劇打擊樂的,以鼓板(檀板與單皮鼓)、大鑼(高音、中音、低音)、鐃鈸、小鑼(高音、低音)四件樂器為主,大多數情況下在指揮(鼓板)的指引下,一起擊打勻速有力或者由慢到快、由快到慢等節奏分明的聲音,通常是以大鑼為主(也分為高、中、低三種音色,音色不同所代表的人物也不同),鐃鈸、小鑼為輔,小鑼多為單獨演奏。
鼓板,單皮鼓和檀板兩種樂器的合稱,戲曲樂隊的指揮樂器。鼓板由鼓師一人掌握。板多用在鑼鼓和唱腔、曲牌的強拍(即板位)上;鼓多用在次強拍和弱拍(即眼位)上,或用在節拍自由的散板中。板通常只表示強拍,而鼓點則可以多樣變化,除按眼位擊奏外,在樂曲中還可加打花點以活躍節奏用;或為突出強調唱、念、身段動作的表現之用。鼓師為樂隊的指揮,他不僅要有相當的演奏水平,還須熟記演出劇目的情節內容和全劇的音樂布局。凡配合上下場、舞蹈、亮相等表演身段;或為突出語言的句逗、烘托語氣、語調和渲染情緒氣氛;或為開導各種板式唱腔、曲牌;或為場次轉接、戲劇氣氛轉換等,所用的鑼鼓,均靠鼓師開導得宜,才能獲得完美的演出效果。全出戲舞臺節奏的控制與調節、戲劇氣氛的渲染和藝術結構的統一完整,幾乎無一處不與鼓板的指揮有關。鼓師指揮樂隊,主要是靠鼓板打出的節奏音響并結合各種示意動作來進行。
鼓板可用紫檀、紅木、花梨木或其他硬木制作,木材必須干燥,不能有干裂或腐朽現象,對制作的材料有很高的要求。板無固定音高,發音短促,聲音堅實響亮,穿透力強。用紋理旋轉的木料制作的鼓板,發音更為脆亮。鼓板演奏時,左手執底板,使與前兩板相碰而發音。底板中間隆起,下部擊板部位形似人的上嘴唇,故名"板唇",是發音高低、寬窄、悶亮的關鍵。
板鼓是形體矮小的單面鼓,鼓身用色木、樺木、槐木、桑木、櫸木或柚木等硬質木料制作,由5塊較厚木板拼合而成,鼓身直徑25厘米。但絕大部分是木質板面,中間振動發音的鼓面僅有5~10厘米,鼓膛呈八字形,鼓邊高9.5厘米。鼓皮用牛皮,張緊于整個板面直到底邊為止。蒙皮的鼓膛部分又叫“鼓光”,是敲擊發音部位。板鼓發音的高低,取決于鼓膛的大小和蒙皮的松緊。為保持鼓皮的張力,所釘鼓釘較多,并在底部箍以鐵圈。分為418和416兩種型號。418比416的音調要高。京劇一般用418的單皮,昆曲用416的單皮,秦腔兩種都用......,黃梅戲用的是418,聲音明亮穿通力強,在板鼓上擊打鼓心和鼓邊發音高低不同。演奏時用點簽(用鼓簽點擊鼓面)和用滿簽(用鼓簽平擊鼓面)能發出不同的聲響。結合著力度的輕重、鼓點的疏密緩急,杰出的司鼓常能做出多樣的變化。
打法上戲曲打擊樂歸納為四種基本點子:
1.以“倉大”沖頭型為主及其變化形式,包括沖頭、導板頭、帽兒頭、五擊頭、四擊頭、住頭、歸位、九錘半等。
2.以“倉七臺七”長錘型為主及其變化形式,包括慢長錘 、快長錘、一錘鑼、鳳點頭等。
3.以“倉臺七臺”閃錘型為主及其變化形式,包括滾頭子、紐絲等。
4.以“倉臺臺七臺臺”抽頭型為主及其變化形式,包括抽頭、馬腿兒、鳳點頭、收頭、奪頭等。
其他鑼鼓點基本都由上述不同的節奏組合而成。
劇中開幕第一篇章主要演員亮相,打擊樂演奏者共七人:指揮兼司鼓(檀板、單皮鼓、廣東板、小堂鼓)、定音鼓(揚琴兼)、排鼓、大鑼(黑管兼)、小鑼、鐃鈸(兼吊镲)、大開镲(大提琴兼)。
大幕在低沉壓抑的音樂聲中緩緩拉開,燈光昏暗搖曳,音效發出鬼魅般“嗚嗚”的風聲,單皮鼓大八大、大八大、大八大八......輕輕擊打著,似乎不可預知的神秘和危險即將到來。魯貴身著灰色長衫,手提煤油燈,躡手躡腳走上場:“……三年前也像這個夜晚,我就撞見兩個鬼……”此時打擊樂器吊镲輕輕滾奏發出如水的聲音。魯貴繼續言道:“一個男鬼。”司鼓用鼓簽擊打單皮鼓發出“大、大”聲。魯貴用手指著上面(暗指繁漪):“一個女鬼”,司鼓用鼓簽擊打單皮鼓發出“大大大大……”,吊镲輕輕滾奏,映襯著似乎和諧卻又隱藏著些許不安的場景,隨后聲音漸漸消失。“......月亮長毛啦?明天準是個雷雨天!”魯貴背向觀眾,手提燈造型得意狀:“月亮長毛,不可小瞧。大雷大雨,地動山搖。”魯貴搖頭吟唱,拖音中大開镲在指揮的指引下猛烈撞擊發出洪亮的“嚓嚓”聲,仿佛天神雷鳴般刺耳劃破天際。
魯貴驚叫“誰!”身著白色長衫的周萍和綠白相間丫鬟打扮的四鳳慌亂中從舞臺右邊上場門走出,害怕地躲閃著……排鼓(高低音兩面)緊密錯疊發出“咚大大大、咚大大大……”,定音鼓(高低兩面五度音程)仿佛尋找審判的腳步聲催命的“咚、大、咚、大......”緊緊跟隨。偶然卻又必然的兩個相愛的人兒手觸碰到一起“鳳兒!”周萍歡喜雀躍想要抓住膽怯弱小的鳳兒的手。打擊樂停止。“鬼,兩個鬼!”魯貴蹲在椅背后大聲道。此時,一分鐘里,貫穿整個劇目的主題打擊樂合奏開始:重疊緊密的“咚大大大……”一浪浪排鼓聲好似鳳兒和周萍年輕的腳步,定音鼓“咚、大、咚、大……”像極了舊社會的黑暗和荒誕的愛,相互追逐著、探索著、尋覓著……吊镲聲響起,如水般起伏高低近遠,好像節拍有序又似雜亂無章,無所依托。兩個(本不該愛戀)相愛的人兒隨著如水的吊镲聲效手拉著手旋轉著,不舍依戀。此刻高潮迭起:打擊樂響起高亢有力的馬腿節奏“倉臺臺七臺臺、倉臺臺七臺臺……”周萍、四鳳在打擊樂聲中舞蹈,尋找希望、尋找溫暖。定音鼓、排鼓、大鑼、小鑼、鐃鈸在板鼓的指揮下一起奏出縝密嚴謹響亮有序的聲浪,“咚、咚”聲中打擊樂全部停止。
四鳳甜蜜地依偎在周萍懷里的經典亮相。魯貴似乎發現了什么,大聲叫道“這個家真有鬼吆!”打擊樂齊奏再次響起……周萍義無反顧地挽著鳳兒的手轉身急速地向牢門外的自由世界沖去。此時追逐的腳步聲、關門聲、打擊樂齊奏聲在指揮的指引下戛然而止。一切恢復平靜,好像都沒有發生。
黃梅戲《雷雨》先后斬獲了2007~2008年度國家舞臺藝術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劇目”及第九屆中國戲劇節“優秀劇目大獎”兩個國家級大獎。主演安徽省黃梅戲劇院院長蔣建國在劇中飾演男主角周萍。蔣建國曾獲得過中國戲劇“梅花獎”,也獲過中國藝術節“文華獎”。曹禺的《雷雨》,話劇、電影、電視劇等藝術樣式都有過非常好的呈現。蔣建國說: “其實這個題材也非常適合黃梅戲,因為黃梅戲比較擅長于人物的塑造,善于對人物情感的深刻挖掘和表現。”為了避免出現“話劇加唱”的尷尬,黃梅戲《雷雨》在造型、音樂、鑼鼓等方面都致力于黃梅戲劇種的個性凸顯。他舉例說:“比如造型方面,開場時,大幕拉開,幾組展示戲曲身段的人物組合出現在舞臺上,讓觀眾第一感覺:這就是戲曲,而不是其他。開場時打擊樂的運用也很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