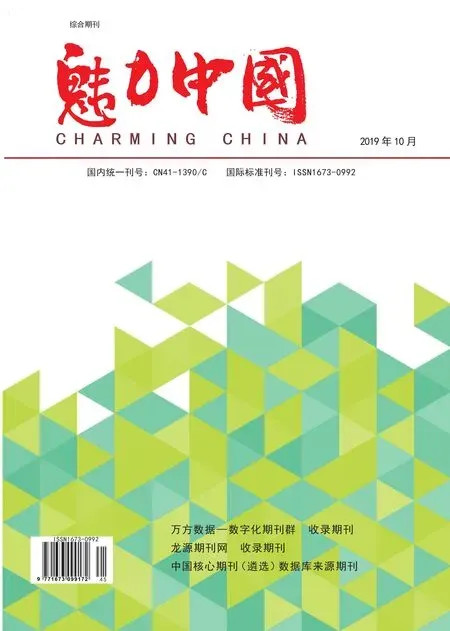試論蒙古族禮儀音樂的神圣性與世俗性互涉
郭安妮
(白城師范學院音樂學院,吉林 白城 136000)
引言:蒙古族自古以來傳承的民間生活習俗和約定俗成的程序方式就是所謂的民俗禮儀活動。這些習俗源自于生活和民眾,且服務對象也是民眾,在蒙古族民眾發生生活大事時,就會啟用禮儀活動。而禮儀音樂則是禮儀活動和音樂的結合體,故蒙古族禮儀音樂具有神圣性和世俗性互涉的特點。
一、蒙古族民俗禮儀音樂的文化遷移
蒙古族禮儀音樂的神圣性和世俗性互涉,主要是指社交禮儀與娛樂表演活動相結合的文化狀況。蒙古族擁有優秀的發展歷史,在漫長的發展歷史中,形成了大量的優秀民俗文化,民俗儀式活動就是其中的代表。國外民族學家認為,一些民族的文化和習俗,其遷移能力不會受到人類想象力的干擾,對祖先生活管理進行延續,是一部分民族遷移文化和習俗的主要方式,這一點在蒙古族上得到了體現,比如:自古以來,暖房與宴歌的伴生關系就沒有發生過變化,音樂世俗性的特點在其中發揮了十分關鍵的作用。不管是在形式還是內容上,與蒙古族家庭的社會交際需要相適應,成為了蒙古族禮儀音樂表現形態變動的主要依據。而蒙古族文化傳承與社會關系結構遷移的載體為世俗化的民間社會交際體例,其在蒙古族民俗文化傳統和發展這一過程中,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1]。故蒙古族群文化遷移的社交表征,成為了蒙古族民俗禮儀活音樂神圣性和世俗性互涉的基礎。
二、蒙古族鄉俗禮儀音樂的經驗雜糅
鄉俗禮儀音樂是蒙古族禮儀音樂的重要組成部分,以那達慕草原盛會為例,在盛會上蒙古族人民會載歌載舞,繼而形成一個音樂景觀,我們可以將其視為一個位于特殊區域的視聽系統,且這個視聽系統具有雙重的屬性,不僅存在著物質音樂景觀,也存在著非物質音樂景觀。這里所說的物質音樂是器樂的表現,因為器樂在演奏過程中需要使用樂器,基于這一特點,被稱為物質音樂景觀。一般情況下,器樂演奏的目的在于歌頌民族精神,以及對未來生活的期盼等,屬于一種代表蒙古族風俗習慣和文化特征的代表。非物質音樂景觀則較為虛幻,是指蒙古族草原時空開放性和民眾通過禮儀音樂促成的一種心靈體悟。前者蘊藏著傳遞民族景觀的歷史想象,而后者則是通過禮儀音樂使族群歸屬感和民族凝聚力被喚醒。故我們可以將蒙古族鄉俗禮儀音樂的音聲景觀看作是特定區域內蒙古族經驗的雜糅,是以世俗化動態音樂景觀為基礎,對人、音、地進行傳遞的一種關系。具體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音樂基于地域文化,形成詞曲和風格;(2)音樂會成為地域文化強化民族生存現實語境的重要條件[2]。而人是促使二者有機結合的唯一因素。人不僅能夠在日常生活中,對民族地域環境進行體驗,同時還能創造地域性經驗,上文中提到那達慕草原盛會中所體現的地域性經驗,亦可被稱為音樂經驗,象征著世俗文化,這種世俗文化可以通過音樂的形式,使民族交流感知力量得到提升,最終成為締結民族情感紐帶的神圣力量。
三、蒙古族宗俗禮儀音樂的精神隱喻
蒙古族宗俗禮儀音樂的精神隱喻,主要是指音樂變體能夠成為音樂精神符號。以蒙古族敖包祭祀為例,蒙族敖包祭祀屬于蒙古族宗俗禮儀的重要活動形式,在這一活動中,蒙古族民眾所唱的歌曲,其音樂變體不僅是為神明服務,同時,還會為人服務。首先,從為神明服務的角度上看,蒙古族敖包祭祀活動十分莊嚴和肅穆,信徒們會嚴格遵循宗教的禮儀流程,在跪拜之后聆聽僧侶和喇嘛的誦經或唱詞,在這一個過程中的音樂表現,其目的已經不再是彰顯音樂,而是為了對宗教觀進行傳遞。比如:僧侶在誦經唱詞過程中,經常會通過拉長音調的方式,表現與神靈的精神溝通,神明成為了此時音樂主體的角色對象,在這種宗俗禮儀下,音樂成為了一種人神溝通的媒介,而不再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媒介。其次,從為人服務的角度上看,與神明進行溝通和交流是敖包祭祀的音聲表現,但其最根本的目的為希望得到神明的庇護,說的通俗一點就是“請神上身”。故在祭祀過程中所使用的神杖就有了兩種不同的含義,一種是敲擊鼓面的樂器,另一種為宗教權力的媒介,在宗教祭祀來到高潮時,信眾們會伴隨著神杖的揮動而歡呼,并通過搖鈴的方式予以響應,在他們看來神明已經在神杖上附身,并會庇護每一個信眾。從本質上看,這不僅是一個簡單的祭祀活動,更是人們內心對力量的渴望和追求。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曾經說過,宗教儀式從表面上看是人崇拜神的活動,但在實際上卻是人們通過崇拜神對自己進行崇拜。敖包祭祀宗俗音樂屬于一個藝術載體,促進了神圣與世俗的有效結合。
結論:綜上所述,本文從民俗、鄉俗和宗俗三個角度,對蒙古族禮儀音樂的神圣性與世俗性互涉進行了分析,闡述了其中蘊藏的文化內涵,以加深人們對蒙古族習俗文化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