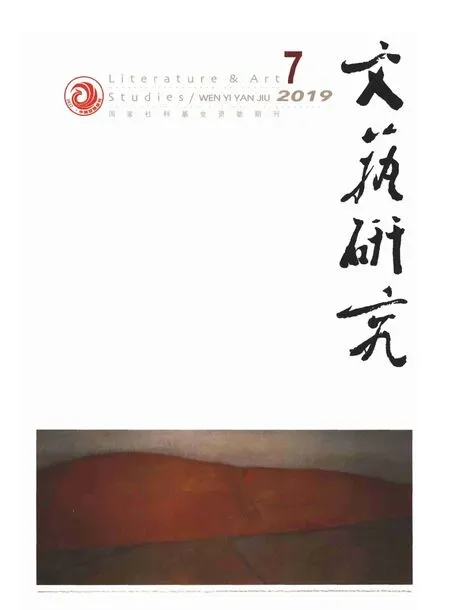塞尚、電影與梅洛—龐蒂的知覺問題
舒志鋒
一、“知覺還原”的“考古發掘”
喬納森·克拉里在《知覺的懸置:注意力、景觀與現代文化》中認為,很多關于塞尚繪畫有影響的揭示,與20世紀早期的現象學有關聯,二者都被視作對“社會與文化的附添”與“日常的習見”的懸置與還原,以及由此對一種本真與始源狀態的回歸。胡塞爾被認為是這場現象學運動的奠基性人物,而梅洛—龐蒂則直接將現象學理論運用于對塞尚繪畫的闡釋,克拉里認為:“根據梅洛—龐蒂的著名揭示,塞尚尋求‘一種穿透強加在人們身上的人性秩序、直接抵達事物之根的視覺’,想要確立一種直面世界的立場,這個世界先于心靈與肉體、思想與視覺的區分,他寫道:‘塞尚恰好回到了那種原初的經驗,這些觀念正是來自這種經驗,并與這種經驗不可分離。’在這種觀點看來,塞尚的作品提供了進入事物本身的純化之路,與胡塞爾本人在其對‘觀看本質’的探索中援用的模式相平行。”①
無論是胡塞爾還是梅洛—龐蒂,所使用的都是現象學的方法。但對于以還原與懸置的方法所獲取的知覺的原初統一,克拉里進行了某種福柯意義上的考古學質疑。在這樣一種“考古發掘”中,胡塞爾對于本質直觀的追求被視作為了重建“注意力”作出的努力,其背景是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第一個十年“奇觀”的出現導致的“注意力”潰散。克拉里認為,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隨著生活不斷地被一種動力的、娛樂化的感性所包圍與侵蝕,日常生活被知覺與經驗為碎片化的、游離的與波動的。注意力不斷地被分化、調節、融合與出路,其“恒常性”與“專注性”不斷受到挑戰與弱化,以至于被描述為“易受疲勞、分心和外部掌控影響的”②。胡塞爾不是唯一對此種注意力的潰散以及隨之而來的知覺碎片化做出反應的人。如何在種種相對性中把握住某種恒定與穩固,并給出相應的理論類型以及測量標準,亦成為馮特的視域變體模型、視速儀以及反射弧理論得以產生的根本動力。因此,正如福柯在《詞與物——人文科學的考古學》中將現代知識型的產生置入生物學、語言學、經濟學所交織而成的復雜視域,克拉里亦將“純粹知覺”的可能性問題與哲學、科學心理學、早期電影、藝術理論以及神經學等諸多學科纏繞在一起,以此凸顯知覺與注意力得以被“爭議”(contested)與提出的背景。
不過,與馮特、邁布里奇、亥姆霍茨等人在技術與生理層面對知覺與注意力的標準化探索不同,胡塞爾通過現象學的方法在意識領域進行了此種嘗試。在克拉里的理解中,所謂的“現象學還原”,即排除分散與干擾因素的意識集中行為,而本質性的直觀即懸置任何“非形式性”的東西,以求得純粹直觀中的絕對給予。注意力與知覺被引導進一個前個體的、非個人的先驗絕對領域。在此領域中,注意力屏蔽了來自任何經驗、任何時空的干擾。克拉里認為,胡塞爾的創造性在于將注意力與意向性進行關聯:注意力的提純、反推,被理解為不斷追蹤原初的意向性行為;而意向性本身則成為那束使得事物得以澄明與清晰的“探照之光”“專注之光”,并且其本身帶有一種絕對性的結構與形式。克拉里認為,正是在此語境中,胡塞爾以現象學的方法完成了對注意力的重建:“在現代化的動態分解過程中,他卻提出了一種整體性的注意力技術,可以將統一性、清晰性和連貫性施加在最分散、含混和運動的心理內容之上。為了拯救主體的生活世界的本真性,胡塞爾發動了想要確定其普遍結構的無望的探索。”③經過克拉里的解釋,胡塞爾所有的現象學努力都在“注意力邏輯”之下被重置了。
在克拉里的注意力與知覺的考古學視域中,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亦可被重釋為對知覺原初性的追尋,以及對知覺統一性在現代社會喪失的回應。只不過,與胡塞爾相比,梅洛—龐蒂的現象學還原與懸置更加具有兼容性質,凸顯了現代哲學中的實存維度。這是因為他的知覺理論與心理學、生理學以及神經科學結合得更加緊密。早在《行為的結構》這部著作中,梅洛—龐蒂就通過對反射理論以及高級行為的心理學探討,引申出行為的意向性結構問題,這就是《知覺現象學》中“身體圖式”的前身④。而在《知覺現象學》中,知覺的相對性現象,比如“繆勒—萊爾”錯覺曲線⑤、韋特海默的運動視覺實驗⑥,成為了梅洛—龐蒂探討“知覺的現象場”以及“知覺空間”問題的切入口。而對于克拉里在《知覺的懸置:注意力、景觀與現代文化》中援引的英國神經學家多茲所論述的視覺與其他感官之間的混雜現象,梅洛—龐蒂在其知覺還原理論中亦曾反復探討。多茲在1886年的論文《論視覺的某些主要影響》中論述了視覺與“觸覺、聽覺、肌肉的感覺”相互混雜的狀況⑦。他的觀察無疑在感官的經驗層面否認了“純粹知覺”的可能性,并且證明感官之間并不是相互獨立,而是相互影響的。但正是在知覺經驗的“含混”中,梅洛—龐蒂看到了它們在原初層面上的共生性質:它們同樣源出于一個知覺背景,所有的分化都是在理智層面的后續操作。知覺在經驗層面的“含混”反而成為其在原初層面統一的“癥候”。
梅洛—龐蒂以現象學的方法來重建知覺統一性,最為經典的例證是其關于施耐德病例的分析。他在這里所處理的不是因外部因素的干擾造成的知覺分散,而是由器官損傷或病變造成的知覺綜合功能的缺失。與出現幻肢現象的病人相反,由于喪失了知覺的統一功能,施耐德病例中的病人雖然四肢健全,卻無法完整地使用自身的身體圖式。梅洛—龐蒂通過此病例,從反面揭示了知覺是如何重建自己的統一性以及發揮綜合功能的⑧。在這樣一個層面來揭示知覺的完整與統一,是梅洛—龐蒂的首創。無論是在《行為的結構》中,還是在《知覺現象學》中,面對外部環境刺激以及身體感官自身所帶來的知覺波動、離心現象,梅洛—龐蒂并未訴諸傳統行為理論中的原子主義或傳統哲學中的經驗主義、理智主義予以解釋,而是通過知覺的還原,在知覺的原初層面來對這些混雜現象進行收納,以此將知覺平衡到一個相對綜合與統一的狀態。這些知覺的“熵性”現象,其實可以視作梅洛—龐蒂進行知覺還原操作的外部契機。
二、塞尚繪畫中的“知覺分裂”
梅洛—龐蒂在《塞尚的懷疑》中提出,塞尚繪畫的知覺還原性質最為突出地體現在其構圖上。他認為塞尚繪畫的構圖不是由線條產生,而是從顏色中“浮現”出來的:“通過顏色,透視滅點、輪廓線、直線和曲線被安置為力線,空間框架在顫動中得以構造。”⑨塞尚本人也認為:“構圖隨著上色而進行;顏色越和諧,則構圖越精確……隨著顏色的豐富,形式便獲得完滿。”⑩廢除明確的輪廓線條而代之以明亮的著色,是當時印象派比較普遍的做法,這使得繪畫更具視覺沖擊性且更富于視覺表達。后來馬蒂斯可謂將源自印象派的色彩表達手法推到一個新的階段。但梅洛—龐蒂在此技法中卻看到了視覺與觸覺溝通的可能性。梅洛—龐蒂認為,塞尚之所以能以顏色來代替線條的功能,關鍵在于其在知覺層面進行的操作所引發的是知覺的原初場域。而在這個層面,“觸與看的區分是未知的”。在原初知覺層面,顏色與線條本身是互滲的,因此,從此層面進行的顏色表達并非是對線條的生硬暗示,相反,線條本身從顏色中“浮現”出來。在塞尚的繪畫中,構圖的成功不是著眼于構圖本身,而是來自于對顏色的知覺還原操作。在梅洛—龐蒂看來,知覺還原不但是我們進入塞尚繪畫的鑰匙,同時也是塞尚繪畫創作的關鍵性技法?。
克拉里明顯不贊同梅洛—龐蒂此種現象學化的構圖分析。他認為,面對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第一個十年注意力分散、知覺碎片化的現代境況,塞尚并未在繪畫實踐中進行知覺還原的操作,而是給出了另一種方案:“塞尚拋棄了數百年來視域不斷被疆界化的各種代碼,不是為了揭示一種自然的‘野蠻人的’視覺,而是為了在知覺空間內新建構起來的離心力得以自由嬉戲。”?這等于完全推翻了梅洛—龐蒂在“知覺還原”邏輯支配下關于塞尚繪畫的解釋,而將其導向“知覺的流動與分裂”。塞尚不再是《塞尚的懷疑》中那個擁有“純真之眼”或“嬰孩之眼”的知覺懸置者,相反,他“直面”與“安頓”了知覺本身的不穩定問題。克拉里認為,后期的塞尚不再堅持“純粹知覺”這一現代性神話,是因為他認識到:專心地觀看一事物,并不能導向對該物在場的更為充分與完全的把握,毋寧說,它導向知覺的分解與可見形式的崩潰?。在這一事實性的知覺分解與潰散中,“純粹”與“混雜”、“還原”與“分化”的區別不再有效,甚至成為徒勞。知覺本身被置于一個萬花筒中,其自身的運作就是不斷地旋轉這個萬花筒,像機器一樣不斷生產出知覺。“知覺的白板”只是現代哲學中的一個先驗假設。塞尚無非是遭遇了這樣一個事實:持續的知覺經驗永遠不可能產生傳統意義上“純粹”的東西,知覺的最深刻的形式不可還原地是混合與復合的。在克拉里的闡釋中,塞尚成為一個固執地想要記錄這種知覺的流動與分裂的敏感者。因此,塞尚的困惑不再來自于要在每一筆觸中表達那個豐富的“始源世界”的重負,而是來自于展現“充滿力量和強度的流動的無根基空間”(a liquid groundlessspace filled with forcesand intensities)的艱難?。塞尚以印象派的手法來追求古典繪畫的堅固與形體,在梅洛—龐蒂那里被闡釋為原初知覺得以綻開的技法,而克拉里則將其理解為“知覺的凝聚與分解的動態交互關系”?。
對此,克拉里以塞尚的晚期畫作《松石圖》(1900)為例進行分析。塞尚在《松石圖》中的構圖是多元與不連貫的,因而造成了一種特殊的知覺混雜效果。克拉里從三個方面對此予以揭示。首先,《松石圖》中存在著一個帶狀結構區域,從作品左側中部一直延伸到右下角,沿對角線分布。這個區域再現了一堆混雜的巖石與礫石,并且呈現出飽滿的紫色與肉色。克拉里認為:“在上下光線與樹葉的嬉戲中,它像一塊‘空地’一樣突出來,構成了一條富有立體感與堅實感的紐帶,其中的巖石似乎富有重量感的三維特性。”?在對這部分的刻畫中,塞尚仍然沿用了古典的立體造型手法,通過透視縮短技法營造出浮雕般的錯覺,因此與畫面底部具有震顫效果的巖石肌理及上方二維性的松葉幕與天空形成了某種對照。橫斷的帶狀結構具有明顯的質感清晰性,而其他部分則是朦朧的效果,兩個不同的視覺系統被松散地結合在一起。
其次,《松石圖》中這一帶狀結構中的巖石本身也體現了在知覺綜合問題上的“搏斗”與“猶豫”,即一方面給人以不可改變的實體解體的感覺,另一方面卻又體現了對知覺的“漂移”與“熵性”的抵抗。這是因為,這組巖石在浮雕與堅實錯覺中隱藏著“混雜”與“分裂”的傾向。克拉里認為,我們越是仔細研究左側的那組巖石,就越能發現其被分裂為三組與樹枝緊挨著的“獨立而分離的形狀”?。其中被樹葉所覆蓋的那部分巖石,其空間特性是高度含混的,因為只有部分巖石被呈現為三維的;而右下方的石塊則顯得十分古怪,塞尚在這里并沒有使用正交直線來營造體積感,而是通過輪廓(contour)的飽滿(voluptuousness)來進行暗示。但其輪廓線并非是連續的,左側的輪廓線非常抽象,是連續變化的數學性線條;而右側的輪廓線則是一種羽毛狀的、不精確的曲線。因此,三組巖石中,其實有兩組是十分含混的,介于三維體積與二維平面之間,在空間感上呈現為一種“混雜”與“互滲”的狀態。兩種空間的相互植入,最終生成了一種知覺的流動感。
最后,《松石圖》最上部分的構圖亦表明了注意力的分裂。在左側的第一棵樹與第二棵樹之間的空曠處,存在著一條垂直的白線,這條白線本應為第四棵樹的樹身,因為據此我們恰好可以將畫面的上部分垂直劃分為五等分。但是此處的空間顯然沒有被清晰地給出,而是呈現為一種模糊的未分化狀態,這一“垂直的白線”成為了“猶豫不定的直立著的標記”?。克拉里認為,這種“兩可”的辨認與解讀,恰恰表明這片區域正在開始一種新的“分化”“個別化”以及“變形”的過程,它們代表的是塞尚后期繪畫的關鍵性技法。塞尚在此處的不連貫性構圖,同樣表明了知覺在掌控方面的松弛。
三、從“圖形—底面”到“運動—影像”
從技法角度而言,塞尚繪畫的知覺分裂通過以下方式得以呈現,即“廢除視覺場域中的距離性視點”(abandoned a distanced point of view within a visual field)?,“強烈的去定向化”(intensive disorientation)?,“倒轉傳統視覺聚焦模式”以及“筆觸的自行變動”(strokes that autonomously mutate)?。這些技法被單獨或交互地使用在上面所分析的三部分構圖中。以此方式,塞尚超越了圖形/底面、中心/外圍以及近景/遠景等傳統構圖中的二元對立。在這些二元關系中,圖形/底面無疑是最為基本的,正是這一場域的存在,使得中心焦點與外圍背景的視覺模式成為可能,并且使得近景/遠景得以鋪展開來。“底面”這一基本背景的預設,亦是空間的“定向化”以及“距離性視點”得以投射的基本知覺條件。
梅洛—龐蒂的知覺綜合得以展開的基本場域亦是此“圖形—底面”空間。但與古典透視體系不同的是,梅洛—龐蒂的知覺空間并非是在意識層面進行的抽象建構,而是以身體為中心點的投射。知覺空間在身體與物的意向性交流中綻出。梅洛—龐蒂認為,我的身體之所以能夠以“特別的形象”(privileged figures)出現在一個“無差別的背景”中,只是因為我的身體被其表達任務所吸引,在身體向物體的趨近過程中,二者形成相互纏繞的意向性關系?。“圖形—底面”關系成為身體朝向世界并在此場域中表達自身的方式。身體總是以此“圖形—底面”關系作為自身得以定位的潛在空間與內在坐標,它始終以某種潛在的視域(horizon)為先導。
這就意味著,韓妝的市場份額被這些新興進口品所瓜分已是必然。不過,在上述專業人士看來,新的市場格局也給了韓妝新的機會,“特別是有創新能力的中小品牌。”
即使在面對運動這一現象之時,梅洛—龐蒂仍然以“圖形—底面”模式予以闡釋。他認為,只有在我們知覺范圍內的物體的移動才能稱之為“運動”,我們看到某物移動,這一行為本身即是將我們的知覺加諸物體之上的“把握”(hold)、“遭遇”(encounter)、“含括”(encompass)行為。我們對運動物體的觀看并不是追蹤與被追蹤的客觀關系,某種程度上而言,運動與視看二者是共生的;與其說眼睛是運動物體的“幾何投影形式”(form of ageometrical projection),還不如說它是身體對物體進行“情境化定向”的具體方式?。因此,雖然運動具有流動性,但是梅洛—龐蒂仍然通過視覺的定向,將之收納到身體的知覺背景與界域之中。
就此而言,電影雖然是一種具有運動性質的圖像,是一種全新的藝術形式,但它并不構成對“圖形—底面”模式的挑戰,因為仍然可以將電影還原到原初的知覺背景。梅洛—龐蒂認為:“如果我們現在將電影看成一種知覺對象,就可以將前面所講的有關一般知覺的一切統統用于對電影的知覺。”?從知覺現象學角度而言,電影不是圖形的集合,不是圖形簡單拼合在一起,其背后存在著一個整體性知覺結構。這種知覺結構以時間的形式表現出來。電影中每一個畫面的順序安排將會直接影響其意義的呈現。當三個場景以不同的順序出現時,會產生完全不同的組合效果。這是因為,不同的順序形成了不一樣的基礎性知覺結構。并且,一幅畫面的時長也會影響到知覺的結構,畫面時長本身也構成了一種知覺表達的“手法”。所以在電影剪輯時,快進的時長往往用于表現愉悅的笑容;冷漠的面孔一般在正常的時長中呈現;緩慢的時長對應的往往是痛苦的表情。時長、順序這些電影的“節奏”實際上是有著相當的知覺基礎的,這種知覺基礎像語法一樣嚴苛地安排著電影的“語言”。電影通過節奏、角度、距離、場景等鏡頭語言呈現出一種極為復雜的形式。在梅洛—龐蒂看來,在基礎知覺層面,這些復雜的語言本身是“未分的”與“統一的”?。
但在克拉里看來,電影恰恰構成了對知覺還原的挑戰。電影突破了“圖形—底面”與“點—水平”限制,是空間的無等級展開。克拉里所舉的一個例證是電影《火車大劫案》中出現的場景:“這列真正在運動的貨車(我們自己的位置與其等同)成了‘背景’,在這個背景的襯托下,大地在飛馳,由于其呼嘯而過而不可辨識。在再接著的下一個場面,我們卻突然站在了仍然在運行中的列車車頂上,不過這一次列車以與銀幕相垂直的路線,直接沖向畫面。這里,列車與列車在其中飛馳的風景都成了交織在一起的、可逆的、互為條件的飛馳線,一方的后退與另一方的前行不可分開。”?知覺系統在不斷顛倒與切換的場景中幾乎不可能完成身體的定向。塞尚的繪畫同樣分享了電影的分裂、流動、震顫的特質。克拉里認為,塞尚19世紀90年代的作品與早期電影處于同一個時代,用福柯化的術語來說,二者處于同一個知識型中。在克拉里看來,塞尚與電影的關聯,比起塞尚與立體主義的關聯,更加切中塞尚繪畫的本質。在克拉里的“知覺考古”中,塞尚開辟了20世紀繪畫現代化進程的早期舞臺,處于“17與18世紀知識的古典秩序的視覺的連根拔起”與“20世紀的機器視覺王朝的徹底重置”之間?。
因此,無論是早期電影,還是塞尚的繪畫,都預示著一種全新知覺模式的來臨?。知覺的生產不再依賴于現象學的框架,而是趨向于“運動—影像”這一全新的模式。這種知覺模式不再預設“圖形—底面”的存在,而是在流動與分裂的境況中考察知覺。更為重要的是,這一知覺模式彌合了運動與圖像之間的對立。德勒茲在《電影I:運動—影像》中認為,盡管胡塞爾提出了“所有的意識都是關于某物的意識”,梅洛—龐蒂的知覺場域亦向外部與物性開放,但是現象學并未能縫合意識與物質、圖像與運動之間的割裂?。無論是胡塞爾還是梅洛—龐蒂,均將影像默認為意識的專屬,而運動則被分配給物體。這種對立與割裂無法闡釋圖像與運動的跨界現象,無法應對電影這一“運動—影像”裝置?。在電影中,我們無法用“作用與反作用”的關系模式來界定“影像”與“運動”,在這里“影像”即等于“運動”,因為“電影并不給予我們一個運動添加其上的圖像,它直接給予我們運動—影像”?。通過“剪輯”(montage)這一特有的方式,電影擺脫了“自然知覺條件”(the condition of natural perception)的限制,從而實現圖像與運動之間的融合。
“運動—影像”裝置產生著完全不同于“圖形—底面”模式支配下的知覺體驗。隨著這一裝置的啟動,所有的形象都處于形成或者消解的過程中:“這是一個普遍變化的世界,普遍的波動,普遍的漣漪。這里既沒有軸線,也沒有中心,沒有左,沒有右,沒有高,沒有低……”?這是一個向外部敞開、無限變化的光影世界。德勒茲進一步認為,電影是一種“光之圖像”(the image of light),而且這種光線完全來自其自身內部,無需借助于主體的“意識之光”就能開顯自身?。這意味著,電影不是被其他事物照亮的,而是被自身照亮的。這里完全不存在現象學所言的意識(圖像)與物質(運動)之間的意向性問題,所有的意識(圖像)都是物質(運動)。在此意義上,現象學仍然處于“前—電影”階段,仍然依附于人類知覺的“自然條件”:“現象學所設立的規范是‘自然知覺’以及它的條件,現在,這些條件成為實存性質的坐標,定義了世界之中知覺主體的‘錨固’所在,向世界的敞開可以被表達為著名的‘所有的意識都是關于某物的意識’。”?德勒茲在此所言的“現象學”,具體而言,是指梅洛—龐蒂的知覺現象學。正是梅洛—龐蒂而非胡塞爾著重論述了“自然知覺”的條件問題,使“知覺主體”置于實存化的語境中,并且將“知覺主體”明確為“身體”。處于知覺場域中的身體并非物理意義上的身體,而是現象學意義上的身體。“現象身體”與世界之間形成了某種對等交流系統,隨著實存狀況的變動而不斷調整自身。通過此一身體圖式,身體實現了在世界這片汪洋大海中的“錨固”。
德勒茲認為,電影是對身體“錨固”以及世界背景的同時拒絕。在電影中,所有的形象都以“等距瞬時”(equidistance instant)存在于“運動—影像”之中,這本身就意味著對“特別的形象”的取消?。電影無意于構造一個完整的形象以供視覺進行凝視,知覺現象學中被指派的那個位置——作為扭結而存在的身體——在電影中無法發揮其“投射”功能而喪失其中心性地位。同時,作為平面性的呈現,電影身后并無一個“深度”性質的世界,更無必要通過懸置與還原而回歸一個“始源世界”。電影將世界變成了它自己的圖像,而不是為圖像置入一個世界背景。在此意義上,電影突破了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的身體“投射”范式,展現了知覺的“機器論”形態?。這是一種更高的、更無所限制的、具備了生產性質的知覺形態。
以此“電影—眼”(cine-eye)來看塞尚,所展現的同樣不是自然條件之下的視覺純真。塞尚并非在尋求一種剝離所有習見的純粹目光,而僅僅在追求一種“永恒變動”(universal variation)、“永恒互動”(universal interaction)的視覺世界?。換言之,塞尚其實是以“電影—眼”來審視這個世界,以一種類似于機器的方式來記錄眼前流動的世界。“先于人”并不是退回到作為背景與視域的世界,而是成為“流動圖像”生產的機器。德勒茲將塞尚所創造的這樣一個世界看作是巴洛克式的。巴洛克繪畫并不遵循一套規范與統一的視覺體系,而是不同的平面、不同的深度彼此植入,不同的繪畫單元彼此相互作用而造成某種駁雜與繁復的感覺。這種相互植入與相互作用,形成了繪畫的分化與流動的效果?。深受塞尚影響的立體主義繪畫,在德勒茲看來,并非格林伯格所言的對平面與抽象的趨近,而是對流動與分裂的無限接近:“所有的表面都被分裂、削砍、解體、破碎,好像圖像被置于昆蟲的千面之眼中。”?
結語:另類梅洛—龐蒂
克拉里的“知覺分裂”以及德勒茲的“運動—影像”,都將梅洛—龐蒂視為現象學化解讀知覺問題的代表。梅洛—龐蒂似乎與現象學以及藝術的現象學闡釋形成某種綁定。但隨著梅洛—龐蒂思想的演進,其思想呈現出更為復雜的面貌,遠非“現象學”這個標簽能夠涵蓋。在《可見的與不可見的》中,梅洛—龐蒂甚至對以身體為“中心”的知覺現象學進行了某種質疑:“《知覺現象學》中所提出的問題是無解的,因為我是從‘意識’—‘客體’的區分開始的。”?在其思想的晚期,梅洛—龐蒂通過“肉”(flesh)這一基質性概念,展現的不是一個作為背景而存在的“沉默世界”,而是一個交織(chiasm)與分化(divergence/écart)的“垂直世界”(vertical world)?。一個不同于《知覺現象學》時期的“另類梅洛—龐蒂”呈現在我們面前?。
①②③???????? 喬納森·克拉里:《知覺的懸置:注意力、景觀與現代文化》,沈語冰、賀玉高譯,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2017年版,第223頁,第225頁,第226頁,第235頁,第228頁,第263頁,第261頁,第263頁,第269頁,第275頁,第284頁。
④ 莫里斯·梅洛—龐蒂:《行為的結構》,楊大春、張堯均譯,商務印書館2010年版,第18頁。
⑤⑥⑧?? Merleau-Ponty,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trans.Donald A.Lands,New York:Routledge,2014,p.6,p.259,pp.105-148,p.103,pp.290-292.
⑦ W.J.Dodds,“On Some Central Affectionsof Vision”,Brain,8(1886):25.
⑨⑩? 莫里斯·梅洛—龐蒂:《意義與無意義》,張穎譯,商務印書館2018年版,第12頁,第12頁,第70頁。
? 舒志鋒:《從“現象的身體”到“可逆的肉”:論梅洛—龐蒂美學理論的前后轉換》,載《文藝理論研究》2017年第6期。
? Jonathan Crary,Suspensions of Perception:Attention,Spectacle,and Modern Cluture,Cambridge:MIT Press,2001,p.359.本文中對于克拉里此書的引用分別引自中譯本和英文版兩個版本。凡引自英文版處,均因作者認為中譯本對這些語句的翻譯未能忠實體現作者原意,故進行了重譯。
???Jonathan Crary,Suspensionsof Perception:Attention,Spectacle,and Modern Cluture,Cambridge:MIT Press,2001,p.333,p.340,p.340.
? 不難看出,梅洛—龐蒂對于電影的分析仍然延續了其在對塞尚繪畫的分析中所使用的知覺還原模式。
? 克拉里并非第一次提出19世紀晚期的視覺體系裂變問題。在《觀察者的技術:論十九世紀的視覺與現代性》中,克拉里通過福柯式的考古發掘,將立體透視鏡這一視覺裝置視作全新感知模式的代表。暗箱代表的是一個封閉、孤立、原子化的視覺模式,身體因素與外部因素都被排除在外。暗箱是一種無身體、無器官的觀看。立體透視鏡將身體納入自身的觀看體系中,意味著其是一個開放的視覺體系。立體透視鏡使克拉里發現了一種完全與暗箱模式不同的視看方法,19世紀晚期以來的視覺實踐,即是對暗箱模式的某種消解(喬納森·克拉里:《觀察者的技術:論十九世紀的視覺與現代性》,蔡佩君譯,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191—204頁)。但無論是立體透視鏡還是早期電影,其所指向的都是流動與分裂的知覺模式,這與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以及《塞尚的懷疑》中所呈現的知覺還原模式相異。某種程度上,無論是立體透鏡還是早期電影,其所展現的都是與現象學知覺模式完全不同的知覺類型。
???????? Gilles Deleuze,Cinema 1:The Movement-Image,trans.Hugh Tomlinson and Barbara Habberjam,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7,p.56,p.2,p.58,p.61,p.57,p.3,p.81,p.23.
?德勒茲認為,雖然胡塞爾始終沒有將電影納入自己哲學的思考范圍,但是胡塞爾經典的現象學公式——所有的意識都是關于某物的意識——卻與“運動—影像”問題有著深刻的關聯。梅洛—龐蒂在其《知覺現象學》中提及了電影的問題,但在德勒茲看來,梅洛—龐蒂僅僅將電影視作一個“模棱兩可的盟友”(ambiguous ally)(Gilles Deleuze,Cinema 1:The Movement-Image,p.57)。現象學與電影之間似乎存在難以跨域的差異。
? 德勒茲給出了他關于電影的定義,即“與任意瞬間相聯系而再現出的運動”(Gilles Deleuze,Cinema 1:The Movement-Image,p.6)。
? Heinrich W?lfflin,Principleof Art History,trans.M.D.Hottinger,New York:Dover Publication,1950,pp.13-16.
?? Maurice Merleau-Ponty,The Visibleand the Invisible,trans.Alphosno Lingis,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8,p.200,p.201.
? “另一個梅洛—龐蒂”的說法仿自道恩·威爾遜的《另類胡塞爾:先驗現象學的視野》。道恩·威爾遜認為:“當胡塞爾在其理論中通過現象學的‘靜態分析’與現象學的‘動態分析’做出成系統的區分,并用以拓展他的方法的時候,他已經走出了‘笛卡爾式的表達’的局限性。‘靜態的現象學’與‘動態現象學’的區分,為我們提供了關于胡塞爾的‘另外’一個方法論來源。”(道恩·威爾遜:《另類胡塞爾:先驗現象學的視野》,靳希平譯,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2頁)值得注意的是,梅洛—龐蒂本身是這個“另類胡塞爾”的發現者,在1959—1960年法蘭西學院演講稿中,他就已經提出了“另一個胡塞爾”的觀點(Maurice Merleau-Ponty,Husserl at the Limitsof Phenomenology,trans.Leonard Lawlor,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2002,p.15)。
?伊莎貝爾·托馬—福吉爾:《“空間作為存在之數”——梅洛—龐蒂和投射空間》,龐培培譯,杜小真編《理解梅洛—龐蒂:梅洛—龐蒂在當代》,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190—192頁。
? 伊莎貝爾·托馬—福吉爾認為,“侵越”所表示的是我與世界的接觸關系,而非界限關系。甚至可以說,“侵越”透露出對界限與規則的僭越與打破,而這恰恰是梅洛—龐蒂在后期所提出的“交織”“可逆”得以可能的前提。
?? Jessica Wiskus,The Rhythm of Thought:Art,Literature,and Music after Merleau-Pont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3,p.23,p.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