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張病危通知單
凌晨三點,我趴在電腦前假裝研究著那些沒有情節只有骨與肉的片子。
實際上我正注視著搶救室拐角處那兩位忙碌著的大爺,他們正有條不紊地整理著那些我們身為中國人都將穿上的衣物。
急診搶救室門外突然傳過來一陣騷動,有人在罵街,還伴隨著砸東西的聲音。
于保護自己的習慣,我并沒有立刻沖出去,而是扒著門縫偷偷張望。
原來是一位大媽同收費員發生了爭吵,說著一些有辱斯文、不堪入耳的話。
是什么原因讓一位大媽同收費員在深夜發生爭吵?
仔細聽來卻又不是什么大事,只不過是因為醫保系統在按預定計劃升級。
在醫保系統停機維護期間,醫保患者只能先行自費掛號、付費看病。一旦系統恢復正常工作,可以憑借繳費發票換回醫保。
雖然收費處的同事已經做了解釋,但這位大媽依舊不理解。
直到圍觀的病人、值班的保安,大家紛紛上前勸說、解釋,大媽才不甘地離開。
這只是日常工作中非常常見的場景,并沒有什么特別之處。
實際上,生活中有很多人都帶著厚重的戾氣,他們很少去傾聽、去理解。
在醫院里,尤其是在急診,這樣原本毫無必要的紛爭更會時常發生。
大媽離開后,另外一個患者的家屬對站在診室外觀察事態發展的我說了一句話,這句話讓我至今難以忘記。
這位不到六十歲的男性家屬嘆了口氣說:“這種事也值得吵嗎?像我們這樣到了拿錢也換不回命的時候,自然也就不吵了。我最害怕的不是醫生讓我花錢,而是醫生不讓我花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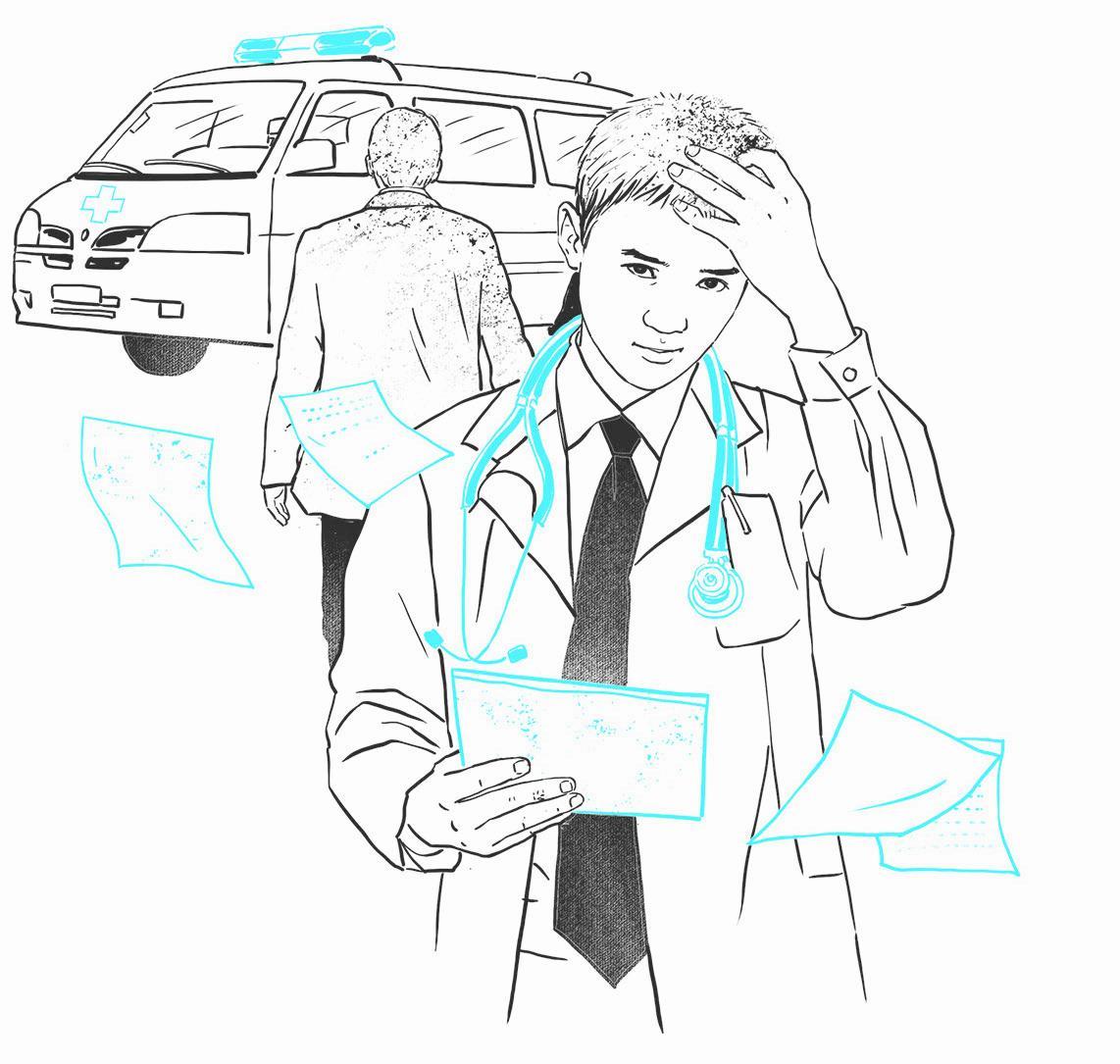
他的話像一記重拳一般猝不及防地打在了我的胸間,讓我突然感到一股軟綿綿的蒼白無力。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聽見這樣飽含人生智慧和無奈的話了,它像是夜幕之上的一顆明燈,讓深夜有了一絲光芒。
“在生死面前,這些都不是事。”也正是這聲從我身后發出來的感慨,才讓我對他有了不一樣的看法。
因為此時此刻的搶救室內正發生同這個男人有著莫大關聯的事情,他卻非常不合時宜地出現在了我的身后。
一切都要從兩天前開始說起,那天我是急診搶救室中班,120救護車送進來一位嘔血的56歲女性患者。
患者被送進搶救室的時候甚至有些讓我震驚,因為她的口角、衣服上全都是散發著腥臭味的血跡。
“她是肝癌晚期,吐血快一個小時了!”患者的丈夫是一位身形消瘦、戴著眼鏡的男人。
此刻的患者已經處于休克狀態,并且很快陷入了昏迷。
毋庸置疑,對于一位肝癌晚期并發消化道出血的患者來說,死神已經握住了她的一只手。
對癥處理后,患者的血壓暫時得到了穩定。
患者的丈夫對我說:“就這樣吧,不要再折騰了。”
初聽這句話時,剛經歷了這場大搶救的我有些不解,甚至有些憤怒:什么叫作不要折騰了呢?難道我和趙大膽的勞動都是瞎折騰嗎?如果不愿搶救治療又何必送進醫院呢?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要帶回家嗎?”我停下了手中的筆,確認他的意見。
我坐在板凳上仰頭看著站在我面前的患者丈夫,望著這雙我在急診搶救室里無數次碰撞過的眼神。
他停頓了幾秒,回答我:“我不帶回家,我的意思是不要去ICU,也不用住院了,氣管插管、心肺復蘇都不要了,輸點液體就可以了,我可以簽字,一切后果我自己承擔。”
我見識過很多不愿意配合搶救的患者和家屬,也聽過各種各樣的理由或者意見,但這樣有著充分準備和擔當的要求并不多見。
“你知道如果不積極搶救的話,她隨時隨地都會沒有命嗎?”我必須要確認家屬知道疾病發展的方向和可能。
患者的丈夫看樣子是一個有一定知識水平的人,也是一個溫文爾雅的男人:“就算積極搶救,也已經不可能治好了,對她來說,多活一分鐘都是痛苦。”
無須過多交流,如果不是經歷了生活的重大磨難,又怎么可能對疾病和死亡有著如此冷靜和清晰的認識?
事實上,在患者被確診肝癌的14個月之中,曾經發生過五次消化道大出血。
每一次都是一場生死劫難,每一次都曾讓這對夫妻充滿絕望。
“這是我收到的第十七張病危通知單。”他拿起筆簽下了病危通知單。
雖然他對患者的病情有著充分的了解和心理準備,雖然他曾多次經歷過這種場面,雖然我已經做了反復的溝通,但他拿著簽字筆的右手依然猶如灌鉛一般沉重而緩慢。
后來患者的病情不可避免地急劇惡化,生命體征在急診室的黑暗之中被慢慢吞噬。
宣布臨床死亡后,家屬并沒有哭鬧,甚至就像患者還沒有離去一般。
我將呈現一條直線的心電圖遞到患者丈夫的面前,他平靜地點頭認可,并無言語。
此刻提供喪葬一條龍服務的兩位大爺正在為他的妻子穿著那些花花綠綠的衣服,他卻還在搶救室外看著熱鬧。
我知道患者長時間的病情一定讓他非常疲憊,我知道患者多次經歷的劫難也一定讓他看透了生死。
所以,我能夠理解他做出放棄積極搶救治療的決定。
所以,我能夠理解他面對妻子死亡時的鎮定自若。
但是,我卻不能理解當妻子正在被穿著壽衣時,他卻也站在了圍觀熱鬧的人群中的舉動。
“穿好衣服準備走了嗎?”
圍觀的人已經散去,只剩下站在搶救室門口的我和他。
他單薄的身影在急診搶救室凌晨的寒風之中顯得格外單薄:“還沒有,我是想謝謝你。”
這又是對我內心的一記重拳,我沒有想到此刻他追著從搶救室里出來竟然是為了道謝。
這些都只是我的本職工作,我甚至沒能夠為患者爭取回一秒鐘的生命,甚至還在腹誹著他,又怎么配謝謝這兩個字呢?
一時間我不知道該如何回答,只好勉強回答道:“早一點離開就是早一點結束痛苦吧。”
那晚憤怒之中的大媽,離開后再也沒有回來。
那夜我的穿著花花綠綠壽衣的患者,同樣被死神永遠地帶走了。
簡單交流后,家屬和提供喪葬服務的大爺們匆忙消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夜幕之中。
但是有兩句話,卻讓我至今難以忘記:
他說:“這是我收到的第十七張病危通知單。”
他說:“在生死面前,這些都不是事。”
我想我的患者一定是去了另一個世界,那個世界里的月光一定不會遺漏她。
我想被我腹誹的丈夫一定開始了新的生活,生活在一個沒有病危通知單的人世間。
(田龍華摘自微信公眾號“最后一支多巴胺”圖/豆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