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就是一種歸來(lái)
阿來(lá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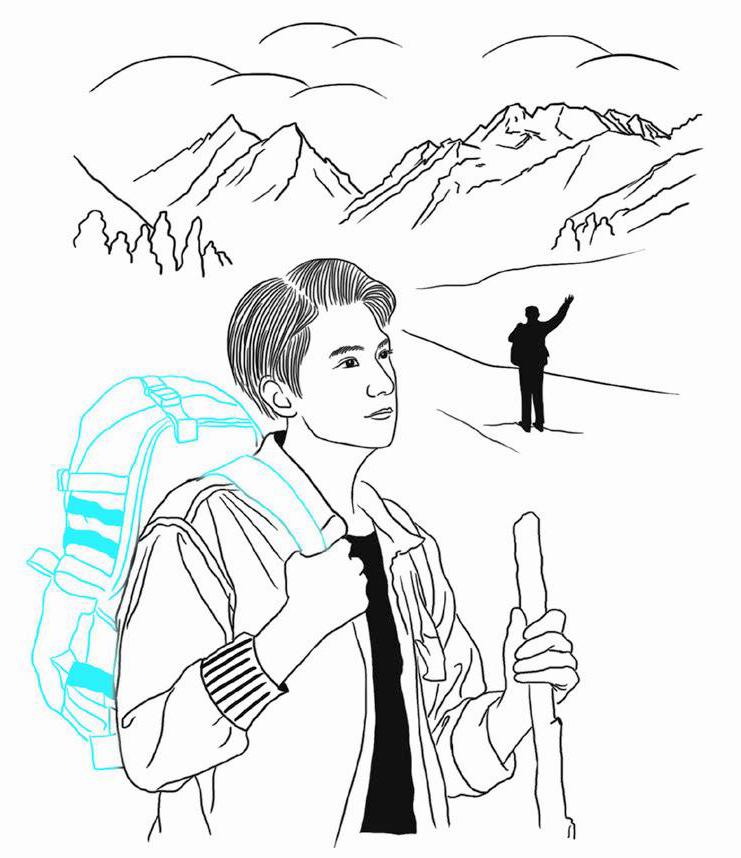
我為拍攝一部電視片,在深秋十月去攀登過(guò)一次號(hào)稱蜀山皇后的四姑娘山。這座海拔六千多米的高山,就聳立在距四川盆地不過(guò)百余公里直線距離的邛崍山脈中央。我們前去的時(shí)候,已經(jīng)是水冷草枯的時(shí)節(jié)。雪線正一天天下降到河谷,探險(xiǎn)的游客已斷了蹤跡。只在山下的小鎮(zhèn)日隆的旅館墻上留下了“四姑娘山花之旅”一類的浪漫詞句。
上山的第四天,我們的雙腳已經(jīng)站在了所有森林植被生存線以上的地方。巨大巖石的陰影里都是經(jīng)年不化的冰雪。往上,是陡峭的冰川和藍(lán)天,回望,是一株株金黃的落葉松,純凈的明亮。此行,我們不是刻意登頂,只是盡量攀到高一點(diǎn)的地方。當(dāng)天晚上,我們退回去一些,宿在那些美麗的落葉松樹下。那天晚上下了一場(chǎng)大雪。早上醒來(lái),雪遮蔽了一切。樹,巖石,甚至草甸上狹長(zhǎng)的高山海子。
我又一次看到被雪覆蓋的山脈一列列走向遼遠(yuǎn),一直走到與天際模糊交接的地方。這時(shí),太陽(yáng)出來(lái)了。
不是先看到的太陽(yáng)。而是遽然而起的鳥類的清脆歡快的鳴叫一下就打破了那仿佛亙古如此的寧?kù)o。然后,眼前猛地一亮,太陽(yáng)在跳出山脊的遮擋后,陡然放出了萬(wàn)道金光。起先,是感覺全世界的寂靜都匯聚到這個(gè)雪后的早晨了。現(xiàn)在,又覺得這個(gè)水晶世界匯聚了全世界的光芒與歡唱。
“太陽(yáng)攀響群山的音階。”
我試圖用詩(shī)概括當(dāng)時(shí)的感受時(shí),用了上面這樣一個(gè)句子作為開頭。從此,我就把這一片從成都平原開始一級(jí)級(jí)走向青藏高原頂端的一列列山脈看成大地的階梯。
從純粹地理的眼光看,這是把低海拔的小橋流水最終抬升為世界最高處的曠野長(zhǎng)風(fēng)。
而地理從來(lái)與文化相關(guān),復(fù)雜多變的地理往往預(yù)示著別樣的生存方式、別樣的人生所構(gòu)成的多姿多態(tài)的文化。
不一樣的地理與文化對(duì)于個(gè)人來(lái)說(shuō),又往往意味著一種新的精神啟示與引領(lǐng)。
我出生在這片構(gòu)成大地階梯的群山中間,并在那里生活、成長(zhǎng),直到三十六歲時(shí),方才離開。之所以選擇這個(gè)時(shí)候離開,無(wú)非是兩個(gè)原因。首先,對(duì)于一個(gè)時(shí)刻都試圖擴(kuò)展自己眼界的人來(lái)說(shuō),這個(gè)群山環(huán)抱的地方時(shí)時(shí)會(huì)顯出一種不太寬廣的固守。但更為重要的是,我相信,只有在這個(gè)時(shí)候,這片大地所賦予我的一切最重要的地方,不會(huì)因?yàn)閷?lái)紛紜多變的生活而有所改變。
有時(shí)候,離開是一種更本質(zhì)意義上的切進(jìn)與歸來(lái)。
我的歸來(lái)方式肯定不是發(fā)了財(cái)回去捐助一座寺廟或一間學(xué)校,我的方式就是用我的書,其中我要告訴的是我的獨(dú)立的思考與判斷。我的情感就蘊(yùn)藏在全部的敘述中間。我的情感就在這每一個(gè)章節(jié)里不斷離開,又不斷歸來(lái)。
作為一個(gè)漫游者,從成都平原上升到青藏高原,在感覺到地理階梯抬升的同時(shí),也會(huì)感覺到某種精神境界的提升。但是,當(dāng)你進(jìn)入那些深深陷落在河谷中的村落,那些種植小麥、玉米、青稞、蘋果與梨的村莊,走進(jìn)那些山間分屬于藏傳佛教不同教派的或大或小的廟宇,又會(huì)感覺到歷史,感覺到時(shí)代前進(jìn)之時(shí),某一處曾有時(shí)間的陷落。
問(wèn)題的關(guān)鍵是,我能同時(shí)寫出這種上升與陷落嗎?
當(dāng)我成人之后,我常常四處漫游。有一首獻(xiàn)給自己的詩(shī)就叫作《三十周歲時(shí)漫游若爾蓋大草原》。
記得其中有這樣的句子:
我們嘴唇是泥,
牙齒是石頭,
舌頭是水,
我們尚未口吐蓮花。
蒼天啊,何時(shí)賜我最精美的語(yǔ)言?
(圖/張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