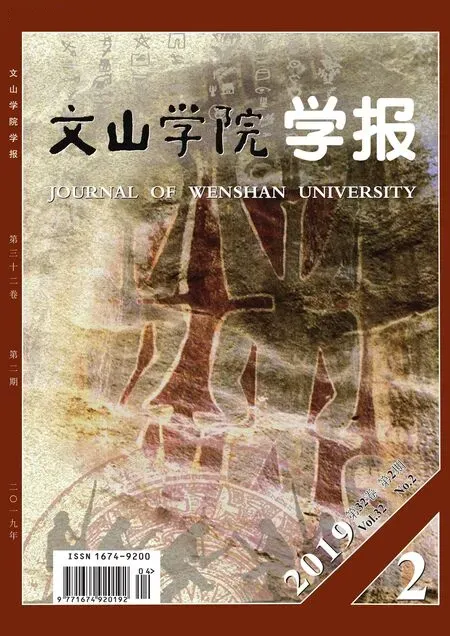云南邊境地區網絡信息安全的新情況與新問題
戴子寒
(云南師范大學 歷史與行政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互聯網的問世及飛速發展,改變了人類生產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將整個世界日益聯結為超越時空限制、即時聯絡的地球村落。中國自接入互聯網20年以來,已發展為一個互聯網大國,整個社會對互聯網的依賴日益加深。據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2018年發布的《第42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8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為8.02億,互聯網普及率達57.7%;我國手機網民的規模7.88億,網民中使用手機上網人群的占比達98.3%,且超過五成的網民明確表示自己難以離開網絡,廣大網民的信息獲取、交流溝通、商品交易、生活娛樂越來越依賴互聯網所提供的多樣化服務[1]。而對于國家層面,我國當前處于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深刻轉型時期,國家現代化程度不斷加深,無論是能源安全、軍事設施安全、電力維護、金融保障,還是教育普及、商業運作、文化傳播、社會運轉等,都離不開日益復雜的網絡系統的支持[2]。但是,互聯網所具有的跨域性、實時性、去權威化和去中心化的特質,在給當今社會帶來多種便捷的同時,也不容忽視與其相伴而生的相關安全問題。
習近平指出,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就沒有經濟社會穩定運行,廣大人民群眾利益也難以得到保障[3]。在當今時代,各類對安全帶來威脅的活動與形式也呈現出與網絡相結合的特征。特別對于我國多民族邊疆地區,其本身就處于非傳統安全問題多發地,而民族宗教、跨境犯罪、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等因素與網絡安全問題的結合,將使該地區本身就復雜的安全形勢變得更為棘手。
一、網絡信息傳播在云南邊境的特點
(一)信息傳播工具的變化
對于云南邊疆民族地區的一些群眾,其以往接觸境外信息的方式主要是通過安裝小鍋衛星接收器收看境外電視,或通過報刊、光盤、收音機等渠道獲取信息。如一些傣族群眾,時常收看泰國電視節目。但近年來隨著國家對這方面監管的加強,小鍋等私人衛星收發器被陸續拆除和取締,但還有部分邊境民眾私自安裝私人衛星發射器來獲取境外信息。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及智能手機的普及,智能手機已成為邊民或跨境民族通信的主要手段,手機的功能也大大超越了傳統的通信范疇,而大面積的網絡覆蓋,也為境外意識形態乃至不良信息的流入編織了一張巨大的信息通道。目前云南邊境跨境民族或邊民通過電腦或手機瀏覽的境外網站主要是泰國、緬甸、越南、新加坡等國的網站,特別是中文網站。而長期接收來自境外的電視及網絡信息,特別是一些境外網站對中國的報道,難免會影響信息接收者對國內外及黨和政府的觀點和看法,對他們的生活方式及思想觀念方面也有一定影響。當地有相當一部分民眾時常通過手機等移動網絡設備收到來自境外的視頻、音頻、文字、圖片等政治或宗教方面的宣傳信息,其內容主要包括對我國黨和政府及其領導人的誹謗或抹黑、蠱惑民族仇恨、煽動顛覆社會主義政權、國家分裂及法輪功等邪教歪理邪說[4]。同時,智能手機也成為邊境地區各種犯罪活動得以實施的有力工具。這表明,對新的信息載體的使用使得信息在云南邊疆地區的跨國傳播愈加普遍,當地民眾特別是跨境民族群眾已成為境外敵對勢力通過網絡進行滲透的首要目標,信息的跨國傳播也使該地面臨更大的犯罪隱患。的確,便捷的信息網絡使得各類信息以網絡為介質或通道迅速蔓延,為多種非傳統安全風險的傳播及擴散提供了條件。多發于云南邊疆地區的非傳統安全問題將借助網絡的力量不斷升級,對邊疆乃至全國安全帶來威脅。
(二)網絡宗教滲透的隱蔽性
國內外敵對勢力往往利用文化的民族性與異質性等特征,對我國邊境多民族地區進行宗教方面的思想文化滲透。非傳統安全中的宗教滲透問題屬于云南邊疆跨境民族地區的典型安全性問題,其誘因不斷增加,之間的關系也愈加復雜,呈現出國內與國際因素、歷史與宗教因素、社會經濟發展與科技因素相交織的狀態。從歷史文化上看,云南作為我國宗教信仰種類最多的省份,其邊境地區少數民族多數跨境而居,且秉持相同的宗教信仰,他們由于極易對本民族和宗教產生認同而滋生過激行為;從地緣因素看,與緬甸、越南等國接壤的云南邊境地區,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往往成為敵對組織的首要目標;從社會經濟因素看,當地欠發達的經濟發展水品導致當地民眾生活條件艱苦,且跨境往來便利,這為不法組織以經濟利益引誘當地信眾和人民從事不法活動及宗教滲透活動提供可趁之機;從文化生活角度看,云南邊境大多屬于農村,農村文化生活相對匱乏,導致文化真空地帶的形成,這也為某些邪教和異端邪說的滲透和擴散帶來方便。在前互聯網時代,境外宗教傳播及滲透的傳統方式主要是境外宗教組織或個人以非法入境的方式,攜帶大批與宗教有關的印刷小冊子或福音書入境分發,或以舉行少數民族慶典活動為幌子進行傳教與滲透活動。而科技水平的進步與普及更是改變了傳統的宗教傳播與滲透方式。
習近平在2016年4月22-23日召開的全國宗教會議上指出:“要高度重視互聯網宗教問題,在互聯網上大力宣傳黨的宗教理論和方針政策,傳播正面聲音。”[5]網絡的普及使網絡空間中的宗教活動與相關信息的傳播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打破了傳統的以人為主的傳教方式,使得宗教活動與信息的傳播更加隱蔽。這表現為:首先,網絡宗教使得傳統的宗教活動場所發生改變。目前網絡上建立的以宗教為主題的門戶網站和論壇的數量飛速上升,傳統的宗教交流方式和場所在網絡空間里演變為網上寺廟、網上教團等虛擬形式。各宗教團體,包括合法登記和未登記的以及非法團體、宗教界人士通過網絡建立網上宗教場所、網上教團,倡導網上修行,同時通過版主與網民互動,建立了宗教網絡傳播模式新形態[6]。目前云南邊境地區一些較為年輕的佛教信眾在平常的宗教交流和學習活動中,在去當地或周邊的教堂、寺廟采用面對面、文對文、集體修行等方式的基礎上,還利用互聯網工具進行學習與交流;其次,網絡宗教的信息傳播渠道更為多元。手機日益強大的上網功能使使用者通過網絡接觸宗教信息更加容易,不管是信教人士還是普通民眾都能頻繁接收到載有宗教信息的群發短信。目前以基督教為主題的移動手機APP就有萬余個,以伊斯蘭教為主題關鍵詞的APP有兩千余個[7]。這些與宗教相關的手機APP可提供宗教資料的在線閱讀與下載,其信息傳播顯然是不易控制的。而網絡時代產生的“手機依賴”現象也使得使用者頻繁接觸網絡宗教信息。
網絡宗教的虛擬性以及邊境民眾對手機等移動網絡設備的使用,為網上傳教和滲透提供了快捷而又難以控制的渠道。在舉行傳統的宗教活動時,其信眾和成員是共同在場的,而互聯網宗教活動場所存在于虛擬空間,導致互聯網宗教活動可以跨越時空、情景分離,即無論是白天還是黑夜都可以進行網絡宗教活動,并將相關信息傳遞到任何一個角落。這使得地域和時間的限制并不影響虛擬宗教組織的固定性和宗教信息傳播的全天候性,給境外非法宗教活動及有害網絡宗教信息的傳播提供了便利平臺。如一些境外第三國勢力通過互聯網,利用跨境民族這一便利條件,在境外以微信、QQ、Twitter或短信等方式傳播含有宗教滲透信息的文字、視頻等,或對云南邊境地區的宗教滲透活動進行遠程操控,而操縱的源頭可能來自全球的任一角落,具有很大的隱蔽性,對此則難以追根溯源。據有關部門統計,利用基督教對云南進行滲透的外部組織有上百個。這些組織以極為隱蔽的傳播方式,利用網絡對我國邊境地區人民進行宣傳誘導、混淆視聽。他們一方面通過相關網絡平臺發布詆毀我國傳統文化、攻擊我國少數民族政策等言論,宣揚“民族文化滅絕論”等有害觀點;另一方面通過網絡宗教對該區域少數民族信眾進行隱性滲透,以達到挑撥民族關系、煽動國家分裂之目的。如“國際基督教關注”是一個由美國各教會參與的人權組織所建立的網站,它致力于所謂的“援助和支持那些為了實現自己的信仰而遭到迫害的基督徒”,該網站的內容含有大量的對所謂中國“宗教迫害情況”的報道,以“簡訊”“深度報告”和“新聞發布”為主要形式。
二、網絡跨國犯罪的超時空性
信息化時代到來加速了本身就在進行中的全球化進程,犯罪的跨國化趨勢隨之發生重大變化。跨國犯罪的犯罪類型、犯罪結構、組織形式、行為方式都呈現出全新的態勢[8]。關于刑法對于跨國犯罪的定義,其中一個重要特征便是犯罪人或犯罪行為是否流動于兩個以上的國家。而網絡使得危害行為超越了時間和地域的限制,即網絡信息可以在短時間內到達任何有網絡存在的地方,一項犯罪行為的執行可能只需幾毫秒的時間,理論上犯罪人只需一臺聯網的終端機,就擁有了利用網絡到世界其它國家實施犯罪行為的能力[9]。且犯罪分子及其所使用的網絡服務器或終端設備可以不在同一個國家或地區。這就為犯罪分子實施跨地域的有組織犯罪提供了便利,也給法律的定義及監管帶來一定的困難。
我國中緬邊境地區本身屬于跨國犯罪多發地,隨著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浪潮,以及邊境的日益開放,境內外國際交流日益頻繁。與此同時,云南邊境傳統跨國犯罪的復雜性與網絡信息化技術特色的交媾,使得犯罪分子可以跨越時間、空間實施犯罪活動,導致該區域的跨國犯罪不僅數量上增長,且犯罪方式愈加多樣,組織形式也更為隱蔽。在我國云南邊境地區比較典型的網絡跨國犯罪主要包括:
(一)跨國電信網絡詐騙
借助發達的現代通訊網絡及便捷的電子支付手段,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問題愈加突出。網絡跨國詐騙具有超時空性,其在空間上大跨度、大范圍作案已成為常態,這主要表現在:首先,網絡改變了傳統詐騙活動中詐騙者和被害人需要同時面對面的條件。而在網絡詐騙中二者就算相隔千里,犯罪分子也可在任何時間段對受害人實施詐騙,即非接觸性;其次,網絡詐騙幾乎無需物理空間和物理道具,即不需店面之類的場地或行騙所需的各類物品,這些均被網絡設備及其收發的視頻、圖片等數據所取代。尤其是近幾年,隨著智能手機引領網絡終端的最新潮流,其詐騙犯罪的實施方式也不斷創新,如手機虛假APP、微信紅包、微信木馬等。還有的受害人僅僅在智能手機上點開了某陌生網站的鏈接,或是無意中掃描了詐騙分子制作的二維碼,手機便被犯罪分子遠程控制或入侵,其受法律所保護的利益隨之受到侵害。
在我國,由于各地公安加強了對國內電信網絡詐騙的跨地區合作打擊,不法分子實施這類詐騙的藏匿窩點及服務器便逐漸轉向境外,東南亞的多國也成為他們的藏身地點之一,其隱蔽性更高。2018年9月,通過中緬警方開展的跨國聯合打擊行動,逮捕了兩個藏匿于緬甸撣邦的跨境網絡詐騙團伙,他們通過微信等網絡社交平臺,利用網絡彩票和網絡游戲進行跨境詐騙。還有長期盤踞在老撾邊境的網絡詐騙團伙,他們租賃或購置當地酒店作為詐騙犯罪窩點,并仿冒境外一些知名博彩網頁設置虛假賭博網站,同時通過短信、電子郵件、微信等進行宣傳,以誘使國內賭博愛好者投注賭博,通過后臺人為控制開獎結果,誘騙參與者不斷追加賭注等方式騙取錢財[10]。在這些網絡詐騙事件中,犯罪分子和受害者在物理空間上均相距遙遠,甚至不在一國境內,且任何時候都可通過虛擬網絡相聯系。其時空跨度大,增大了行為的隱蔽性,降低了犯罪成本,同時加大了監管與查處的難度。
(二)跨國網絡販毒
毒品犯罪問題是一項典型的非傳統安全議題,是當今世界范圍各國和地區面臨的共同“瘟疫”,也是云南邊境地區的突出問題之一。英國學者巴里·布贊指出,毒品犯罪會對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及環境五個領域都帶來危害和沖擊,其中,毒品生產國、消費國及過境國都不能免于沖擊[11]。我國云南邊境地區,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及錯綜復雜的地形,使之成為境外毒品犯罪的前沿陣地。據相關官方資料顯示,2016年至2017年生長季,緬北、老北地區地區罌粟種植面積達60萬畝,可產鴉片550多噸,緬北地區在保持較大規模海洛因和冰毒片劑產量的同時,開始大量制販氯胺酮、病毒晶體等合成毒品[12]。由于該地區各國政府對毒品深惡痛疾,并陸續對境外運輸通道進行管制,嚴格管控毒品攜帶及運輸,使得毒品傳播圈日益縮小。
網絡的普及應用則為該地區的販毒分子提供了一種新型交易模式,開辟了廣闊空間。販毒手段科技化、智能化明顯升級,使得問題變得更加棘手。網絡販毒即利用互聯網進行的毒品交易行為。不法分子利用網絡空間中信息傳播跨越時間、空間的特點進行隱蔽性交易,以躲避監管。云南邊境地區的網絡跨國販毒活動的特點主要包括:一是網絡販毒交易場所的超時空性。在網絡化時代,跨國販毒分子可以不使用任何交通工具,通過建立涉毒網站、利用網絡聊天室或即時通信工具便與境內聯系,網絡在這里變成了販毒者和有購買意愿者之間信息溝通的“橋梁”,使他們通過網絡便可獲知毒品的銷售渠道及供貨源。二是網絡販毒過程中溝通行為的隱蔽性。雖然公安機關多次組織開展針對網絡涉毒信息的專項打擊行動,但是,隨著新技術、新思維的不斷應用,以“找戰友”“找路子”“出肉”“出牙簽”等關鍵詞信息代替了傳統的“販毒”“吸毒”“交易”等關鍵詞信息,在我國特別是云南邊境地區范圍內不斷快速傳播。還有的販毒分子甚至不用輸出言語,只需動動手指,就可從網上通過電子代碼互換,達成交易意向[13]。三是網絡販毒交易方式的超時空性。在網絡販毒活動中,犯罪分子通過支付寶、手機號、Q幣、比特幣等在線支付方式便可進行線上匯款,完成跨國、跨地域性毒品犯罪交易活動。還有一些毒品制造者借助網絡上的信息,獲取冰毒等毒品的制作方法,在當地制作并通過現代物流寄遞業,將毒品藏在茶葉、發膠或音響里寄出,并采用匿名、假名、虛假地址等障眼法,以逃避打擊和監管,降低被追查的風險。
對于網絡跨國販毒,其信息傳播的跨時空性使其活動更為隱蔽,增大了監管難度,無形中也增加了調查取證的難度。如一個16歲少年在百度貼吧看到內容為“尋找人員幫助運輸毒品,一趟活三天,一趟一萬塊”的內容,便留下了聯系方式,隨后就有人聯系他,讓其體內藏毒從緬甸帶回境內。還有的販毒團伙利用網絡進行有組織的販毒活動,他們往往分工明確、組織嚴密,團伙內部有專人提供制毒資金,制毒活動的實施也由專人組織;犯罪嫌疑人通過微信、QQ群等通訊工具在線交流和學習制毒技術并招募制毒技術人員,甚至越境奔赴緬甸學習制毒技術。該類組織正是利用網絡,將從原料提供、輸送、制毒、販毒到吸毒這一全鏈條進行跨時空的隱蔽性串聯。
(三)網絡恐怖主義
近幾年來,隨著國際聯合反恐的進行,極端分子在高壓下加速外溢,南亞、東南亞地區逐漸成為他們的滲透破壞目標。我國西南邊境地區鄰國近年來頻繁發生的恐怖事件對我國境內的暴恐分子所起的示范效應刺激也不容忽視。西南邊境亦是我國藏族的主要聚居地,是境外反動集團的重點滲透破壞地區之一。在對新疆“三股勢力”等犯罪團體的常年打壓下,其活動呈外溢趨勢。他們利用西南邊境的人文環境及區位的特殊性潛入潛出,大大增大了該區域的不穩定。與此同時,境外“東突”組織欲加速融入國際恐怖網絡,以中亞和東南亞為轉運通道[14]。云南由于自身民族宗教、地緣以及國際國內等因素,其邊境地區近年來已成為新疆籍人員非法出境的主要通道之一,偷渡案件呈現出“境外指揮、疆內組織、內地集結中轉、邊境偷渡出境”的特點,且云南境內有大量穆斯林聚集地區,存在“三股勢力”落腳繁衍的隱患。此外,“三股勢力”在老撾、越南、馬來西亞、泰國等云南周邊東南亞國家建立了聯絡站和接應店,其數量也在不斷增加,為實施恐怖活動作準備。
網絡恐怖主義即恐怖分子通過網絡渠道所進行的危害國家安全、破壞社會秩序、造成經濟損失并產生一定的恐怖效果的網絡犯罪。它具備一般網絡犯罪的特征,又有區別于網絡犯罪的動機、行為等犯罪要素,是網絡犯罪的惡性發展和極端形式,帶有明確的政治性和極大的恐怖效果[15]。雖然網絡不是恐怖事件的根本誘因,卻是傳播極端思想和組織恐怖主義活動的重要手段。我國政府也很早就意識到了網絡恐怖主義活動的嚴重危害,加強了對境內電信市場、互聯網及非法出版物的管理。但超越國界的互聯網卻增加了監管和處置的難度,帶來巨大挑戰。利用網絡,恐怖分子只需一臺連接網絡的電腦,或手機等移動通訊終端,便可在任意時空或移動過程中發動多維、多點、多次的隱蔽性進攻,24小時均可作案,犯罪時間可短至毫秒計[16]。
目前中東的一些極端組織中,有相當一部分成員在歐洲出生、長大,這反映了恐怖分子早已跨越國界,甚至形成了“全球聯網”。跨國暴恐勢力對網絡的使用,使得新時期的暴恐活動呈現出一些新特征:
1.暴恐勢力通過網絡進行組織活動。包括培訓專門技術人員和建立分裂網站實施招募,以組織、拉攏、操縱部分人員;同時利用境外第三方電子支付平臺實現涉恐融資的跨國流動,獲得來自西方反華勢力的資金支持,以躲避我國在物理層面嚴厲的反恐措施。
2.通過網絡進行滲透。新時期的“三股勢力”更多地通過建立大量網站以及電子郵件、微信QQ群等即時通訊工具或經過偽裝的手機APP,來宣傳他們的極端思想,發掘一些好奇心強、社會閑散和持極端主義等對恐怖組織感興趣的受眾群體為恐怖組織成員,以擴大組織規模;或炒作、歪曲事實,制造事端,引起公眾恐慌,意圖引發社會秩序的混亂。
3.通過網絡進行跨時空有組織犯罪。恐怖分子利用網絡可以輕松進行情報以及技術上的跨地域、全時段交流,境外不法分子可能將具有殺傷性的生化武器、槍支彈藥等武器的技術圖紙資料通過互聯網傳輸給境內接收者,后者通過3D打印等先進技術手段進行組裝和制造。同時,境外恐怖分子通過網絡直接指揮境內的暴恐行動,形成了“利用互聯網或手機等方式進行境外策劃指揮,境內分頭或是統一組織實施的特點”[17]。
網絡恐怖主義的跨國傳播使其具有高度的隱蔽性,且擴散迅速,對我國特別是邊境地區帶來極大的安全隱患。例如于2013年9月21日上午發生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西門的“內羅畢商場屠殺事件”,就是由來自英國、索馬里等多國恐怖分子通過社交網站組織、策劃并實施的。還有2013年4月15日在美國波士頓發生的馬拉松賽恐襲事件,就是犯罪嫌疑人通過臉譜網接受極端思想,并在網絡上學習了炸彈的制造方法,在自家廚房制作簡易爆炸裝置后實施的。
三、網絡民族主義情緒傳播的跨國性
民族主義按其利益出發點的群體,大體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以國家為基礎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與通常所說的愛國主義比較相近;另一種則是以種族為基礎的民族主義,如一國內部存在多個民族或種族,那么每個民族或種族都有自己的民族主義。后者所指的民族主義,若其民族主義情緒過于極端,則不利于一國、特別是多民族構成國家的團結穩定。我國屬于多民族構成國家,特別是云南地區就有26個少數民族,是我國少數民族最多的省份。其中有多達20個跨境民族跨兩國或三國而居,是國內外反動勢力長期制造民族矛盾、挑撥中國與接壤國家的民族關系和煽動祖國分裂的重點地區。在這里,多種公共事件和突發事件容易與民族問題相摻雜,民族主義情緒在該地區的蔓延容易使得問題變得更加微妙和復雜,易激發負面民族主義情緒,傳播民族主義過激言論或民粹主義言論,甚至增強族際政治和經濟關系的對抗,從而引發跨界沖突。加之東南亞地區的三股勢力若與跨界民族問題結合,極易對跨界民族產生煽動性影響。就云南與東南亞跨界民族而言,東南亞的恐怖主義往往利用民族分裂勢力對所在國的不滿情緒,煽動后者對本國政府采取極端手段以強迫政府對他們的獨立要求讓步。若政府不同意,他們往往會采取恐怖主義的方式來解決。這種極端做法易被跨界民族所效仿,成為其向所在國政府訴求領土主權與經濟利益的手段,并逐步演變為地緣政治的不穩定因素[18]。
網絡民族主義是指,網絡空間中民族主義思潮和民族主義行為的總稱,它以網絡作為平臺、途徑、工具和手段進行相關的傳播、表達及行動,是民族主義在網絡條件下的新發展[19]。隨著網絡技術及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的普及與應用,民族主義傳播的渠道更為多元,互聯網的便捷性不僅使得信息傳播更加廣泛和深入,也調動了人們參與民族主義活動的積極性,越來越多的民族主義者通過網絡來發表各自的民族主義言論。他們充分利用網絡的跨地域性、時效性、便捷性等特點來傳播民族和國家事件,并發表引起網民廣泛討論的觀點,極大的擴大民族主義的傳播范圍和社會影響力。但不容忽視的是,網絡就像一個放大鏡,在放大人性的善的同時,也放大了人性的惡[20]。理性的網絡民族主義對民族發展及社會進步可以起到積極的作用,但非理性、極端偏激的網絡民族主義情緒會帶來消極影響。民族情緒牽引的缺位造成非理性言論的傳播,它們經過網絡的放大,將直接侵蝕民族間關系的和諧相處。如2018年11月17日,法國巴黎“黃背心”運動的爆發與持續,其重要原因就包括民族主義情緒經由社交媒體的網絡漫射。除了對互聯網及新媒體平臺的廣泛應用,云南邊境網絡極端民族主義情緒主要來源于:
首先,境外反華勢力和敵對勢力從未放棄利用互聯網信息傳播的無國界性,通過互聯網散布謠言,他們利用網民的民族主義情感和不明事理的心態,歪曲事實,傳播不良信息,煽動與蠱惑我國邊境少數民族群眾,削弱主流意識形態對他們的吸引力及凝聚力,以達到擾亂邊境秩序,破壞社會公共秩序以及犯罪分子的政治目的。他們一方面通過網絡,利用邊境地區現存的宗教、民族等問題進行意識形態領域的滲透,散布各類政治謠言,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指責我國的宗教政策與民族政策。甚至利用我國的民族主義分裂勢力為他們效勞,企圖削弱少數民族的國家認同,擾亂我國邊疆穩定;另一方面,境內外敵對勢力之間相互勾結,策劃并實施分裂活動。他們在境外組織與策劃,同時通過網絡與境內不法分子勾結,并發展境內成員、以及以西方國家為后臺的國內民族主義分裂勢力。如一些不法分子為了煽動民族對立情緒,將不實報道通過“翻墻”技術在境外網站傳播,而這些謠言正是境外敵對勢力希望加以利用的信息,他們對這些信息進行別有用心的再加工,以捏造事實。還有一些西方媒體也不惜舍棄文明的外衣,制造一些網絡輿論去刺激邊疆少數民族中一些人的不滿情緒,對網民進行思想滲透,以煽動邊境地區的群眾及信眾對抗黨和政府。2009年,極端組織“世維會”對廣東韶關市一玩具廠發生的員工械斗事件進行別有用心的利用,在網絡上散布謠言,傳播虛假視頻等信息,以挑撥民族情緒,將其人為泡制成一件民族沖突事件,煽動不明真相的維吾爾族群眾“積極展開活動,不怕犧牲”,最終釀成新疆“7.5”暴力沖突慘案。
其次,國內網絡民族主義者的惡意或非理性煽動。目前國內有相當一部分的網民,特別是大學生,在涉及國家或自身切實利益的問題上發表觀點時,往往只憑借自身主觀意志在網絡上發表和傳播情緒化和感性化的偏激及暴力性言論,而不經過理性與冷靜的思考。這些極端化言論在網絡上經過一定程度的傳播可能轉化為現實中的實際行動。網絡民族主義在我國的階段不成熟性易導致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在我國特別是云南邊境多民族地區的蔓延,對該區域主流意識形態安全建設帶來沖擊和挑戰,增加了該區域的社會不安定因素,亦可能造成云南邊境地區少數民族群體之間對各自身份的消極區分,威脅社會穩定與政治安全,亦有損我國的國際形象。比如對于一境之隔的緬甸,近年來國內戰事不斷,其戰火時而波及我國,2018年5月14日,緬甸兩枚炮彈落入云南境內,并造成中方平民死傷。隨后國內的社交媒體便開始出現一些極端民族主義文章及言論,其內容包括制造流言蜚語聲稱緬甸炮彈將再次投入我國邊境,并指責我國政府和軍隊對自身主權受到侵犯坐視不管;或呼吁邊境跨境民族對緬甸胞波的救助。這類時真時假的網絡宣傳信息極大的刺激了網民的民族主義情緒,對我國的外交選擇也產生一定影響。
當然,極端民族主義情緒在網絡上的傳播往往離不開國外反對勢力以及國內不理性網民的共同煽動。如對于目前的南中國海問題,大量帶有極端民族主義情緒的信息在網絡上產生和傳播,加上一些外媒的不實報道,導致許多中國網民在網絡上與他國網民之間展開罵戰,甚至有些中國黑客借助事件的發生而去攻擊其它國家網站,給他國造成中國黑客是一種有組織、由政府支持發動,或至少得到政府默許的錯覺,從而對我國的國際形象以及外交選擇帶來消極影響。還有2013年我國在緬甸的萊比塘銅礦項目被迫停滯,其中離不開西方勢力的煽風點火,以及緬甸國內一些政治組織和激進分子利用民族問題在社交媒體和大眾媒介上發布不負責任的言論誤導公眾。隨著事件的升溫,該地民眾通過網絡號召游行示威運動,該銅礦項目多次遭到當地村民的大規模阻攔,導致維持秩序的警察與村民發生沖突,造成人員傷亡,而后網絡上有許多人把人員死亡的責任,錯誤地歸咎于中國企業,甚至在社交媒體上呼吁“向越南學習,趕走中國人”“徹底終結萊比塘銅礦項目”等極端民族主義言論。這些極端民族主義言論及其導致的后果不僅影響緬甸國內的政治穩定,也對我國西南邊疆的帶來不穩定因素。
四、結語
網絡信息安全問題,已日益影響到云南邊境地區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以及國家安全,必須針對該地區網絡信息安全的新情況與新特點,建立一支有效防控和處置網絡信息安全的專業隊伍,形成云南邊境地區網絡信息安全的多級防控體系,以維護云南邊境地區的網絡信息安全,從而維護國家總體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