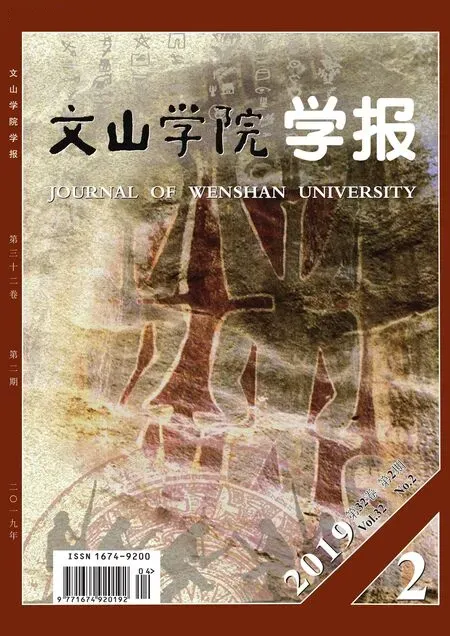“書同文”:對于滇東北次方言苗文通用文字統一使用的反思
葉洪平,汪 倩
(1.云南大學 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2.云南財經大學 物流學院,云南 昆明 650221)
作為文化的象征之一,文字不僅可以記錄歷史、創造文化和傳播文化,也有利于社會的管理、群體的認同以及國家的穩定和發展。對于一個民族和群體來說,文字的有無關系到了他們自尊心和自豪感的高低,同時也關系到個體對外交際范圍的大小。在近代中國社會中,由于社會發展與地區地理位置的限制,沒有文字的民族尚多。位于滇東北苗族支系的大花苗便是其中的一個典型。大花苗主要分布在川滇黔三省的交界處,在滇中、滇南亦有分布。由于其主體主要聚居在滇東北地區,因而大花苗的語言被稱之為“滇東北次方言”。該種苗族方言由于各種原因,在歷史上形成了三種文字,即“老苗文”“拉丁新苗文”以及“規范苗文”。
在基督教傳入滇東北之前,該地區的苗族社會被視為一個“化外之地”,能識漢字之人極少。直到傳教士來到該地區根據苗族衣飾上的花紋并結合當地的方言和拉丁字母以及苗語音調(聲母)創制了苗文——“波拉德文字”,即現在的“老苗文”,大花苗才有了自己的文字。隨著社會的變遷,政府和當地的知識精英為大花苗先后創制了“拉丁新苗文”和“規范苗文”。由于教會在當地的影響深遠、當地的信徒眾多,加上基督教在傳教和布道過程中對于“老苗文”的使用頗為重視,因此“老苗文”在苗族地區的使用范圍廣,運用的人數多并且影響久遠。時至今日,在以石門坎為中心的滇東北地區的大花苗群體中仍然廣泛使用這種文字。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拉丁新苗文”和“規范苗文”也同時在大花苗中推行。這三種苗族文字的并行使用造成了該群體中對于文字運用的茫然,究竟該如何對苗文進行統一以及使用哪一種或者如何融合這三種苗文形式值得考慮。本文的出發點即在于此,筆者在文中將結合中國文字上的“書同文”的推行及影響從“認同”的方面給予相應的回應。
一、秦朝“書同文”的實施與影響
作為中國文化史上影響最大的一次文字運動,秦代所施行的“書同文”政策對于整個中華民族的形成、融合及團結都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中國的文字歷史甚為久遠,在“書同文”之前的不同時期具有不同的文字,如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時代的文字、六國文字以及秦系文字[1]40。即使每一個統一的朝代都有數種不同并行使用的文字,但在全國統一使用的字體卻極少出現。商代所用的文字主要有甲骨文與金文。雖說這兩種文字同時在商代流行使用但二者在“字體上有不同的特點”[1]42,且字體的寫作方向也存在差異,甚至相反,不固定[1]45。到了西周春秋時代,字體的使用情況仍然如此。此時雖主要流行的文字是金文,但甲骨文和盟書仍在社會中占據重要地位。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的發展與習得依靠于社會剩余資源的支持,戰國之前社會物質產量普遍低下,中下層社會居民大都沒有學習文化的機會,文字的使用自然僅限于上層貴族。到戰國時,社會有了相應的發展,社會資源的剩余情況較以前提升了許多,因而個體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機會也隨之增大,民間使用文字的范圍也逐漸有所擴展。
眾所周知,文字作為一種文化的載體,會隨著地域的不同而出現差異,對于那些在行政和社會管控上有獨立行使權力的國家區域中也是一樣。東周戰國時期隨著各個諸侯國的獨立發展,出現的正是如此情況。各國由于地理位置不同,風俗習慣存在差異,因而在字體的寫作上差別甚大,流行的字體形式各樣,如金文、璽印文字、貨幣文字、陶文、簡帛文字、秦系文字等形式。即使有幾個諸侯國使用一種文字的情況,但是普遍來看仍然存在不同之處。在語言相同的地區,文字的差異性對于民間個體的日常生活的影響幾乎不大,然而在政治上卻形成了極大的困擾。一個在語言上、習俗上以及文字上都存在極大差異的國家,它在政治上的統治與社會管控更是難上加難。秦始皇二十六年,秦朝統一中國之后所面臨的便是如此一些困境。
秦始皇統一中國后,結束了由于諸侯爭霸導致的常年動亂的局面。盡管秦始皇在政治和軍事上實現了統一,但由于諸侯割裂的時間前后達數百年,因此秦朝各個區域在文化上的隔閡一直存在,即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所言的“田疇異畝,車涂異軌,律令異法,衣冠異制,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的社會狀況。這種差異并不像政治和軍事一樣會立刻隨著秦朝的統一就實現共融,除非政治上的強制,否則只依賴于民間的流動和訴求,它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情況。作為社會最高管控者的秦始皇為了自己的統治利益必然要進行文化上的統一。所以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才有如此記載:“一法度衡石丈余,車同軌,書同文字”。在文字的統一方面,自然是值得考慮的事情。
陳夢家先生認為:“每一個民族的文字,或為自造的,或為承襲別一民族的。……中國歷史的通例,常是武力強盛的異族接受被征服民族的文字,而被征服民族的文化較征服民族高。”[2]這一點對于朝代的更迭后統治者在文化的選擇上亦是如此。雖然秦國的文化較之于其他諸侯國的文化不一定為優,但秦國統一了全國,成立了政治管理部門,而且這個時期又是處于剛統一之后,對于樹立秦朝的權威和認同至關重要。選擇秦國自己的文字即隸書(小篆)作為全國的通用文字無疑最為適合。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說:“是時,秦滅書籍,滌除舊典。大發吏卒,興戌役。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而絕矣。”其他對秦朝“書同文”的記錄大抵如此。從中可以看出,為政治服務是秦始皇實現文字一統的原因之一。在完成“書同文”之后,這一政策對于當時的社會以及后來的中國社會、文化、經濟等等方面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對于秦朝的當政者來說,“書同文”使得之前的文字得到簡化,易于書寫,在民間社會得到普及和傳播。這對于中國文化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由于“官獄職務繁”,使用不同的文字進行書寫過于復雜,因而“書同文”可以避免這些不必要的繁瑣。使用隸書,其不但字體簡易,且便于書寫。這極大地提高了當政者的行政效率,同時也使行政人員在處理公務時更便利。秦代的“書同文”作為中國漢字規范的最要一步,為后來漢字的逐漸發展奠定了基礎。這些都是應該且已經被其他研究者所注意到的。然而,還有一方面需要提及的是“文字”與“認同”之間的關系。
歷來研究族群和民族的人類學家和民族學家對于“認同”頗為重視。但是他們多以個案的闡述來窺探某一個特殊的群體的認同,對于多元化的民族群體甚少有人注意。中國的民族構成復雜,地域廣闊,因而不同地方和民族在語言使用方面多顯復雜且各地風俗各異。如果僅僅以語言作為彼此之間的溝通手段和橋梁,恐無進行交際的空間。若以同一種文字作為彼此的交流工具,無論語言的差異如何大,只要書寫出來,兩個交流的對象之間的溝通便會進行下去。對于個人的認同來說,亦是如此。雖然單元個體對于國家整體的一些方面僅憑借自己的了解可能會出現認知上的偏差,但通過文字傳遞,便能給予相應的認識補充,這對于國家整體的團結是非常重要的。即使某一個個體,不識漢字,也可以由其他那些懂得自己語言又知曉漢字的人轉述。這不但能夠使得個體認識不同的世界,也能促進個體認知的提升和視野的擴展,同時使得群體之間的交融與互動更加頻繁,從而為自己在社會文化等諸方面的發展創造一個有益的空間。
或許“書同文”對于政治治理、社會穩定以及文化的影響與上述觀點相差不遠。“滇東北次方言苗文”的創制、發展與統一使用的目的都在于此。然而,“書同文”在當今滇東北次方言苗文的統一是否適用呢?欲回答該問題,必須闡述滇東北次方言苗文的發展歷史和幾種字體形態及其使用的爭議。
二、滇東北次方言苗文的發展與幾種形態
作為苗族的一支,大花苗的歷史頗為悠久,然而在文字方面一直是其“短處”之一。雖然歷史上苗族的其他支系曾出現過文字,但是這些文字是否為苗族自己所創而不是其他群體的借用至今仍然是懸而未決的問題,對于大花苗來說更是如此。在大量的史籍中至今仍沒有足夠的證據確定大花苗存在過相應的文字。許多學者認為大花苗曾經擁有過象形文字,并引用各種縣志作為證據[3],然而他們所忽視的是自己所引用的縣志多出自于民國時期,此時所記錄的大花苗文字即老苗文仍是外國傳教士在清末來到該地區后才逐漸形成的一種拉丁拼音文字。
苗族過去雖有文字使用的記載,但并沒有得到廣泛傳播的主要原因在于自身遷徙過于頻繁,進而造成散雜的分布格局所致。自從先秦時期開始,苗族就開始從黃河向南大量的遷徙,經過歷代的變化使該民族的分布雜亂,彼此之間的聯系交往弱,從而造成發展不均衡的局面。所以就算是某一支系的苗族擁有文字也只能在內部甚至本地區使用。
另外,苗族與其他民族相比稍顯自閉,“新中國建立前,苗族是不與異族通婚的,否則便認為是一種傷風敗俗的行為”[4],與異族通婚的苗族會遭到其他人的唾棄,甚至會被趕出寨子。就連呂思勉先生在撰寫《中國民族史》的時候都感嘆苗族“派別至繁,彼此不同婚姻,故不能團結。其于漢人,有深閉固拒,不肯通婚者;亦有慕與漢人結婚者。然漢人多鄙視之,不愿與通婚姻。今貴州男子,有娶苗女者,猶多為親族所歧視;甚至毀其宗祠。至漢女嫁苗男者,則可謂絕無矣。以是故,其種類頗純,迄今不能盡與漢人同化。”[5]加之其“遷入之地,又多是荒僻山區,惡劣的自然條件阻礙和延緩著生產力的提高”,“居住的分散,形成了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嚴重地影響著苗族統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形成,”“遷徙使苗族各部之間彼此隔絕,少于交往。由于各自所處的自然條件不同,歷史不同,受其他民族的影響也不同,從而導致相互間出現較大的差異,造成支系多、方言差別大、服飾類型多樣化的現象。”[6]因此“苗族既難團結,習俗自生相異……半載以外,視如路人。老死不相往來,鄉音亦隨環境而改。同枝連理,幾至判若二族。若是者,非血統之各特殊,實環境所役使”[7]18。以上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苗族文化的相對“落后性”,本民族之間以及與漢族或彝族等等民族交往甚少,文字的出現更是無從談起,加上“自閉”的性情,“不識字苗民,居全數百分之九十以上”[7]39。
較之于整體苗族的上述情況,大花苗更是如此。他們“與他種苗族無婚姻關系,其性格孤僻,不與外界接觸,故生活完全形成一種獨立形式”[8]。因而該族群文字的出現和使用也是如同其他苗族支系一樣是在晚近時期。但是,從現有的文獻和影響程度上來看,大花苗的文字較之于其他苗族支系則顯得更加的突出。
大花苗最早的文字,被稱為“老苗文”,是由清末民初傳教士和當地的漢族、苗族等一起創造的拉丁文字。由于這套文字是在外國傳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主導之下進行創制并改善的,所以也被稱為“柏格理文”或者“波拉德文”。這套文字是創制者“從大花苗的傳統服飾紋樣中獲得靈感,借助于祖先古歌、故事遺傳文字失而復得的神話,(因而)苗民相信這套文字是從苗族衣裙圖案中重新識別和恢復出來的。”①加上基督教采用一系列的措施辦法在滇黔川等地區進行傳播,又著重以學校擴大影響,當地的教會及其勢力頗大,學校的分布亦廣。據20世紀40年代的調查顯示,“計在黔滇境界有三十七所,川境有十五所,共計五十二所,苗夷子弟培植成功為數甚多。”[9]由此可見,“老苗文”在大花苗中的影響久遠,同時也獲得了大花苗的認同。時至今日,在大花苗社會中仍在廣泛使用。
“新苗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國家考慮到許多少數民族沒有文字,由國家民委組織了一批專家來為他們創造的文字。“規范苗文”則是20世紀80年代之后,由滇中地區楚雄武定的部分大花苗知識分子與干部的共同努力下為了改善“老苗文”,克服“老苗文”音位符號不準、一音多字的問題而創制出來的“苗文”形式,被稱為“滇東北次方言云南改革版苗文”或“楚雄規范苗文”與“滇東北規范苗文”。
以上是現在在滇東北大花苗中使用的三種文字形式及其創制與發展的情況。從其產生和發展來看,不論是“老苗文”或者“規范苗文”還是“新苗文”都有自己特定的意義和社會背景,因而在一些不同的苗族地區在使用“苗文”方面也存在差異。滇東北次方言苗文的三種形式是在不同地區和不同時期內由不同的人創制和改善。作為一種集體的記憶和自尊心、自豪感的象征,在不同文字創制的地區都有不同的人在使用。目前的大花苗社會中這樣的文字使用狀況仍然存在,且情況愈變復雜。
“老苗文”是由中底層群體開始創立的,因而具有極強的群眾基礎。該套文字的構造與大花苗社會中的生活日常以及神話傳說聯系在一起,簡單易學,同時又在教會中通過教會書籍和教育的宣傳,所以在很多大花苗聚居地區都在使用。即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30年,屢次遭受到打擊,甚至在官方的各種宣傳中接近消失,但在大花苗的民間社會中仍然薪火相傳。至于“拉丁新苗文”,雖然得到行政力量的推廣,但是創制該套文字的人對于大花苗缺乏一些日常生活的體驗,加上后來的推廣力度不夠和時間周期不足,使用的人數較少,至今為止學會和使用的人并不多。“規范苗文”是在“老苗文”的基礎上修改而成,錯誤較之于“老苗文”更少,音字之間的聯系也更強,但“規范苗文”難學習,且缺少一種如同教會一樣具有跨地區的推廣力量,因而只能在“規范苗文”的創制和修改地區即楚雄的部分大花苗地區使用。對于那些較為注重文化傳統的大花苗來說,他們依然遵守傳統的書寫和認知范式,即使用“老苗文”來進行自我的認同以及對他人的教學。
三、反思與討論
前文已經對秦始皇的“書同文”與大花苗各種文字的創制進行了簡要的梳理。從中可以看出,秦始皇“書同文”的前提是秦朝統一之前各個諸侯國都已經有了相當成熟的象形文字,雖然在書寫上具有較大的差異,但是在字體的構成上大同小異。秦朝的統一、強有力的政治推廣和民間的自我需求為“書同文”的實施賦予了更加強有力的政治與群眾基礎。秦朝的“焚書坑儒”的推行,使得各國文字遭受到了更加嚴重的打擊,同時也推動了“書同文”的實現。按照唐蘭先生的說法這實際上就是:“新文字的發生,根于事實的需要,因為產業的發展,文化的進步,增加了無數的新語言,只用圖畫文字和引申假借是不夠表達的,那時的聰明人就利用舊的合體文字、計數文字、聲化文字的方法來創造新文字。這種新文字一發生,就很快的發展起來。”[10]78
苗文(特別是老苗文)的創制和實施與“書同文”之間存在一定的相似之處。首先,在“老苗文”創制之前,大花苗是沒有文字的,但在大花苗群體中又具有讀書識字的需求,因而“老苗文”的推行實際上是大花苗的自我需求的滿足,這與“書同文”的前提一致。其次,與隸書和小篆一樣,“老苗文”是從苗族社會生活中和神話傳說中來進行創制的,簡單易寫,對于沒有文化基礎的苗族個體來說學習起來甚是容易。最后,與秦朝利用高效的行政力量推廣一樣,“老苗文”在教會的組織下進行傳播和推廣,遍布眾多大花苗的聚居區。而且由于“老苗文”創制地區的發展,其文化地域成為“西南地區苗族文化的最高區”,前來求學的人絡繹不絕,這對于“老苗文”的推廣作用甚大,在民間的使用范圍廣泛,逐漸成為了大花苗的文化自信與自豪以及自我認同的象征符號之一。正是如此,后來的“新苗文”以及“規范苗文”(即使是在老苗文的基礎上改制而成)失去了“老苗文”的傳播基礎,并沒有在大花苗地區廣泛的使用,因而這兩種文字的影響遠遠遜于老苗文。甚至在2018年1月在威寧召開的“滇東北次方言苗文通用聯席會”會議上將老苗文認定為大花苗的通用文字。
但是值得反思的是,老苗文真的能夠如同隸書那樣能夠在“書同文”的開展下得到統一使用嗎?“書同文”的實現對于中華民族的認同和溝通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并成為近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的一種愛國標志,亦成為學人宿儒們的研究方向之一。較之于拼音文字,中文不僅消除了中國各個地區不同方言之間的隔閡,而且實現了古今對話的時空交流,這是拉丁文字所不具備的功能。唐蘭先生認為:“中國文字沒有發展為拼音的,而只是注音的,在學習時雖然不如拼音的方便,但是它能代表古今南北無數的語言,這是拼音文字所做不到的。”[10]9
然而,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甚至在近代以降,在中國的許多其他沒有文字的民族受到西方文化的影響,采用形音一致的拉丁字母來創制少數民族的文字,這無疑在中國的民族社會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一點在“新苗文”的創制中早有體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為全國創制拉丁苗文時,由于不同地區的苗族方言之間存在極大的差異,導致語言學者們不得不采取不同的方言來為不同方言區的苗族創造文字,最后形成了多種苗文即“湘西方言”、黔東方言和“川黔滇方言”等并行使用的情況。由于形音一致,因此在不同苗族語言地區不能進行相互的溝通與交流,這也就喪失了“漢字”的跨語言與地域的交流功能,對于苗族支系之間的認同無法起到鞏固的作用。
“老苗文”作為目前有直接證據證實的,是由苗族參與創制的文字,它不僅成為了大花苗文化史上的一個里程碑,而且對生活在大花苗附近的其他民族亦有影響。在某種意義上來說,“老苗文”使得大花苗從以前文化被動的角色中轉向了文化傳播的主動角色,這對于大花苗的民族自豪感的產生和提高具有關鍵的作用,自然很多大花苗群體愿意使用它。按照同樣的邏輯關系,“規范苗文”是在滇東北地區改善和推廣的。該地區的大花苗也同樣存在一種文化自豪感,接受和使用都存在合理的一面。然而現在卻要使之成為一種文字來使用,其中必定存在相當多的困難。
“滇東北次方言通用文字”既沒有如同“書同文”那樣的執行效率,也沒有像中文那樣形音分離的功能。加之上文所分析的文化自豪感在群體中的相互沖擊,更加使得“滇東北次方言通用文字”的統一難上加難。若要使得滇東北次方言的文字得到統一,這兩點是必須要考慮到的因素。
注釋:
①參見沈紅.活在苗寨的字符.載于楊華明編,苗文課本·第一冊.未刊稿第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