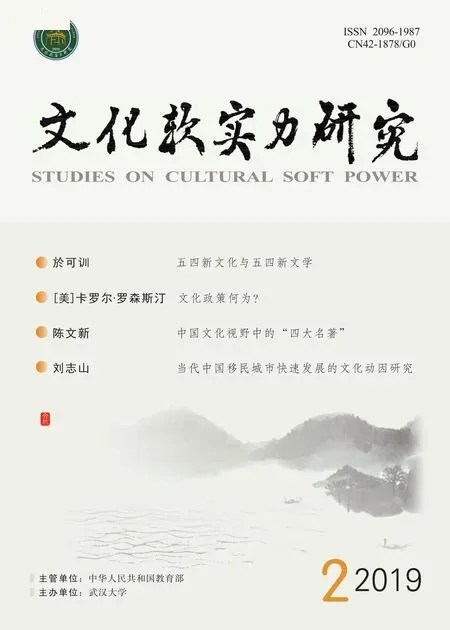五四新文化與五四新文學
——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
於可訓
今年,是五四運動發生一百周年紀念。以五四運動為標志的五四新文化,是新舊文化的分水嶺;以五四新文化精神為標志的五四新文學,也是新舊文學的分界線。雖然新文化的醞釀和新文學的發生,都經歷了一個較長的孕育過程,新文化和新文學的萌芽,在五四之前已初露端倪,但五四運動作為一場以先進青年知識分子為先鋒、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愛國革命運動,一場中國人民為拯救民族危亡、捍衛民族尊嚴、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偉大社會革命運動,同時,也作為一場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偉大思想啟蒙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其標志性和里程碑的意義,卻不可低估。五四運動是一個歷史事件,但五四新文化卻不宥于事件發生的某一個歷史時刻,而是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在近現代之交經歷艱難蛻變浴火重生的結果。因此,研究五四運動,要堅持“大歷史觀”,討論五四新文化與五四新文學問題,也要堅持這個“大歷史”的觀點。
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之前中國的舊文學,雖然也存在某些“人民性”和“民主性”的文化因素,晚明和近代文學甚至還包括某些現代啟蒙思想的萌芽,但從總體上說,受制于儒家思想占主導地位的封建文化,正統詩文受其影響更甚。所謂“文以載道”,雖然對“道”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但終歸不出儒家的“道統”。從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五四新文化運動發生之前中國的舊文學,是“文”和“道”同一的文學,也是“文統”和“道統”同一的文學。清代陳玉璂說:“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以道相傳,稱曰‘道統’。所傳者道,而道之賴以傳者文,故曰:‘文者,載道之器’。文與道固未可歧而二之。”①(清)陳玉璂:《文統序》,載李國均主編:《清代前期教育論著選·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47頁。
因為這樣的“文統”和“道統”從形式和思想兩方面束縛人們的思想,阻礙社會的發展進步,所以,五四“文學革命”就不但要求語言文字和文學形式的“大解放”,而且還要以這種“解放”了的語言文字和文學形式“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這種有別于封建“道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在五四之前雖然比較駁雜,但在經過激烈的新舊文化思想斗爭,尤其是在五四運動和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逐漸集中到業已形成的以五四運動為標志的新文化方向上來。這個新文化方向所凝聚的新文化思想,不但是指引五四以后新文學發展前進的路標,而且也是五四以后新文學反映社會生活、觀察人生問題乃至藝術革新的思想利器。它貫穿于五四以后整個新文學的歷史,是五四以后新文學的靈魂和主腦。雖然在不同階段的新文學中,這種新的文化思想影響有不同的表現,但其內在精神都源自五四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的一脈傳承。
作為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起點和邏輯起點,五四時期的文化革命,是從批判封建舊文化,尤其是儒家的封建禮教開始的。魯迅的小說和雜文,包括文學研究會和早期“鄉土文學”作家作品,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也深入地解剖了受這種禮教毒害而被扭曲的“國民性的劣根性”。郭沫若和冰心等人的詩歌創作,則從另一方面,或以磅礴之力發出反抗的呼號,或以赤子之心謳歌母愛和自然,都因為五四新文化的影響,而使這期間的文學充滿戰斗精神和青春氣息。
從五四到20世紀20年代中后期,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學由“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的轉變時期。早期共產黨人針對五四以后出現的短暫的“退潮”現象,適時地發出了“革命文學”的倡導,并在蘇區的文化活動和文學創作中,開始了初步的實踐。這樣的倡導和實踐,對20年代后期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促成了“文學革命”向“革命文學”的歷史性轉變。這種轉變同時也是現代中國新文學的一種方向性選擇,是五四新文化深入影響現代中國新文學的表現。因為這種轉變,五四新文化對現代中國新文學的影響,也由抽象的啟蒙理念,進到具體的革命思想;由知識分子的思想文化啟蒙,進到人民大眾的階級政治啟蒙。雖然這期間的“革命文學”即早期“普羅文學”創作還難免稚嫩,甚至招來“革命加戀愛”之譏,但卻為30年代的“左翼文學”創作開辟了道路,奠定了基礎。
30年代的“左翼文學”,是受五四新文化影響的現代中國新文學開始結合中國革命的實際,確立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文學主體的時期。這個時期,從域外譯介引進了較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和革命文學作品,為在五四新文化影響下確立的革命文學方向,提供了理論根據和實踐經驗,促進了“左翼文學”的理論建構和創作發展。魯迅的“匕首投槍”式的文學批評,瞿秋白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譯介,以及茅盾和“左聯”五烈士的文學創作,集中顯示了“左翼文學”的實績,文學“大眾化”運動也收獲了最初的成果。與此同時,以巴金為代表的一批“革命民主主義”作家,雖不屬于左翼陣營,但始終堅持五四新文化徹底反帝反封建的立場,且在藝術上日臻成熟,在這期間,也以他們成就卓著、影響深遠的創作,秉承和發揚五四新文化傳統,成為“左翼文學”有力的同盟軍。
抗日戰爭時期,因為日本帝國主義入侵,民族矛盾上升,五四的“救亡”意識和愛國精神,在這期間的文學中空前高漲。文學在“拯救民族危亡、捍衛民族尊嚴、凝聚民族力量”的斗爭中,成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①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載《毛澤東論文藝》,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版。的有力武器。毛澤東通過《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確立了“人民大眾”這個五四時期反帝反封建的主體作為文學的服務對象,并通過“民族化”和“大眾化”的形式,為五四以后的新文學創造了一種“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②《毛澤東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4頁。五四的文化精神被毛澤東創造性地發展成獨特的新民主主義的文化思想,成為引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以及此后相當長一個歷史時期中國文學發展前進的方向,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歷史影響。根據地、解放區描寫勞動人民翻身得解放和戰斗英雄奮勇殺敵的作品,集中反映了五四新文化精神的不同側面,是廣大人民群眾反帝反封建的要求和救亡圖存、爭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意識的藝術結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五四時期所追求的“青春中國”的理想開始變為現實。五四新文化中所包含的社會主義因素,也開始變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中國社會由五四所追求的徹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義,進入到追求更高革命理想的社會主義階段。這種歷史性的轉變,見之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文學,是以五四所特有的革命激情和理想主義精神謳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反映五四以來,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為實現共產主義理想而前赴后繼的革命斗爭歷史。以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為題材,尤其是以農業合作化運動為題材的作品,以及反映革命斗爭和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歷史的“新英雄傳奇”,是上述方面在創作上的代表。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文學,又以“回歸”五四的姿態,接續五四傳統,重建五四精神,以更開放的觀念和更新的形式,反映中國人民建設現代化強國的歷史實踐。這期間文學中的“新啟蒙”思潮,是五四新文化影響的重要表現。
從改革開放新時期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五四新文化傳統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光大。五四的愛國主義、革命精神和強國夢想,正集中凝聚、體現于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追求奮斗之中。現階段中國文學正在這條奮斗之路上,由雄渾的“高原”向巍峨的“高峰”攀登。100年前發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結束了封建時代的舊文學作為封建“道統”“載道之器”的歷史,開創了一個“傳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識”的現代中國文學的新時代,引領現代中國文學為實現五四的偉大目標,作出了巨大貢獻,造就了中國文學歷史上一個輝煌燦爛的新世紀。在實現強國夢的未來兩個百年時間內,五四精神仍將是燭照中國文學前進的精神火炬,中國文學也必將在五四精神的引領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創造更輝煌的業績。
謹以此文紀念五四運動一百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