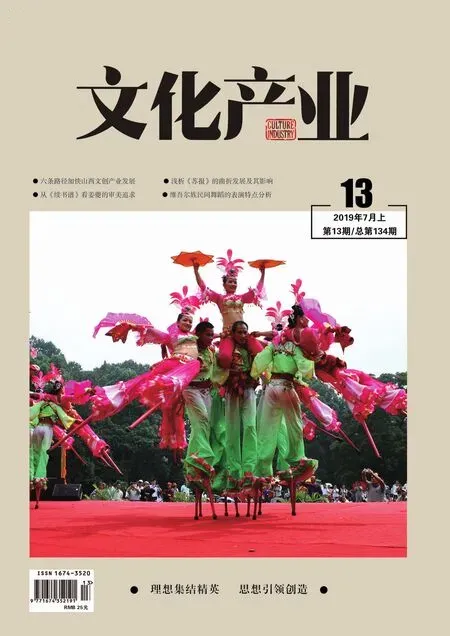從《續書譜》看姜夔的審美追求
◎葉立青
(高州市第七中學 廣東 高州 525200)
一、引論
《續書譜》是南宋最重要的書論,代表著當時書論的最高水平。它不但具有很強理論價值,而且包含了豐富的美學意義。本文欲通過解讀其書法理論,探尋藝術理念,進而解讀其藝術風格與人生追求。和《書譜》相比,無論是理論價值上,還是美學意義上,《續書譜》都略遜一籌。但《書譜》也有其缺點:理論為主,語焉不詳,可操作性差。《續書譜》則很好地彌補了《書譜》的不足,它立足書法本體,從小處入手,以通俗的語言對書法藝術作出頗全面的、精練的分析。全篇共二十二條:總論、臨摹、書丹各一條;論書體的有三:真書、行書、草書;論用筆、墨的:用筆、真書用筆、筆勢、遲速、用墨等五條;論章法布局的:位置、疏密、方圓、向背各一條;還有風神、情性、血脈等論書法審美的。論者忠實于實踐和親身感受,論說簡潔通達,宜于初學者學用。王鎮遠先生說:“《續書譜》意在發揮孫過庭《書譜》中語焉未詳的內容,力求以平易通俗的語言出之,又頗多取自實際經驗的甘苦之言,較孫氏之論更為凱切明白,故歷來為學書者所重。”①
二、內容和藝術意蘊上的神妙之美
魏晉書法以俊逸名世,以風度為勝。李澤厚說過:“書法藝術以極為優美的的線條形式,表現出人的種種風神狀貌,‘情弛神縱,超逸優游’‘力屈萬夫,韻高千古’‘淋漓揮灑,百態橫生’,從書法表現出來的仍然主要是那種飄俊飛揚,逸倫超群的魏晉風度。”②眾所周知,姜夔是個藝術全才,他在詩、詞、樂、書上都有很高的造詣。首先,祈好魏晉,強調風神蕭散、高妙自然,追求瀟灑飄逸,表現“神妙之美”是姜夔書學、詩學乃至詞學的最突出的審美追求,也是他的審美理想的最高表現。
“神”是《書譜》中最重要的美學范疇。據統計,在《續書譜》中,“神”字共用了20次,主要有:風神、精神、神氣、神奇等,其中以風神和精神為最多(各有6次)。在論草書時說:“若風神蕭散,下筆便當過人。”關于“風神”姜夔總結了8點:“風神者,一須人品高,二須師法古,三須筆紙佳,四須險勁,五須高明,六須潤澤,七須向背得宜,八須時出新意。”他所謂的“風神”,是以書家的品格和修養為基礎的,從其書法中呈現的神韻氣格。所以“人品高”與“師法古”放在首要位置,又需紙筆精良,結體得當,富于變化和個性,故有“險勁”“高明”“潤澤”等要求。其實“風神是包涵了書法創作中的主客觀雙方及技法等因素在內的一種綜合的審美理想,它主要以疏散放逸、超塵絕俗為特征,故姜夔在論‘疏密’中說:‘書以疏欲風神’;論行書中說:‘所貴乎濃纖間出,血脈相連,筋骨老健,風神灑落’;論‘臨摹’中說:‘字書全以風神超邁為主。’以疏朗、灑落、超邁等詞來形容‘風神’,可見其意在標舉自然灑脫的審美趣尚。”③可以說,高妙風神、自然飄逸是姜夔的審美追求的最高境界。
為此,姜夔認為一方面要達到“妙”境;《續書譜》中“妙”共用了8次:神妙、精妙、奇妙、要妙、妙處等。“妙”既是一種審美效果和原則,也是一種審美追求。在論詩中,他認為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二曰意;三曰想;四曰自然。所謂“高妙”就是超凡絕俗、風神高雅,也就是反俗倡雅的體現。對于這四種“高妙”的意義,郭德強先生分析道:“此種四類高妙的逐步升級,對于啟發藝術家從較自覺的藝術追求,到審美情感與藝術構思的自由升華,是很有意義的,它有益于藝術家從切近創作的實際的自覺追求逐步進入藝術的大悟境界。”④
另一方面,必須要避俗。《續書譜》中,“俗”字出現了8次,如:俗病、俗論、俗濁、塵俗、俗姿、近俗等。姜夔反對“俗”,與其為人品性及審美原則密切相關。關于神妙境界的標準,可參考其詞論:“喜詞銳,怒詞戾。哀詞傷,樂詞荒,愛詞結,惡詞絕,俗詞屑。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其唯關雎乎?”⑤神妙應該剔除:銳、戾、傷、荒、結、絕、屑等“俗”病。神妙之美,是絕俗的藝術創造和藝術家修養共同作用的結果。
三、形式和表現手法上的中和之美
“中和之美”是中國古典美學的重要標準和原則。姜夔強調風神高妙、文雅自然文藝美學的同時,還重法度、構思與安排。這種中和理念,表現為追求高妙自然與法度經營統一的風格。
他既重變化,反對單一呆板,又重法度,要求不出離法度,于法度之中融入變化。《續書譜》主要從筆法、墨法、章法、構字等方面分析書法之法。文中“法”字用了13次,除3次是書法之名外,其余均指法度。如“轉折者,方圓之法”“雖復變化多端,而未嘗亂其法度”等。他認為學書要取法古人,并且取法不是固守成規,要會變化。在變化的基礎上,追求晉人之飄逸,避免俗與滯,進而達到諧和統一的中和之美。
至于筆畫,他主張筆鋒要藏露兼用,變化多端,動靜結合,變化飄逸又符合法度。其中包含著一系列對立統一的關系:藏與露、起與伏、動與靜、發與變等。這正是他中正和諧的審美理想的表現。只有融合各端、不走極端、立足雅正,才能在對立統一之中追求自然、和諧、高妙的優美境界。
在討論字的結體中,姜夔道:“字之長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齊,孰能一之?……魏晉書法之高,良由各盡字之真態,不以私意參之。”魏晉之書之高妙,是因為他們懂得變化之妙,順乎漢字之“形態”。在論“疏密”的時候,認為不能夠刻意、矯作,要順乎自然,合乎天;在論草書時,他認為草書結體上要同中有異、異中含同,出乎意料,又合乎規律,于無法處見法;在用墨上,他認為墨色要根據書體的不同而不同,墨分五色,要合理運用,潤燥、枯濕、清濃相結合。從這一系列的關于法度的探討,可看出他既講究藝術的人為因素,重視自然天放,又反對固守陳規、囹于法度,努力實現“心手諧和”“人書俱老”的天人合一的自由境界。
在詩法上,姜夔在繼承江西詩派:“點石成金”“奪胎換骨”等詩法理念的基礎上,突出活法,提出“圓活說”。郭德強先生分析道:“黃庭堅最早的活法是‘奪胎換骨’,呂本中的活法則是‘圓轉’‘變化’,楊萬里的活法帶有更加自由的性質,是‘優游厭飫’,而姜氏的活法才可以說是‘輕松圓活’。”正如白石自己說道:“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自不俗。”詩之高,不僅僅在意、在情,更在于法。“如兵家之陣,方以為正,又復是奇;方以為奇,忽復是正。出入變化,不可紀極,而法度不可亂也。”⑥
其實,姜夔之所以不固守成曲,樂于自度詞曲,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圖新、圖變。要想有所突破,要如柳、周一般,努力尋求自己的藝術詞匯,言自己獨特之情性。且“變法”有內容上的,也有形式上的。按江蘇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宋詞鑒賞辭典》之附錄三詞牌介紹中所述:姜的主要自度曲有《揚州慢》《暗香》《疏影》《長亭怨慢》《淡黃柳》《八歸》《角招》《凄涼犯》《翠樓吟》等9首。幸運的是姜夔的初衷得以實現,《揚州慢》《暗香》《疏影》等曲是他的代表作,無論形式還是內容都足以與李、蘇、周并肩。
姜夔追求和諧優美的審美境界,追求藝術創作過程中法度的圓活與變化,力求擺脫類似唐人楷書那樣的刻板、缺乏飄逸之氣的囹圄,寄希望于在對立統一的矛盾審美活動之中以找到一種左右逢源的方法。在符合綜合原則的前提下,盡可能增加或者激活審美藝術的自由程度,從某種程度上說,這是對江西詩派的“過分理性自覺”思想的一種突破。
四、結語
姜夔以詞名聞名于世,但其詩名、書名、樂名亦應受到足夠的重視。藝從心生,其詞格即人格,其藝品亦即人品,白石以他杰出的藝術才華,以他深邃的藝術情懷,以他瀟灑飄逸、襟懷灑落的品性,為我們呈現了一個與眾不同的,如閑云野鶴般的,“騷雅狷介”的專業平民藝術家形象。
每一位藝術家都是一名探索者,是藝術殿堂中的創造者。客觀地說,姜夔對魏晉藝術之飄逸清雅、高妙自然、變化合宜的美學理想的認同和追求,是他長期的藝術經驗的總結;也是一種自覺的有意識的選擇;更是他的品性、人生哲學等主觀因素與時代背景、思潮、現實社會等客觀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在《續書譜》中,貫穿著一種探索精神,其中,有書法本體上的,也有關于書法主體的,還有關于藝術手法上的。正是這種對藝術創作的不斷創新與不懈的探索,積淀了姜夔的書論的審美準則。因此,神妙之美與中和之美,既是白石先生書法藝術理論上的成果,也是其審美追求的重要組成部分。姜夔的努力在于總結前人的經驗,尋一條自覺地達于和諧優美的途徑,因此,他更多是從審美藝術的角度思考探討問題的。⑦
從《續書譜》到《降貼平》;從《白石道人詩說》到《白石道人歌曲》;從《白石詩集》到《琴瑟考古圖》,姜夔以他豐碩的藝術成果,向后人展示了他獨特藝術魅力和哲學思想。從南宋書壇的衰微之中、南宋末期詞壇的柔婉之中、南宋詩歌的纖巧之中,姜夔融合了各藝術門類的陰柔之氣質,為實現風神高妙、和諧優美的藝術境界而不懈奮斗。而透過《續書譜》,白石先生向我們展示了其在書法和詩詞藝術中的審美追求和美學理想。
【注釋】
①③王鎮遠《中國書法理論史》,黃山書社,1996年,294-295頁。
②李澤厚《美學三書》,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92頁。
④⑦郭德強《宋元文化與宋元美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144-147頁。
⑤趙仁珪《論宋六家詞》,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233頁。
⑥郭德強《宋元文化與宋元美學》,人民出版社,1994年,1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