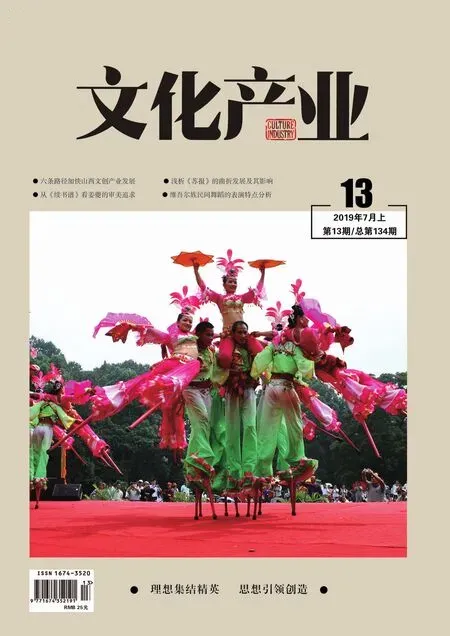從《老錢的燈》看寫作中的靈感思維
◎王 光
(靈璧縣高級職業技術學校 安徽 宿州 234299)
創作是人腦的一種創造性思維活動。在創作中,有一種特殊的心理現象稱為靈感。靈感作為一種創作狀態,常常為詩人作家們苦苦追尋。那么靈感究竟是如何產生、如何閃現、如何外化的呢?這一直是我感到困惑的問題。
讀了北京大學副教授孔慶東的散文《老錢的燈》,我為其語言的表達、思想的表現、情感的涌現、意象的選擇所驚異。文章雖僅有短短幾百字,但它處處閃現著靈感的火花,通過對文本的深入思考,關于靈感的問題,我有了一些體悟。帶著這些問題,從《老錢的燈》這篇文章的解讀入手,也許是探討靈感思維在寫作中的運用與內在機制的一個很好的角度和方法。
一、靈感對創作過程的整體統馭
在這篇文章中,孔慶東之所以選擇“燈”這個意象作為切入點,以小見大,概述錢理群先生的生活點滴,自有其深刻的道理。自古以來,許多文人墨客就喜歡用“燈”“蠟燭”等來比喻人的孜孜不倦、無私奉獻的精神,如文章中提到的“白發無情侵老境,青燈有味似兒時”[1]和李商隱《無題》中的“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等等。古典文化的深刻影響,使孔慶東在很久以前就已經把自己的導師錢理群比喻成“蠟炬”般的人物,他會時時注意著老師那盞青黃的燈,正如文章中所說:“不知不覺,我竟養成了一種毛病,只要晚上出門,來回總要繞到那窗下。看一眼那燈,似乎心里就多了一份舒坦。”正是這種情感上的積淀,才使得孔慶東能在偶遇外界刺激的情況下,迸發出靈感的火花。
靈感實際上是創造性思維的一種形式,在藝術構思或創作的過程中,處在一種特別活躍的狀態,是藝術構思或創作階段最重要的思維方式之一。靈感是一種帶有突破性、創造性的活動,它的發生和其他創造性思維認識活動一樣,必須基于實踐而始于問題[2]。
文學創造的素材是作家從社會生活中獲得的。但是生活中的各種信息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被及時選擇,其余的則被“遺忘”了。這里所謂的“遺忘”,并不是丟失,現代心理學發現,這部分被“遺忘”的信息則是進入了潛意識,當積累到一定的程度,達到質變的階段或者受到外界的刺激,作家就會出現創作的欲望和激情,這就是靈感突發的瞬間。阿·托爾斯泰不只一次說他的短篇小說:“鬼知道是從哪里來的,有的是從十年前某人說的一個故事,有的是從一個可笑的字眼。”[3]隨著時光的轉換,當作家的創作意向發生變化或遇到外界刺激,可能就會有靈感閃現,這些在當時不被注意的故事或字眼又跳入作家的思維中。
孔慶東和錢理群先生相處的分分秒秒,導師的一切都在作者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盞燈,一聲笑,一個煎餅果子……這生活的一點一滴,被孔慶東的大腦吸收,慢慢積累在潛意識當中。當積累達到一定程度,被某一事物觸發時,比如由一個薄煎餅果子,想到“老錢”也許正餓著,再由此想到“老錢”的生活點滴,引出對導師治學精神的贊美,潛意識中的印象上浮,進而完成一篇贊美導師的佳作。
二、靈感在創作過程中的閃現
孔慶東和錢理群先生朝夕相處,自然對老師身邊的事物熟悉至極,可是他為什么單單選擇“燈”這個意象來作為表現老師治學精神的切入點呢?
(一)一般意象的燈
從原文得知,孔慶東和同學們經常晚上去導師那討論問題,自然就無法避免和導師“那間斗大的宿舍里”的家用電器——“燈”打交道。“一片黑乎乎的身影”使原本就不亮的小屋顯得更加昏暗。“我常常從那支燈下經過,21樓的西半邊,沖南,二層中間的那個窗口。我披星戴月從三教回來,耳朵里落進一串老錢粗獷的笑——大概又在接見什么文學青年吧。我深更半夜從校外回來,那窗口像一只炯炯發光的眼睛注視著我。不知不覺,我竟養成了一種毛病,只要晚上出門,來回總要繞到那窗下。看一眼那燈,似乎心里就多了一份舒坦。”經年累月,習慣從那盞燈上尋找老師身影的孔慶東,當忍不住想為自己的導師寫點東西的時候,那盞青燈自然而然地就出現在作者的頭腦中,這就是長期的生活積累帶來靈感閃現的結果。
由此可以看出,靈感在作者選擇主體意象的時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沒有“只要晚上出門,來回總要繞到那窗下”,這種習慣性的行為,就不會有靈感的迸發,就不會有“燈”這意象的產生。我們知道,當一個作家在構思某個作品時,那種構思的沖動是長期積累的結果,而這結果往往會被作家心靈感覺到的一個視覺形象、一段經歷、一次遭遇、一條消息、一個故事、一個人物、一個細節等某種偶然因素所觸發,往往與作品中最富生命力的意象相聯系,這也是靈感降臨的表現。在《老錢的燈》中可以明顯發現這一點:“我就想:去看看老錢的燈吧,順便吃個煎餅果子。”自己在餓的時候,想到吃個煎餅果子,進而想到導師也是一個普通的人,應該也餓了吧,而深嵌在心靈深處的那盞燈,此時又浮現在作者的腦海中……
(二)老錢的“燈”
“我常常首先倡議解散,因為我知道人走茶涼之后,那支燈說不定要亮到寅時卯刻。”“只要它亮著,老錢就像著了魔似的翻呀,寫呀。寫魯迅,寫周作人。”“青黃的燈光”,它昭示了老錢孤獨、寂寞的求學之路,和古代的“青燈苦讀”不謀而合。不到生命的終止,就不會停止對學問的追求,這里的燈象征著錢教授安貧樂道、積極進取的人生態度,象征著錢教授孜孜不倦、勇于探索的治學精神。即使“混了50個年頭”,也“沒有混到一塊法定的私人居住空間”,即使是頭頂過早的禿了,依然無法減少其追求學問的熱情。可以說,“燈”見證了老錢的一生,通過對燈這個意象的描寫,將一個“苦行僧”似的學者形象——老錢,生動而豐滿的描繪了出來,這不得不說是作者在創作時充分抓住、運用靈感的結果。
(三)導航的“燈”
作者最后寫道:“燈嗡嗡地喘息著”“老錢是個普通人。但他的燈,亮在我心上”。這里明確寫出了老錢徹夜不眠,為人導航的人格力量。“每當我沖著書縫打呵欠時,不禁就想到:老錢大概還在干著吧?我再忍會兒。”老師的那種永不停息的奮斗精神,促使作者不停前進。“當我覺得白天之重和黑夜之輕都壓得自己難以承受時,我就想:去看看老錢的燈吧,順便吃個煎餅果子。”這里老錢的治學精神和人格魅力,已不是他自己的精神和魅力,而是變成一盞不滅的“燈”,指引著迷途的人,帶給他們一個心靈的港灣,它已成為以“我”為代表的青年知識分子的人生導航燈。
當作者為表現導師那種孜孜不倦的治學精神而苦苦追尋一個恰當意象的時候,靈感的閃現幫助他解決了這一問題。前面我們提到,靈感是在作家進行藝術構思時對意象的選擇進行重新組合與銜接,能夠恰如其分地表達作品的主題和突現人物形象。孔慶東在《老錢的燈》中對“燈”的描寫,從作為一般意象的“燈”到象征老錢治學精神的“燈”,再到象征著徹夜不眠為人導航的“燈”。“燈”的內涵不斷深化的過程,充分體現了靈感在創作過程中的閃現。在靈感降臨時,作家進入了一種最佳的創作狀態,他借助“燈”這個意象將作品的主題表現得淋漓盡致:通過對自己的老師錢理群教授宿舍的一盞青燈的贊美,表現了老師忘我的鉆研精神、執著的治學態度。同時,突出了老錢這個人物形象:平凡且偉大,德高望重且幽默風趣。讓每一位讀者都會對這樣一個治學嚴謹的知識分子產生由衷的欽佩之情,會被他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
三、靈感在語言表達中的作用
創作的最后一個階段是文學創作中“形之于心到形之于手”的階段,即表達階段[4]。當藝術形象構思成熟時,作家要運用恰當的語言把內心的藝術形象描繪出來。
用語言把作家心中的形象真實的描繪出來,實現已有的意象與語言的巧妙結合,靈感在此時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世紀俄國作家屠格涅夫,有一次曾為寫好一篇作品里的晨景而冥思苦想,當靈感來臨時,他感覺到了有什么東西推動了他,使他創作出了真正的美句“早晨的樸素的壯麗”。這就是靈感突致使意象與語言在瞬間形成的完美結合。我國著名的文藝理論家魯樞元感嘆:“文學的成果誕生在瞬間,文學的修辭是在瞬間完成的。(我)猜測著這里可能隱匿著文學言語的重大奧秘。”他接著又說:“這種‘瞬間修辭’可以看作‘言語在潛意識中完成的創造’。”[5]這種瞬間完成的組合,自然可以看作是靈感突現的結果。
“去看看老錢的燈吧,順便吃個煎餅果子。”這句話在《老錢的燈》這篇文章中,有著它特殊的含義:
“當我面對書本‘讀欲’不振時,當我獨望窗外無所事事時,當我覺得白天之重和黑夜之輕都壓得自己難以承受時”,休息一下,是理所當然的,“順便吃個煎餅果子”填充一下肚子,對于一個普通人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然而作為普通人的錢老師是不是也想吃個煎餅果子,他有沒有也想休息一下?“燈嗡嗡地喘息著”,這里以燈喻人,作者將無生命的事物擬人化,作為普通人的老錢也是會累的,但他依然“像一盤時間的磁帶在轉動”,在此作者記錄了老錢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艱苦治學精神。錢教授不顧身體上的疲憊和饑餓,依然堅持著對學問的鉆研與追求。通過對“煎餅果子”的描寫,作者將老錢物質上的樸素追求與精神上的高雅追求形成內在的反比,更加突出了老錢精神追求的可貴。“吃個煎餅果子”是作者靈感閃現時的執筆一寫,它是全文最大的亮點,看起來很平常,實則是令人回味無窮,這時作者將積淀在心靈深處對老師的景仰之情,全部釋放了出來,實在是令人叫絕。
靈感如火山迸發,所謂文思泉涌也許是這一現象的最佳注解。沒有“踏破鐵鞋無覓處”的辛酸,就不會有“得來全不費功夫”的靈感,正是這種鍥而不舍的追求,才能迎來靈感的降臨,這是深度思考的智慧結晶。
靈感,作為一種創作中的思維現象,激發出創作的沖動與因由,又繼而統馭寫作全程,并流溢出許多優美、意蘊豐富的語言。《老錢的燈》中的“煎餅果子”讓我們難以忘懷,它使我們體會到作為學生對老師的那份景仰與尊重,也使我們感佩錢教授嚴謹的治學精神,更使得我們對這篇美文中隨處閃現的靈感之光有了深刻的體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