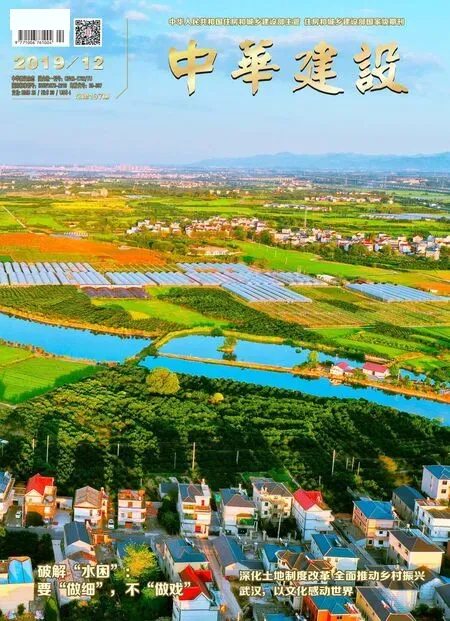世界的結構 慧眼中的世界讀《建筑的永恒之道》
Samuel

“借我借我一雙慧眼吧,讓我把這紛擾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這是那首曾經紅極一時的《霧里看花》中的歌詞。雖然我不喜歡這首歌,但是歌詞卻印象深刻。確實,世界太大、太多樣,而且變化太快,我們享受世界的精彩,同時也不得不面對內心的困惑,甚至我們產生了懷疑——以我們有限的心智是否能夠認知變化萬千的世界?
確實,我們無法了解事物形態上的所有變化,但是我卻有可能認知這些變化背后更加深層的、穩定的實質。萬變不離其宗,通過理解這些實質,我們可以從容應對各種變化。而我的這些自信源自這樣一個事實——我們的世界有一種結構。
所謂認識某種東西的結構通常意味著我們“希望簡單的勾畫它的輪廓,把它作為一個整體來理解”,“這也意味著,一旦可能,我們將用盡可能少的要素勾畫出這一事物的簡單圖景。要素越少,它們之間的關系就越豐富,這些關系的‘結構’中所展現的圖景就越多。”
關于世界的結構思索其實在幾千年前就開始了。我所知道的經典理論有兩種。一種是哲學意義上的。例如,古代中國人認為世界具有由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構建的基本結構,元素之間的相生相克是世界的基本秩序,形成了世界的運動。歐洲人有相似的理論,不過元素的個數減少了一個,包括風、水、火、土四種。另一種源于對微觀世界的觀察——各種物質都由種類十分有限的簡單基本粒子構成,在現代科技基礎上的這個發現竟然與兩千多年前偉大的古希臘唯物主義哲學家德謨克里特的原子理論驚人的相似。
然而上述兩種理論都還不夠。首先,那個優雅哲學上的結論太過抽象,將其映射到實際過程中還需要補充大量的信息。雖然經過幾千年智慧的積累,我們已經能將其應用于一些領域,例如五行說在中醫領域的應用,但要將其應用拓展于新的領域卻非常人能力所及。另外,微觀世界中,物質結構理論的應用范圍也有很大的限制。畢竟宏觀世界遠沒有微觀世界那么單純,我們如果嘗試著尋找直接構成宏觀事物的基本粒子,結果也只能是令人沮喪而已。
但是,Alexander在《建筑的永恒之道》中提出了一種觀察世界結構的新視角——模式的視角。何謂模式,Alexander并沒有給出定義。我理解所謂模式是一種模型,是對同一類事物中反復出現的、足以刻畫該類事物特征的特質的抽象。
具體到建筑學領域,模式表現為兩種關系:一種是其作為一個局部在更大的整體中,與其他局部之間的關系;另一種則是其作為整體本身,組成它的各個局部之間的關系。我們以“門”為例來進行分析,第一種關系表現為:門分隔了兩部分空間,并且為兩部分空間的連通提供了一個連接點,通常這個連接點是可以開啟或者關閉的。第二種關系則表現為:組成門的門框、鉸和門扇之間的關系。雖然門千變萬化,各不相同,但是門的模式卻是相對穩定的。我們之所以認為眼前這個東西是一扇門,并不取決于它的顏色、形狀、材質、大小,而是我們看到的這個物體確實在一個更大的整體中起到了兩部分空間連接點的作用,以及該物體由上述若干局部按照一定的關系組合在一起的事實。正是刻畫這些關系的模式才揭示了門的本質特征——我們根據這些特征來識別是否為門。再進一步分析,我們發現門中的那些局部又由更小的局部所組成:門框由柱、橫檔、鉸榫、線腳等組成,門扇由挺、橫檔和板組成,鉸由葉和釘組成……顯然,門中的每一個局部(門框、鉸和門扇)還是模式——識別門框同樣是依據上述兩種關系。如果不斷地分解,我們發現所謂構成各種建筑的元素,其實并非實體,而是關系,這些關系是構成建筑學領域中所有事物的分子、原子、原子核、電子……
而且,這些模式是數量有限的。建筑五彩繽紛,但是構成建筑的元素(模式)卻數量有限,Alexander在《建筑的永恒之道》系列叢書的第二本《建筑模式語言》中列出了二百多種模式。
如果所有的建筑都是由數量有限的模式結合生成的,而又正是這些模式賦予了建筑的特征,那我們就很容易得出一個令人振奮的推論——好的或壞的建筑源于它們之中蘊含的好的或壞的模式。因此想要建造好的建筑就可以采用這樣一個辦法 ——發現、收集或創造好的模式、清楚地描述這些模式、定義模式之間的關系(也就是建造一個模式庫),然后再應用這些好的模式來建造建筑。雖然建造模式庫的工作可能難度比較大,需要大師深邃的觀察與思索;但模式庫一旦建成,那么無數的人都可以加以利用,建造出無數美妙的建筑。這不僅僅是一個經驗、知識或靈感復用的理論,它已經成為了事實——Alexander花費數十年打造出了一個這樣的模式庫(《建筑模式語言》),并且還利用它完成了建筑的實踐(《俄勒岡實驗》)。
《建筑的永恒之道》絕不僅僅適用于建筑,其中的方法、思想,尤其是模式的思想已經被遷移到了軟件工程領域。設計模式就是這種遷移最成功的案例。
推而廣之,其實我們的生活中到處都可以發現不斷重復的模式。比如音樂中有模式,協奏曲中的模式:快——慢——快的結構。又如:流行歌曲中的模式:先有一段節奏比較緩慢的鋪墊,然后進入旋律清晰、易于記憶的副歌;通常副歌第一遍演唱是不會有太多修飾的;整個唱完一遍以后會再從鋪墊開始重來一遍,歌詞可能重復也可能不重復,但是第二遍進入副歌后,副歌可能會反復出現幾次,而且演唱時出現越來越多的修飾;在歌曲快要結束時曲終奏雅。再如:無論是古典音樂還是流行歌曲中都曾出現的,我稱之其為“海上風暴”的模式——波浪從遠處漸漸形成,近處風平浪靜,但是你可以隱隱感覺到遠處有一種力量正在聚集。有時候你會經歷一個小高潮,不過很快它就過去了,你了解,更大的風暴還在后面。你緊張地等待著,感覺到有一種力量在背后不斷推你,使你充滿期待、緊張地等待著,直到那一刻排山倒海般到來——你的心門一下子被巨大的力量撞開,感覺每一根汗毛都顫栗起來,甚至淚流滿面……想想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或者那首“人鬼情未了”,迥然的音樂,相同的模式。
為什么偉大的音樂作品中會出現相同的模式?因為這些模式是好的模式。因為它們順應了人們的行為模式——試想如果沒有鋪墊,上來就直接面對那些排山倒海,你可能無法被感動,人的感情、思維就需要那樣一個鋪墊的過程。就像Alexander說的,建筑中好的空間模式,一定是與人的行為模式相匹配的。
以模式的視角看待這個世界,我們就擁有了一雙慧眼。我將嘗試用這雙慧眼來觀察身邊的一切,才短短幾天,我就仿佛已經看到了不同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