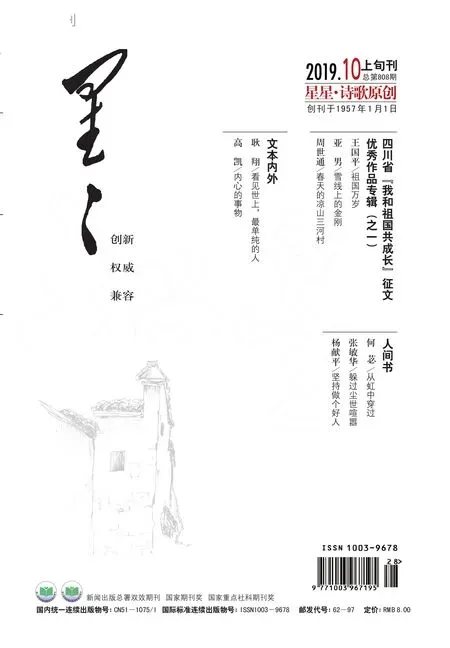故鄉活著的木犁(外二首)
2019-12-29 09:56:10郭茨斌
星星·散文詩 2019年28期
郭茨斌
從前朝投遞下來的一個名詞
像平置的阿拉伯數字
它孤單地倚靠老墻邊
仿佛等著在光陰的廢墟上生銹
等著螞蟻和蟲子把家搬上來
等著打工的小主人回來慰藉
活在郭家灣的最后一把木犁
被共同村留存下來
和木耙,牛軛
以及先輩們披過的蓑衣
共同為農耕文化做證詞。面對我
這個背井的家鄉人,它緘默不言
像是對著我素描,臥雪眠霜
蝴 蝶
穿花衣的女孩,獨自
坐在春光的指尖上,讀書
讀到藍天,高興得扇動幾下翅膀
讀到白云,飛起又原地落下
讀到一條河流把岸邊的落花帶走
她淚光閃動,仿佛懂得什么叫憂傷
眨眼就看到夏至了。她還在讀
認真的模樣像守在地角的一株胡豆花
目不轉睛,讀那伸出小手的麥穗
笨手笨腳地編制小草鞋
雪
清明。一片灰蒙蒙的愁云跟著我
心的方向,向南,向先祖居住的半山坡
母親提前
把多余的雜草和蜘蛛網清除
郭公王母
郭公魏母,郭公張母李母
她們的名字瞬間映入眼簾
在墓碑前,我和弟弟
把打成捆的哀思一沓一沓點燃
青煙空茫,依然無法抹去的悲傷
就像父親轉身離去的那個秋天
突如其來的一場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