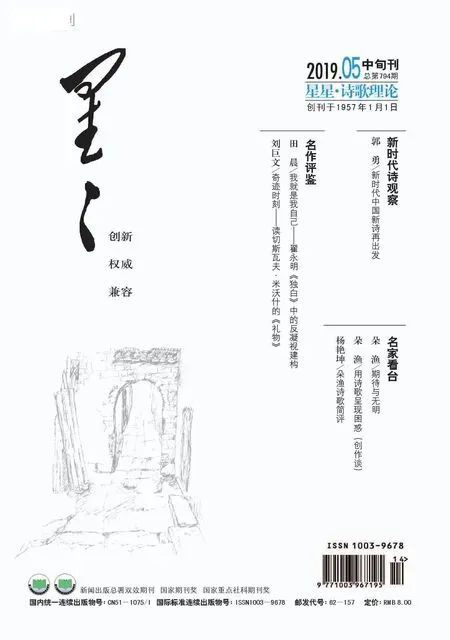從與詩無關到超驗精神與無窮盡
■ 趙 依
論及詩歌中的神秘、隱蔽和燃燒的聲音,首先要承認其無法窮盡的精靈族群。若將詩與思類比并訴諸哲學探討,人們在引渡并自困于他者之前,首先要慶幸危機的存在:沒有危機,便無從探討;沒有真正的問題,便不需深刻思考——唯其無窮盡,人方能永遠追索并不斷與詩“附體”。毫無疑問,這種聲音包含詩歌本身及與詩無關的一切。諸如,詩歌的繁盛意象之激活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交互譯介;詩歌的分行及結構性,又有長詩的內在嵌套和呼應循環,短詩、超短詩和截句問題;詩歌語言的現代化轉變及其對駁雜現實的紛繁觀照;理論批評與之所溢出的哲學性、現實性及其對所根植的歷史和政治等復雜背景的上下超越……
這一切又處于不斷變化的某種傾斜之中,歷經全然的現代派影響和徑直的反傳統,目前中國詩歌已在對西方現代藝術的傾心過甚中重拾古典美學和傳統韻味,新詩潮更為開闊,而這又與世界不再阻隔的整體性相適。中國詩人心靈深處回響著深遠文明和詩學傳統的召喚,連同現代意識和生活的再造再鑄,一并為新詩“起興”。
作家作品及所涉藝術的方方面面都無法擺脫深層的文化心理,以剖析與再現為意圖的詩歌創作不勝枚舉,其中又不乏以“原”冠名的本體論,其主要涵義同時指向中國新詩的青春和成熟化。鼓涌著的藝術更新自有其無窮的力量,正如理論批評伴隨著新詩的誕生與發展,與詩學形態緊密相關的焦點問題(詩歌現代化、詩體解放、語言自由等)的梳理辨析,同屬當代詩歌的現代化進程,而社會、物質、文化等諸多重要層面,與詩的演變及其詩性精神互為表里。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新詩的審美性是否需要標準而標準為何的問題仍然值得在當下展開更為開闊的討論。敘事詩、抒情詩、史詩等,又或是自由體詩的散文美,新詩的美學品格及具體作品里蘊含的美學視角顯然與其他文學體裁的藝術風格演變交相輝映。而詩歌與小說、散文的文體特征乃至其他文學傳統在不同程度上的通約和互動,也是中國當代文學整體性的重要表征,其超驗精神還指向思想與藝術如何平衡、現實主義主潮與新詩美學觀念的趨向、現代社會的時代意識和經典化原則等文學母題,相應地,也催生了各自思潮史的研究和新的理論框架生成。
詩歌語言上,自白話取代文言并沾染西方語法始,舊詩藝術規范一時被徹底打破,而新的規范卻遲遲未妥,卻為后來者時時提供警醒,也是一種持續的批評借鑒之聲,而“破”與“立”的矛盾統一也成為新詩的核心藝術糾纏之一:一旦有確定的權威和規范,便即刻要面臨新“聲”對其的挑戰和取消;一旦有新“聲”的昌明,隨即便要招致權威和規范的合法追溯與價值判斷——如此“方生方死”式的糾纏或可被轉于詩意地詢問:如何以一種兼及自我、他性和跨文化的神話思維來感悟當下與未來?
正如詩歌語言的透明與幽微,在異常艱難的歲月里,中國人在思考救亡圖存時,也在設想詩和文學的變革大略,現實和文學兩個層面緊密地、甚至互為因果地同步化、一體化。如今,則幸有無數選擇的可能和無與倫比的包容度,連同因之廣泛覺醒的個性化意識,一齊加劇了好詩標準討論的懸而未決,而反復的討論嘈嘈切切(如同詩歌朗誦本然的眾聲喧嘩),似乎也喧賓奪主為一種力量源泉。此即,詩與文學的現實向度與境界祈向。不論是古典的“詩言志”“詩以載道”“興觀群怨”,還是新詩對人和藝術之自由的“活”的執著,詩之為詩的超驗精神總是使其成為文體試驗的先鋒和先鋒本身。
科技發達的當下,人工智能又發先聲,AI寫作已涉及新聞、簡評、提綱乃至文學領域的詩歌和科幻小說創作。過去的科幻小說里有層出不窮的機器人寫作橋段,如今,這些舊日的“先鋒”早已過時為“現實”之一種,并由此衍生出科技現實主義和科幻未來的文學新命題。
——詩歌將如何在這些新生命題中唱響?
——用超越的詩心去觀照,從詩性的高度去實現,應是當下詩歌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