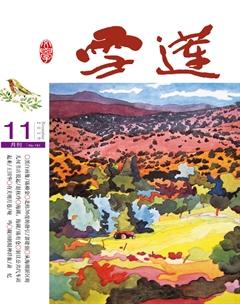別讓公共汽車站起來
一輛公共汽車夾雜在車流中間,浩浩蕩蕩地匍匐前進。道路兩旁高大的榕樹各自向中間側著腰身,攏成一個濃綠的棚頂,長長的望不到頭。
新能源電動公交車的噪音很小,悄沒聲地啟動,行進,停下來。再啟動,再前行。車流如見縫插針的水,穿過高樓大廈,拐進偏僻的小巷,然后進入一條長長的隧道。前面后面都是車。它們呈淹沒之勢,洶涌而來。然而車道上的公交車開著開著突然就剩下了自己。其他車輛全部隱去,似被陰影遮蓋。這輛車不肯按部就班,隨波逐流,越走越明亮,仿佛被打上了光環。光環越來越重,讓公共汽車變得越來越大……
車流中的任何一輛,都可能成為這凸顯的一輛。我只盯住了其中那輛公交車,感覺那輛車變成了我。
公共汽車是極富詩意的一種事物。它的平常性、世俗性、不確定性和憂傷,為這個城市鋪上了一層底色,讓這個城市的人生動起來。每天只要看到它,我陡然感到,這是我的城市,這是我的一天。
深圳的樹真多,排兵布陣般站到道路兩旁。榕樹、紫荊花、異木棉、鳳凰樹,三百六十五天總有花開。紅的,黃的,粉的,藍的,走馬燈一樣隨著季節此消彼長。它們伸出長長的枝條,時不時擦碰著倏忽而過的公交車,似乎要攔住它。是公交車欠了它的錢,還是它要和公交車說些什么。或者,這僅僅是個玩笑?那些樹在路邊空空地度過了一個又一個白天和黑夜,十分寂寞。它們和鳥聊過天,和天空交流過季節轉變時的陣痛。如果某一個晚上,一輛公交車拋錨在路邊,周圍的樹是否會湊過來一起跟公交車聊聊。和這些一輩子不動地方的樹比起來,公交車真算見多識廣了。它的每句話,每個見聞都會讓樹枝驚呼不已。
依然沒離開這條路,還是冷熱不忌地站在這里。獲知了外面的世界,心態就不一樣了。在天亮之前回到原位,它們的葉子中間除了鳥糞還有故事,自身有了重量。等它們去世的時候,就可以無愧地說,我是一棵有故事的樹。
樹的下面是等車的人。
我寫過一首詩。《傍晚》:老人點起一支煙,吸一口/遞給坐在對面的老人/石凳托著他們倆/大樹下,夜晚彌漫起輕霾/候車亭燈光暗淡/十幾個年輕人站在馬路牙子下面/各自低頭看手機/吱嘎一聲/公交車關掉遠光燈/下來一些人/上去一些人
這首詩中,我是個旁觀者。年輕人是十幾年前的我。石凳上的老人是若干年后的我。我介于他們中間,乘著公交車,從我的青年走向我的老年。
公交站臺已不是人來人往的地方。平時坐公交的也沒幾個人。公交車大搖大擺開過來,打開門,一個上車的都沒有。司機也不尷尬。這個流程不能省略,必須過一遍,關上門繼續開。我經常可以看到空空蕩蕩的綠色公交車在街頭落寞地奔跑。
一天中只有上下班高峰期才會擁擠。
外地人第一次到深圳,公交站點長長的等車隊伍也許會給他們一點點震撼。人潮蜿蜒著,神龍見首不見尾,從地上排到天邊。我親眼看到一個人從地下走到天上。
排隊是個好習慣,它的內核稱為“文明”。等大家從大驚小怪到視之為常態,文明也就浸入骨髓了。基本的生存越來越不是問題的時候,人們自然就越來越區分行為上的差別。
文明是表現優越的一種姿勢。你火燒眉毛一樣,左顧右盼,心神不定。我的從容不迫可以襯托出你是個土老帽,讓你自慚形穢。哪怕你穿著和我一樣的西服,系著同款的領帶。排隊時各自的神情和心態,已悄無聲息地展現出彼此的不同。
猶記當年在北方C城,離下個站點還差一站地,售票員便急吼吼地喊,某某站快到了,要下車的乘客提前到后門等候。如果不配合他做出一副著急的樣子,而是不緊不慢往后門挪,脾氣暴躁的司機就會破口大罵。有一次,因為售票員推搡懷孕的妻子,我還跟那個蓬頭垢面的年輕人干了一架。后來派出所處罰了售票員并向我們做了賠償,但這一架在我身體里生成了記憶,固定了我的公交思維模式。
到深圳后第一次乘車還是急急忙忙往后門趕。司機提醒,不要著急,等車停穩再下車。再看周圍,幾個乘客麻木地瞅著我,給我一股無形的威壓。心想,露怯了。
這里的公交車司機更注意安全問題。萬一磕碰,司機是要負責任的。他讓我感受到另一種生活方式,在北方那種集體焦躁之外的生活方式。
排隊的長龍一點點按比例剪短。但七點四十分左右,隊伍忽然一陣騷動。大家都看著表,掐著自己的時間呢。有的八點半打卡,有的九點打卡。公交車正常行駛半個小時,高峰期一般會堵上一陣,延遲十分鐘到二十分鐘。這一趟趕不上,下一趟一定晚點。隊伍迅速由長變粗。車剛停下,乘客一哄而上。手、胳膊和腰暗暗使勁,以期把別人擠下去,把自己撐進來。他們還是忍住不暴露動物本性,可已經產生的不安,必須通過擠壓才能釋放。人的伸縮性此時體現得最為明顯。只要三四個人同時屏住呼吸,就能擠出一個人的位置來。
最后所有的人都擠上去,無一剩余。整個車廂好像鼓了起來。
這一趟車走后,排隊的長龍一下子消失了。再來,便是零零星星的人。兩三個人懶懶散散地繼續排著一兩米的隊,恢復了文明景象。
按常理,晚高峰應該重演一次長龍變粗,但文明表現出更強的韌勁兒。畢竟回家早晚是自己的事,不用打卡,大家都不這么著急了。能等下一輛就等下一輛。
坐在雙層巴士上,立交橋仿佛離頭皮只有十公分。兩側的車輛都矮了很多,霸道的SUV也成了小爬蟲。平日需仰望才見的芒果樹上,掛著一個個堅硬的,隨時掉下砸到人的水果,現在看則是可憐巴巴地吊在那里。我只要輕輕一吹,它就會掉下去。
一朵接著一朵,串成粉紅花環的簕杜鵑也變低了。昨夜一場雨,簕杜鵑的花萼里積了一小汪水,此時正一點點“滴下去”,若是站在路邊,看到的是“滴下來”。
原來高處的事物,現在都一覽無余,溝溝坎坎只是溝溝坎坎,并沒那么多心機,也不再咄咄逼人。看清這一切,我便發現過去那些日子的斤斤計較和絞盡腦汁是多么可笑,公交車拐一個彎兒,那些曲折就不見了。即使當時不糾結,事情也會迎刃而解。
其實只是高了一米多一點。這一米多確是另外一個世界。就像姚明和曾志偉,同時眺望,看到的分別是兩個遠方。
那個巨大的廣告牌,確定無疑是深紅色,這會兒在陽光的照射下發生了變化。正面看到的亮麗,側面是清淺,背面是陰郁,公交車繞過了它,仿佛繞過了一個世界。早晨的陽光和中午、晚上的陽光又不一樣,它們把不同的表述投射到任何一個物體上,命其一天到晚變化不斷。
密密麻麻的樓房,也不復原來的樣子,此時成了一個純純的建筑物。里面住著的那些人,那些人的故事,恩恩怨怨,愛恨情仇,都被這連綿的建筑物淹沒到忽略不計。這些建筑成了一個個頗具文藝范兒的作品,被誰創作完成,擺在這里,還刻意修理了一番。刷上另一種顏色,就是品質升級;上面加幾個小小的雕塑,就成了另一個品種。
等紅燈的時候,車上的人可以感覺到公交車輕輕的震顫,仿佛一匹長途奔襲后暫停下來的馬,身體不由自主地發抖。一只螞蟻也會顫抖,但沒人看得到。越是巨大的事物,哪怕是輕微的震顫都能傳染給接觸到它的人,以致乘客都情不自禁地輕顫起來。
我在公交車里,道路上的事物裝飾了我的畫面,一幕幕像過電影似的。我閉上眼,他們依然在我腦子里流淌,進入我的心里。
我可以看到那些一邊走路一邊低頭刷手機的人,眼看就要撞到樹上了,一拐,很自然地繞過去。他的腦門上像是長著第三只眼,可以引領他走向目的地。這個世界上的人,腦袋上都長著兩只眼,他們不靠兩只眼睛領著回家,而是靠第三只眼。他們行色匆匆,神情恍惚。累了一天,腦子要休息了,眼睛也閉上了,但那只眼睛神一樣引領著他。無論是看手機的時候,騎共享單車的時候,都像公共汽車引領乘客一樣。他們在公交車外面,卻似乘坐了一輛無形的公交車。
還有迎面而來的電單車。電單車上的人,大多四五十歲,胡子拉碴,也有頭發蓬亂的婦女,他們都眼神僵硬,在機動車道上迎著公交車或者私家車就直接開過來。公交車并沒有停下的意思,一眨眼,公交車和電單車各自沿著自己的方向走了。沒有看到爭吵。沒有文明和野蠻。沒有規則和違規。
他們的心里長著第三只眼。
我看到,一個山頭挨著一個山頭,深圳的山真多。公交車剛才還在繁華的大都市里穿梭,轉眼就是一個山嶺。山嶺舉著一棵一棵的樹。它們被抬得那么高,自己都不好意思彎腰,一個個站得筆直,聚成一團,直沖云霄。
有的私家車在公交車道上奔跑。公交車專用道用黃色實線框定下來,上下班高峰期禁止其他車輛使用,跨線者輕則罰款,重則扣分。私家車沖進來,或許是車主要拐彎,或許干脆就是走神了。他意識到自己走錯了路,想拐回去,已經被其他車輛擠住,只好慢悠悠地在公交車前面晃。公交車司機使勁鳴笛,依然趕不走那顆釘在馬路上的蒼蠅。
公交車繼續開,到了海邊。海風吹著,骯臟的水上冒著氣泡。這個濱海城市,適宜游玩的沙灘非常少。只有一個叫作大梅沙的地方,平時人擠人,人挨人,比公交車上的人還多出很多。大梅沙就像一個晃晃悠悠的公交車,無論多少人,搖一搖,都能把這些人均勻地擺布在沙土了。
車廂里上上下下的那些人,我和他們本沒關系。我看見了他們,他們就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水過也有痕,風過也有痕,眼睛的一次恍惚,心里的輕輕一個顫動,眉頭的一次緊皺,都是一次記錄。怎么能說無痕呢。甚至,那些從無直接交集的事物也會給我留下印痕,我全不在意。只在若干年后的某一天,它忽然跳出來,閃閃發亮,仿佛老朋友一般。
公交車司機是一個。他一輩子以后腦勺示人。沒事的時候不會回頭。我分辨是否昨天的司機,只能依據其頭發顏色和多少。即使他的親人上車,也只能看到他的后部。平時都是臉對臉的,熟知其眼耳鼻口,此時看到親人的后腦勺,就像看到了他的隱私,看到了他最脆弱不設防的一面。心里應該有一點點的心疼吧?
而坐在駕駛艙里開車的那個司機還是昨天的司機嗎。如果是,還是去年和前年的司機嗎?
座位總是固定的。司機卻要倒班、輪崗,要退休,也可能遭遇各種波折和變動,他們看似堅固的地位,隨時都會被別人取代。
他掌握了別人的方向,自己的方向卻不一定能把握。取代他的人,每天做著和他同樣的事,握著同一個方向盤(有時也需把方向盤上的套子換一下,洗一下),到了同一個彎路,都要打方向盤。遇到同一個經年不做修整的水坑,都要減慢速度,輕輕顛簸一下。在同一個路口,等同一個紅燈。新任司機肯定有自己的個性,而在這些條條框框里,前任后任要遵守同樣的規則。前任和后任的輪換,對于行走這件事幾乎沒有意義。
開車的人都變了,其他的還有什么人不能變呢。車廂是一個載體,所有的人都在變。司機在變,乘客在變,甚至公交車也要以舊換新,不變的只是一條條道路,把人引向既定的遠方。
哦。道路也要調整。有幾次,我被改換路線的公交車拉到了本不想去的地方。下車后,我像小時候迷路一樣,心里蕩起一絲小小的惶恐。
乘客萬事急不得。有人發現錯過了站,讓司機停車,就近下車。司機不同意,乘客便痛罵司機。他忘了,自己在公交車上是無法選擇方向的。司機才有決定權。既定的道路,既定的速度。你的計劃違背了這個規則,就要自己承擔后果。急性子的我,從不跟司機較勁,就像我從不跟飯店服務員、街頭菜販較勁一樣。
我注重規則,只要乘車,無論大巴還是自駕,上車第一件事就是找安全帶。有一次去大禮堂開會,坐在連排椅上,也下意識地找安全帶。公交車上是不配安全帶的,讓我常常覺得不安全。對安全帶有了依賴,對司機和道路都快信不著了。
夏天的熱特別匹配公交車車廂里的冷。不知他們為什么把冷氣開得那么低。一上車,整個身體的汗毛都松了一口氣,聳了一下,然后又閉合上了。避免冷氣大批量浸入骨髓。下車之后,冷肉被悶熱的天氣灼一下,就成了非常舒服的溫和。從公交車上下來的人,伸一伸胳膊,個個都是一副心曠神怡的樣子。
兩只蚊子在車廂里嗡嗡響。深圳一年四季都有蚊子。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它們依然不會被凍死,但覓食能力減弱,或許也進入了冬眠。它們躲在被褥下面,花瓶下面。有一次我打開一本書,蚊子居然從封面和扉頁之間飛了出來,在我面前晃了一圈,不情愿地走了。它也許正在讀作者寫給我的贈言,讀了一半,被我打擾了。
南方蚊子比北方蚊子要狡猾得多。北方的蚊子都是傻大憨粗的,平時就呆愣愣地站白色的墻壁上。吃飽了人血之后還趴在那里。用書一拍,墻上鮮血亂濺。南方的蚊子叮了你一下之后,躲到你看不見的地方去消化了,他們速度快,反應敏捷,善用保護色,絕不和周圍的顏色形成對比。你很難找到它。
公交車里的蚊子似乎進入了困境。它們當初懵懵懂懂進入車廂,應該不是自己的選擇。車廂里這么冷,絕不適合它。但車廂內封閉性太好,它進來容易,出去卻不容易。車門一開一關,雖然是個好機會,但那個地方的人口流動性太強,它有點眼暈。
既然在公交車里面,就要叮人糊口。就要引起乘客的下意識反應。車座前后的人紛紛拍打,啪啪聲此起彼伏。這種零星的追打很難有什么結果。而乘客和乘客通過擊打蚊子,確立了彼此的關系。
蚊子風波過去后,他們就坐在那里,各自玩著自己的手機。唯一一個手托著下巴,靠窗做長久思考狀的,也是手機沒電了。
前后座的人,如果用快放的方式播映,一個站起,一個坐下,走馬燈一樣。
擁擠的時候,他和我呼吸挨著呼吸,皮膚挨著皮膚。轉眼我們就成了陌路。而我對此視若無睹。每天我有很多可能把陌生變為熟悉,絕大多數還是錯過了。如果拽住某一個陌生和它一起走下去,故事可能就由此展開,我的人生踏上了另外一條路徑。
上下班的公交車和旅游巴士性質不同。上下班的那些人多是沉默的,他們的話在工作時都說完了。面對自我的時候,他們不愿意再多一句話。不像旅行大巴上的人,熱烈地討論著,期盼著他們的前方。
開車的,坐車的,上車的,下車的,實在沒什么話可講。語音提示把該說的全說了:“大浪社區到了,下車的乘客請……”刷一下公交車上車,“嘀”一聲,自動扣費。
高峰階段,后面的人無法擠到前面刷卡,就遞給前面的乘客。前面的遞給更前面的,一直默默傳到緊挨讀卡器的那個人。刷完,再一個個傳回來,大家基本都不用說話。偶爾有人會問,這是誰的公交卡?主人能準確地接過來。那么相似的公交卡,像孿生兄弟,他們都能看出細微的差別。那個公交卡在他的心里已經印了多少遍了。
這些人回到自己的家里或者自己的生活圈子里,應該是生動的,或者是幽默開朗的。但整個車廂讓他們沉默了下來。被沉默籠罩著,想不沉默都不行。在這種沉默里,彼此都成了面目模糊的人。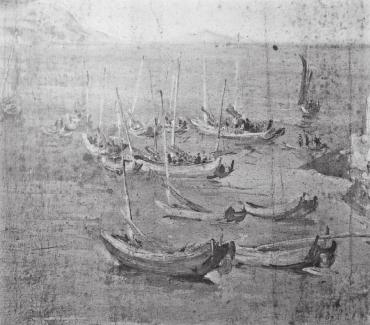
乘坐公交車的人,一年又一年,甚至一代又一代,換了很多人。越來越多從公交車出發的人,漸漸遠離。深圳的公交車乘客基本都是二三十歲,平時則是孩子和老人居多。一些老人喜歡在不擁擠的時候,坐上公交車四處逛逛。紅樹林、大梅沙,以及遍布全市的公園。公園都不大,很精致,一年四季的鮮花,不大的一池水,小亭子,水邊幾個嶄新的躺椅。老人們在這里找到了自己的通道。已經進入下行通道的人,正在學習走好下坡路的人,成了一道特殊的風景。那些行色匆匆的年輕人,還是風景的局外人。
最初被公交車拉過的那些人去了哪里?他們還會回頭看一看公交車,以及公交車上的這些人嗎?他們是有了其他出行方式,比如地鐵,比如私家車,比如干脆離開這個城市,還是坐著另外一個公交車,去了另外一個地方?
公交車貌似一個巨大的隱喻。這個隱喻是什么,一兩句話也說不清。深圳的公交車和其他城市的公交車一定有很多相似之處,但也有自己的獨特之處。以公交車為原點,這里的每一件事,每一棵樹,每一個陰霾里的灰塵,每一個高冷的白領和流水線上穿著統一制服的每一個工人,都散發著各自的氣息。他們被創新、“來了就是深圳人”、漂泊、上市公司、超高房價等宏大敘事籠罩著,努力地堅持著自己,哪怕這個自己異于那個固定的模式。他們的發散外擴,卻成為凝聚這個城市的最核心的氣質。
公交車拉著我。剛才還在寬闊的大道上行進,這會兒進入了一條幽深的小徑。在小徑的盡頭,我不知道有什么等著我,我只是跟著公交車慢慢地往前走,往前走。幽暗的陽光籠罩著公交車。公交車越走越深,似乎進入時間的隧道。
公交車拉著我去遠方。心中的不確定性漸漸生發、長大。如果我不知道公交車的起點和終點,隨便坐上一輛公交車,那么我就相當于把自己放到了大海上的一艘船,隨便跟著方向走。我沒有做自己的選擇,而是讓公交車替我做了選擇。我沉默著。是公交車司機把我帶向遠方,我相信他一定把我帶走,不至于遺忘在這里。他不會把我帶到溝里去,而是帶到一個明確的方向。
那個方向,我不知道,只有公交車司機知道。這仿佛是我們兩個之間的一種默契。他不說,我也不問。我們心照不宣,就像路上兩個人打一打招呼,彼此知道對方要說什么。
如果一輛公交車讓我坐上三遍,我便和它熟悉了。我知道它的每一個站點。每一個站點上,人多還是人少,高峰期有多少人,平常時段有多少人。我熟悉它就像熟悉自己有幾根手指頭,手指頭上的指甲有多長。這種熟悉讓我沮喪。我不再被陌生感覺攫取著,甚至可以躺在座椅上輕輕睡過去。睡多大一會兒醒來,都不用上鬧表,我的生物鐘已經自動調整好了。這種生物鐘會按時叫醒我。沒有陌生感和焦慮感,我就不會睜開好奇的眼睛打量窗外,打量窗外每一個可能出現的陌生和意外。
熟悉到這個地步,這輛公交車對我還有什么意義呢。我要的就是陌生和好奇。如果我每天走向它,跟隨著它,就像吃飯和睡覺一樣,那么它就不再適合我。我只是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而不是從一個熟悉到另一個陌生。我希望它讓我緊張,讓我焦慮,讓我惆悵甚至沮喪和痛苦。
當這些它都給不了我的時候,我只有再換另外一輛公交車。另一輛公交車會帶給我新鮮感。它像一匹飛奔的駿馬馱著我,在深南大道,濱海大道和北環大道上飛奔。它像一條泥鰍把我沉在生命中底部的東西攪動起來。激活它,讓我隨著時間舞蹈,讓我波瀾起伏,動蕩不安。
但另一輛陌生依然會穩定下來,變得熟悉。那樣我會怎么樣呢。再換另外一輛公交車。是的,我必須換另外一輛公交車。好在這個城市有無數的公交車可供轉乘,子子孫孫無窮匱也。然后它們行駛到一個我不熟悉的胡同或者高樓大廈,或者一片小樹林,或者一個地鐵口。那兒的人,我都不認識;那兒的建筑我也從沒見過。它們給了我激烈的撞擊,讓我渴望在這兒多呆一會兒。
我開始了另一個旅程,另外一種生活,雖然這種生活我還會熟悉下去的。
而事實上,我并不是一個樂于追求陌生和緊張的人。骨子里的我,很沉溺于現在的平靜。我熟悉的家人熟悉的朋友熟悉的地點,讓我頗感安全。我可以心無掛礙地睡去,做個不用大聲呼喊的美夢,然后懶懶散散地醒來。但是陌生和遠方對我的吸引卻永遠存在。我在鋼絲上跳舞,并非非此即彼。它和我現在安于的狀態并不違背。反而相得益彰。
它們兩個都在我的身體里。不打架,相互觀望,相互照顧,甚至相互幫助。它們是我身體里的兩個組成部分,構成現在的我。它們看到了過去的我,吸取了沉重的教訓和經驗。它們把現在的我打磨得更加完整。
小時候在農村,偶爾聽到牛馬騾子成精的故事。那些畜生天天和人打交道,吆喝責罵,鞭打腳踢,耳鬢廝磨,沾染了人的神氣,動物有一天突然講話,說出一番大道理,或者幻化成人,與主人及其親朋好友發生一段不可描述的故事。公交車每天接觸那么多的人,縱是無生命的鐵器,也會被這洶涌的人氣改變點什么吧?走著走著,公交車就成了一個自主行動的人,它自己認路。兩輛公交車,好像兩個傻大個兒,在窄窄的巷子里狹路相逢,兩輛車上的乘客幾乎只隔著一層玻璃,臉貼著臉。公交車并不減速,眼看就要撞上了,彼此側一側肩,刷地過去了。那時候我真能感覺到它們側肩的姿勢。
任何一種事物都具有神性。比如一個垃圾桶,你認真盯著它,遠遠地盯上五個小時,如果困了就打個盹,醒來接著盯著它。突然有那么一陣兒,一個人從里面走了出來。沖你笑一笑,向你越走越近,他穿過你的身體,又飄忽地走向遠方。他帶走了你的神魄。你以為自己走神兒了,不相信會有超出自己想象的事情發生,但你真真切切地感覺到他穿過了你的身體。
公交車只是平常的交通工具,對于某些人來說,每天都要走進去,走出來,感知不到公交車的神性。這種情況下,最好不要細想它,就這么每天渾渾噩噩,挺好。對公交車也好,公交車不用有什么負擔。
地鐵和飛速增加的私家車越來越成為大城市的主流。深圳的高速公路上都會堵車。逐漸被邊緣化的公共汽車,更凸顯了它的詩意。如果公交車一直是主流的,被追捧的,獲得的責備和辱罵肯定不少,它和責罵者一起在世俗的泥潭里摸爬滾打。如今因為被邊緣化,它的落寞,讓人產生不忍之心和懷舊之心,讓人在落寞的時候回身打量一下它,對照一下自己,便會同病相憐。
這個龐然大物,一輛輛爬行的動物。在一個明亮的早晨,或者擁擠的傍晚,突然站起來,像一個個奔跑的金剛,成為這個城市的敵人。路上的人四散奔逃。那該是一種什么狀況。
也許有這種可能。
【作者簡介】王國華,河北阜城人,現居深圳。中國作協會員、《讀者》雜志簽約作家,深圳市雜文學會副會長。已出版《街巷志》《誰比動物更凄涼》、《書中風骨》等二十部作品。曾獲深圳青年文學獎、冰心散文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