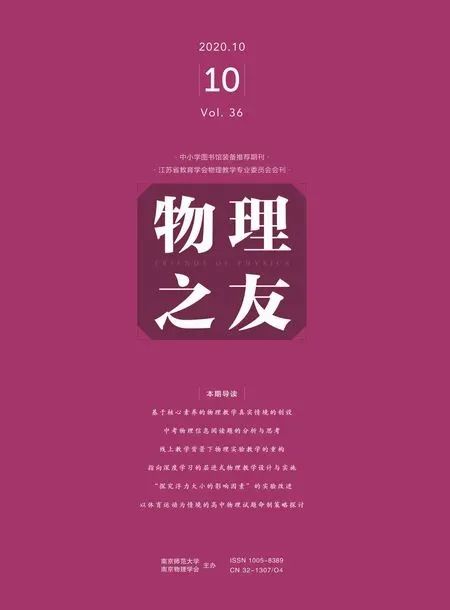建構思考框架 發展高階思維 ①
——以“萬有引力與航天”的習題教學為例
黃 皓
(江蘇省無錫市第一女子中學,江蘇 無錫 214002)
1 問題的提出
“萬有引力與航天”一章歷來是高中物理教學的難點,學生往往是一聽就懂、一做就錯,即便教師反復講解,情況也無多大改觀。教師的困惑是:解答“萬有引力與航天”的習題,無非是牛頓運動定律和圓周運動公式的應用,可學生解題如此困難,原因何在?
“萬有引力與航天”一章的教學困難起源于學生不能直達問題的核心,進而在遇到復雜問題時,無法調用高階思維,會一籌莫展。那么,破解之策又在何處?
2 高階思維沉睡的根源
高階思維沉睡的原因主要在于現行教學模式耗費了學生的大量精力去學習各種知識、技能,卻忽視了高階思維能力的培養,只學習知識而不深究方法,最終很可能導致思維窄化。
從雙基的角度來看,“萬有引力與航天”一章涉及的知識點并不復雜,問題是學生沒有真正理解知識點間的聯系。
當學生自己面對問題時,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是自問“以前是怎么做的?老師怎么做的?如果上述反應都得不到結果的話,基本上內心深處是在重復:怎么辦?怎么辦?學生無一例外在雙基上下了功夫,然而他們沒有或缺少足夠的機會去獨立分析、冷靜思考,從而放棄了與生俱來的強大思考能力。總的來說,教師磨練多年,見多識廣,所以面對各種常見問題時,確實可以“游刃有余”;然而一旦面對全新的情景,沒有可供模仿、借鑒的經驗,往往也會不知所措。從這個角度看,學生其實是教師的“鏡像”,筆者認為這就是“萬有引力與航天”習題教學困境的核心。那么,我們是否能夠喚醒、調用并發展沉睡的高階思維?答案是肯定的。
3 建構高效的思考框架
教師應該順應人腦的運作模式,建構高效的思考框架,幫助學生將需要解決的問題抽象、轉化成一種可以快速調用已有知識、技能的清晰指令,這套思考框架由以下三個步驟構成。
3.1 從問題表象中鎖定本質目標
例1:宇宙中存在由質量相等的四顆星組成的四星系統,四星系統離其他恒星較遠,通常可忽略其他星體對四星系統的引力作用。已觀測到穩定的四星系統存在兩種基本的構成形式:一種是四顆星穩定地分布在邊長為a的正方形的四個頂點上,均圍繞正方形對角線的交點做勻速圓周運動,其運動周期為T1;另一種形式是有三顆星位于邊長為a的等邊三角形的三個頂點上,并沿外接于等邊三角形的圓形軌道運行,其運動周期為T2,而第四顆星剛好位于三角形的中心不動。試求兩種形式下,星體運動的周期之比T1/T2。
分析:在習題教學中,不必急著給出解答的方法或正確的答案,而是先“鎖定本質目標”。對于例1,很多學生反饋說:題目太長,沒耐心看(問題表象)。針對這個問題,教學需要達成的目標是什么?縮短題目長度?很難做到也沒有實際意義。但如果教師回歸到學生的視角,順藤摸瓜分析下去,就會發現一個清晰的線索:學生看不下去是因為沒興趣,沒興趣可能是因為習題內容與學生已有經驗相關度小,教師授課時一般不會涉及四星系統;也可能是因為習題主題結構紊亂,原題沒有配圖、可讀性不足。
由此,教師應先找到真正需要解決的“目標”,理解學生的急切需求,改變切入方向,提升習題教學的邏輯性和實效。
3.2 用精準的語言傳達目標指令
筆者之所以強調“精準”,是因為從腦科學的角度來看,大腦是基于實體環境進化過來的,這導致大腦并不擅長處理模糊性問題,模糊、泛化的語言使人很難調用高階思維。為了調用高階思維,一定要用簡潔、清晰、無歧義的語言給大腦下達指令,當遇到的問題比較復雜時,最好能寫出來。
在習題教學中,教師都規范板演,對學生提出要求:明確物理情景,畫出草圖,選好研究對象,根據運動狀態選擇物理規律列方程。筆者在教學實踐中,在細化要求的基礎上再強調了一點:初學時必須在草稿紙上把它們寫出來,待熟練掌握后可口頭說明。操作次序如下:(1) 畫草圖。(2) 標出研究對象。(3) 明確運動狀態:是否為勻速圓周運動?軌道是圓還是橢圓?(4) 求出合力。(5) 根據已知條件選擇加速度的表達式。(6) 根據牛頓第二定律求解。(7) 檢查結果中各物理量是否已知。有了這些細化后的簡潔、清晰、無歧義的指令后,只需要從頭腦知識庫中調用最適合的技能、經驗(規律、公式等),即可有條不紊地完成任務。
有了上述流程,學生解題就有了抓手,不再盲目地等待教師給予,方向性錯誤得以減少。學生開始主動探索未知,能夠圍繞問題思考、推演,最終得出結論。較高的正確率給他們帶來了成功的體驗,會激發他們對物理的學習興趣。
3.3 推導關鍵執行項
對于實際問題,解讀出目標之后,緊接著要做的是:在資源、信息和時間受限的情況下,如何找到關鍵執行項?對此,腦神經機制的研究者給出了回答。不妨回溯史前社會中的原始人捕獵的方式,鎖定獵物(目標)后,獵人會先識別目標參與者并進行分析。分析內容的有:野鹿(目標)、獵人自身、外族獵人、猛獸、其他非相關獵物(比如兔子、小鳥,可能會提前預警、影響狩獵)。緊接著,獵人從最終目標逆向推導,綜合分析出捕獲獵物需要克服的主要障礙:(1) 野鹿的行為可否預測?(2) 弓箭的力量可否一擊致命?(3) 在有效射程范圍內是否會被察覺?(4) 周邊有無會搶奪獵物的威脅者(如外族獵人、猛獸)?
分析至此,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就不難判斷出達成目標的關鍵執行項。假設獵人對野鹿的行為特性很清楚,對弓箭的力量也有把握,那么關鍵執行項就是判斷有無搶奪獵物的威脅者。但如果獵人確認周邊沒有威脅者,但對弓箭的力量信心不足,那么,關鍵執行項就是盡量靠近野鹿而不被其察覺。
由此可見,對于同樣的目標,主體不同或者環境不同,關鍵執行項很可能完全不同。因此,如果需要調用高階思維,就必須順勢而為。
例2:一衛星繞某行星做勻速圓周運動,已知行星表面的重力加速度為g0,行星的質量M與衛星的質量m之比M/m=81,行星的半徑R0與衛星的半徑R之比R0/R=3.6,行星與衛星間的距離r與行星的半徑R0之比r/R0=60。設衛星表面的重力加速度為g,求衛星表面的重力加速度與行星表面的重力加速度的比值。
在解題過程中,首先鎖定目標:行星和衛星表面的重力加速度g的比值;其次識別目標參與者:星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g(目標)、行星和衛星的質量、行星和衛星的半徑R、衛星的軌道半徑r;再從最終目標逆向推導,綜合分析出與衛星的軌道半徑r相關的是衛星在軌道上的向心加速度an,它與目標無關;最后關鍵執行項自然就是應用“在星球表面附近,重力近似等于萬有引力”的結論,問題迎刃而解。
這樣的教學過程,能夠圍繞特定目標,思維維持在較高的認知水平上,需要有意識地付出持續的心理努力;解題不再是超量重復后的“條件反射”,保障了學生有所為、有所思、有所得,高階思維的發展也就落到了實處。
總之,當遇到復雜問題時,通常無法直接套用已往的知識、經驗、技能。但按照上述思考框架,即可喚醒高階思維,大腦得以直接調用知識、技能來解決問題,知識和技能隨之上升到經驗和思想層面,高階思維得以發展。
4 結語
當下爭論了多年的知識碎片、知識體系的問題,其爭論焦點從一開始就有待商榷。所謂“創新”就是在打破常規的基礎上產生出具有現實意義的東西,當真實問題出現時,它絕不會在你耳邊說:“只要用昨天學的知識甲和前天學的知識乙就能解決”。學生最欠缺的不是知識、技能,而是學會思考,學會調用高階思維、發展高階思維,這樣才能指導、保障、促進和改善我們的物理教育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