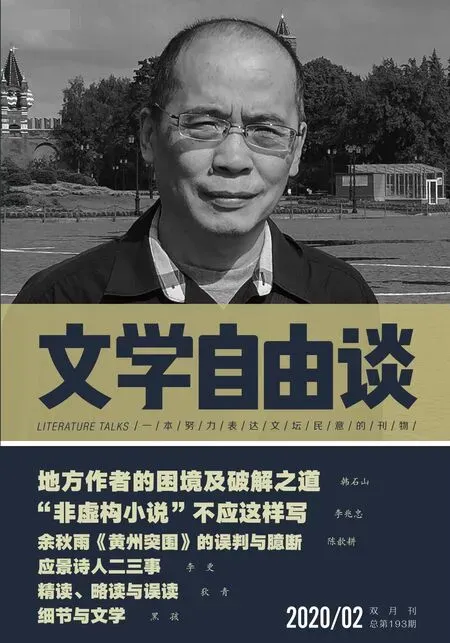赴一場遲來的生命之約
□南北萍
這個小年夜的晚上,收到張景云先生的散文集《秋語》。在思考中進入閱讀。沒想到,這一讀就至夜半,仍難釋手。
作品按《往事回憶》《激情歲月》《山水之間》分為三輯。第一輯《往事回味》中,撲面而來的是熟悉親切的生活氣息。《父親的眼神》《兒行千里》《夢里依稀慈母淚》等篇什中,那濃濃的親情回憶,首先吸引、打動了我。這是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從專業到業余,從大家到草根,有關文本可謂汗牛充棟,想跳出窠臼、寫出新意,殊為不易。景云先生卻以善感多思的敏銳、細膩,寫出了許多屬于個體記憶的獨特細節。如《想起父親》一文中,寫上世紀六十年代一個冬日的早上,當時只有幾歲的作者,因饑餓難捱,父親從帶著去上班的不多的干糧中,分出一份給自己。從父親掏出食物,放在他手上,又拍拍他的頭,說“慢慢吃罷”,到母親的輕輕嘆氣,哥姐的責備目光,這一連串的動作、語言、氛圍的描寫,讓日子的艱辛、孩童的懵懂、父母的慈愛躍然紙上。《兒行千里》中,初中畢業的哥哥為減輕家里負擔主動下鄉,追求進步的姐姐背著母親退了戶口去東北兵團,作者高中畢業應征入伍——伴著兒女一次次遠離的,是母親一次次送別的淚水和因牽掛而日漸的衰老。即使讀過再多與父母離別的文字,這樣“陽關三疊”式飽蘸情感的描寫仍會令人瞬間淚目。從回顧成長追憶親情的《往事回憶》,到十年軍旅步伐鏗鏘的《激情歲月》,這樣的細節可以說俯拾皆是。難得的是,景云先生既有“俯”的姿態,善于細細梳理檢視歲月深處的記憶,亦不乏細節取舍的“拾”的慧眼,最終落在對散文寫作至關重要的“情”字上,從而使自身的個體記憶、生命體驗與讀者產生強烈共鳴,為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庫又增添了寶貴儲存。
《秋語》加深了我的一個認知,就是一個寫作群體的悄然涌現。步入花甲退休之年的五十年代生人,進入天命之年的六十年代生人,是這個滄桑巨變時代的“黃金一代”。集體主義精神、國家社會的責任感和團隊精神的教育,是他們“三觀”形成的精神底色,很多人成為社會的精英骨干。他們經歷豐富,世事洞明,有學識、境界、襟懷,也在讀書與行走、生活與思考中形成了不乏個人魅力的性情、趣味,其中,少年時代因種種機緣在心靈埋下文學種子的一部分人,雖然在工作繁忙時只能把文學當作難舍的情人遙遙相望,但一旦繁務漸去,工作與生活漸趨塵埃落定,便會義無反顧,在人生之秋全身心投入,赴一場與一直鐘情熱愛的文學遲來的生命之約,這似乎已成為當下的一種文學現象。張景云先生無疑也是這樣的“赴約人”。
春華秋實,厚積薄發。書名取《秋語》,景云先生在書中敘述了其中一個原因:自己生在立秋之日,母親給起乳名“秋”。因而,這個書名對作者可謂意義獨具。我想另一重要意蘊,當是他人生之秋的一份收獲,一份與文學之約的遲來告白。于步入人生之秋的景云先生,這本《秋語》當是他文學創作的新的起點。在以個人回憶述往為主的資源寫作基本完成后,我以為,以景云先生靜水深流、善于觀察思考的性格特點,勤于閱讀形成的知識積累和人文素養,多年公務生涯磨煉的獨到眼光和思辨睿智,或許,以歷史的、現實的眼光與哲思,去感悟、思考、表達在讀書、行走中的發現,是景云先生揚己之長寫出經典佳作的方向。如《剽悍的蒙古馬》中對成吉思汗歐亞遠征軍通過騸馬、裂耳、犁鼻三大調馴馬術,使戰馬所向披靡的獨到描寫,解開了我對成吉思汗何以縱橫歐亞雄震天下的疑惑。歷史與現實中需要作家撥云見日去發現的實在太多太多,就景云先生的素養功力而言,這是我期待的寫作和閱讀,而其中最重要的,仍是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