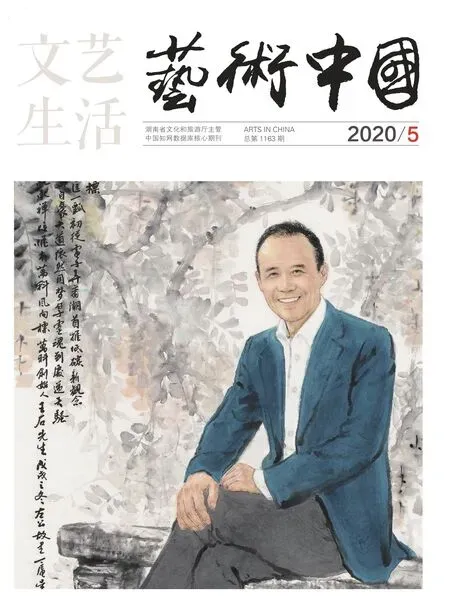試析書法創作中的“由熟到生”
◆ 曹鈺(山東 菏澤)
熟與生是書法美學范疇中的一對審美概念。董其昌提出“字須熟后生”的書法理論對書法美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那么熟與生的關系是什么?其意義內涵又是什么?在書法實踐創作中如何做到“熟后生”呢?
一、熟與生的辯證關系和董其昌的“字須熟后生”理論
(一)熟與生的辯證關系
熟與生,是同一物體在一定因素的促變下產生演進過程的界定語,用以表達一種對立而又統一的辯證觀念。追溯一下,佛經《龍樹菩薩勸誡王頌》曰:“自有生如熟,亦有熟如生。亦有熟如熟,或復生如生。菴沒羅果中,有如是差別。”
此頌中“生”與“熟”是相互超越的一對概念。佛家講要戒掉“貪、嗔、癡、慢”放下執著,才能做到真正的“定”,是謂“定能生慧”也。熟乃執著,生即為破除執著;熟后須破除熟之執著為生,生后須破除生之執著,相互轉化遞進,這正如佛家之進修功夫。熟與生之間互相超越再超越,是經過否定之否定的認識規律。書法對于中國藝術就像雕塑對于歐洲藝術一樣,包涵了中國的傳統思想和人文精神,藝術的發展大多又受宗教影響,熟與生逐漸被引申到書法理論中來,成為書法美學范疇中的一對審美概念。明末書壇領袖董其昌提出“字須熟后生”的重要書法理論,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董其昌的“字須熟后生”理論
1.董其昌提出與“熟”相對的“字須熟后生”理論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號香光,松江(今屬上海)人。出生于嘉靖三十四年,這一時間正處于明代中期,政治昏庸腐敗,生產力遭嚴重的破壞。到了明代中葉之后,資本主義萌芽出現,江南自然條件優越,農業、手工業都得到很大程度的發展,經濟十分活躍。董其昌的大部分時間即居住在江南,這里優越的經濟環境為其藝術創作提供了很好的物質條件。
董其昌以其疏淡、優雅、蒼潤的書法風格卓立于明末書壇,其《畫旨》上提出:“畫與字各有門庭,字可生,畫不可不熟。字須熟后生,畫須熟外熟。”從字面上看,即要求技法在熟練之后,再追求如初學時的那樣生。然而在明代之前的書評和書論中,大都是以“熟”“精熟”來贊美書家的書法造詣。如相傳為書圣王羲之作的《筆勢論十二章》首章談到:“始書之時,不可盡其形勢,一遍正腳手,二遍少得形勢,三遍微微似本,四遍加其遒潤,五遍兼加抽拔。如其生澀,不可便休,兩行三行,創臨惟須滑健,不得計其遍數也。”
此“如其生澀,不可便休”即如果臨寫生澀不能就此停下來。“不得計其遍數也”即不要算計臨了多少遍。可見王羲之要求學書須勤奮,臨帖要臨到精熟。唐孫過庭《書譜》中也說:“心不厭精,手不忘熟。若運用盡于精熟,規矩諳于胸襟,自然容與徘徊,意先筆后,瀟灑流落,翰逸神飛,亦猶弘羊之心,預乎無際;庖丁之目,不見全牛。”
既勤于用心又勤于動筆,同時做到這兩點是很不容易的,這是書法水平提高重要原因之一。不厭其精深,手要熟練,熟能生巧。假若運用過到了精熟的程度,規矩法則暗記在心中,就能達到自由發揮,進入自由王國。意在筆先,能使字寫得瀟灑、流暢、神態飛揚,這就像弘羊善于籌算,對事物預料得非常精確一樣,又像庖丁的眼睛,不看全牛,而全牛的每根骨頭的形態和應從那里下刀都暗記于胸一樣。
還有如歐陽修《試筆》中說:“作字要熟,熟則神氣完實而有余,于靜坐中,自是一樂事。”“熟”是一種功夫,書法作品想要達到“神氣完實而有余”就一定要在字法、筆法上熟練才行,熟是手段和必由之路。講到書家之書寫功力,大多都是講究要熟,熟是一種普遍認識的真理。至于生,則與熟相對,往往被加以否定。
2.董其昌為何卻提出“字須熟后生”的觀點呢?這可以從外因和內因兩方面來分析:
(1)外因即董其昌所處的社會大背景因素的影響
首先,晚明是一個尚“奇”的時代。如米元章說:“時代壓之,不能高古”,在這種文化背景下,可以說董其昌提出的“生”具有一種尚“奇”性。同時,董其昌又深受當時李贄“童心說”的影響。
李贄(1527—1602)明代文學家、思想家、禪師。以孔孟傳統儒學的“異端”自居,反對封建禮教。提出“童心說”, 所謂童心,其實是人在最初未受外界任何干擾時一顆毫無造作,絕對真誠的本心。如果失掉童心,便是失掉真心;失去真心,也就失去了做一個真人的資格。而人一旦不以真誠為本,就永遠喪失了本來應該具備的完整的人格。童心,即心靈的本源。主張創作要“絕假還真”、抒發己見、個性解放、思想自由。
董其昌《容臺集》中談到:1598年初,他在京鄰廟中與李贄邂逅,盡管與其地位、年齡相差懸殊,但兩人一見如故,并許為莫逆。李贄激進的歷史觀和回復真本心的希望使董其昌渴望自己能對藝術革新,去創作出自己的心意。
其次,是趙孟頫書風在晚明的盛行。古語有“物極必反”,一種藝術形式的極度流行,即使它完美無缺也會由于被濫用失去其典雅、端莊,加之晚明時代書畫市場的空前活躍更加劇了趙孟頫書風淪為流俗。董其昌《畫禪室隨筆》中指出:“米海岳一生夸詡,獨取王半山之枯淡,使不能進此一步,所謂‘云花滿眼,終難脫出凈盡’。趙子昂則通身入此玄中,覺有朝市氣味。《內景經》曰:‘淡然無味天然糧’。”
句中說趙書有“俗態”“朝市氣味”,可見,他對趙書的批判甚為激烈。書法作品最忌俗也,但趙孟頫畢竟是在書法史中有地位、影響的一代大家,不是輕易能夠動搖的。董其昌對趙書的批判,不如說是對當時趙書盛行以至淪為流俗現象的批判。師法古人工夫要深但不可以俗,即被古法束縛,沒有了己意。是董其昌對俗的一種批判。
(2)內因即董其昌自身在書法上的審美觀、創作觀
首先是,董其昌對傳統書法和傳統書法理論的理解。《畫禪室隨筆》談到:“大慧禪師論參禪云:‘譬如有人具萬萬資,吾皆籍沒盡,更與索債。’此語殊類書家關被子。米元章云:‘如撐急水灘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蓋書家妙在能合,神在能離。所欲離者,非歐虞褚薛諸名家伎倆,直欲脫去右軍老子習氣,所以難也。哪吒拆骨還父,拆肉還母。若別無骨肉,說什么虛空粉碎,始露全身?晉唐以后,惟楊凝式解此竅耳。趙吳興未夢見在。”余此語悟之《楞嚴》八還義。明還日月,暗還虛空。不汝還者,非汝而誰?然余解此意,筆不與意隨也。
相對于元代及明前期的復古思潮,董其昌對傳統的認識是獨特而又深刻的。董其昌借哪吒拆骨還父、拆肉還母的神話,表達了自己對傳統的認識和態度。第一,對傳統的繼承要建立在不斷創新、不斷豐富的基礎上;第二,提出“妙在能合,神在能離”的見解。離,別也;和,同也。因而董其昌推論出,形成自己風格的書法藝術才是學古的目的。《畫禪室隨筆》還記有:“東坡先生書,世謂其學徐浩。以予觀之,乃出于王僧虔耳。但坡云:‘用其結體,而中有偃筆,又雜以顏常山法。’故世人不知其所自來。即米顛書,自率更得之。晚年一變,有冰寒于水之奇。書家未有學古而不變者也。”
可見,董其昌找到了蘇軾和米元章書法的出處,并指出了其變化方式,對元以來書壇的領袖大旗趙孟頫給予了深刻的批評。后代書家“從古人入”的學習方法是對的,但不可能再具“古人之意”。只有“拆骨”“拆肉”才能“始露全身”,擺脫前人束縛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正如楊凝式并不是不能作歐體、虞體,正是“離以取勢”也。生即離也,離合之道正如生熟之境。
其次是,董其昌“熟后生”的創作追求對待傳統書法的臨習,不管方法怎樣其最終的目的是為了自己的作品能達到自己的審美境界,形成自己的藝術風格。歷代書家如林,董其昌想要自立成家談何容易。如米元章說書學“如撐急水漲船,用盡氣力,不離故處”此比喻形象生動。
董其昌遍觀歷代法書真跡,眼界自然很高,他對待前人的優缺點看的很清楚。這使得董其昌能站在歷史的高度,看到了書法發展的過程,如其《容臺集》中說:“晉人書取韻,唐人書取法,宋人書取意。或曰意不勝法乎?不然宋人自以意為書也,非能有古人之意也。”可以說董其昌認識到了一個時代的文化氛圍。
北宋時期,禪宗思想就逐漸浸透到世大夫們的書法創作和書法理論中,蘇軾、黃庭堅等人的書法創作和書法美學思想都受到禪宗的巨大影響。然而,將自己對書法學習、創作的思想和美學觀念完全置于禪宗思想籠罩之下的董其昌對于傳統書法的繼承與創新關系的認識,帶有明顯的禪宗的印記。董其昌對禪學的探求已是沉酣入迷,他最終在禪學中悟得書學道理,學習古人,還要擺脫古人束縛,最終還是要充分發揮個人心靈的創造性。即從生到熟、再由熟到生的境界。
二、書法“熟后生”之美
中國書法可謂是中國文化的審美表征。它呈現出華夏審美人格及心靈世界,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書法藝術的流程反映出的不只是感官上的美感,更多的還有書藝思維中所產生的藝術哲學,也就是人們常言的書法美學,中國有句古話“字里有乾坤”,可謂是精辟的總結。
那么書法作品中“熟后生”的美是什么呢?明清之際思想家、中醫學家、書法家傅山《家訓》曰:“然筆不熟不靈,而又忌褻,熟則近于褻矣。”意思是在用筆上須熟這樣才能靈動,但是又忌輕浮和不莊重,這“褻”還有千篇一律毫無變化的意思,這是“爛熟”的表現。爛熟繼之為“俗”,一幅書法作品是否美關鍵看是否具有多層次的和諧美的內涵,最忌俗,俗則單調也沒有了韻味。正如董其昌評趙孟頫書有“朝市味”是也,而“熟后生”則是在繼承古法達到熟后再解脫對古法的束縛,去創造自己的新意。熟后之生是熟的繁衍、升華,是超凡入圣,洗凈塵俗,顯現自己面目的美。
明湯臨初《書指》中說:“書必先生而后熟,也必先熟而后生,始之生者,學力未到,心手相違也。熟而生者不落蹊徑,不隨世俗,新意時出,筆底具化工也。故熟不庸俗,生不凋疏。”這第二次的生,是與起始的生大異。在書法上叫做由無規矩的生,進入有規矩的生,是書法建立自我風格的伊始。創新伊始,始于對前人書跡學習己有的消化吸收,新形漸出,雖然多有不周,但此也是在所難免的,但經過不斷的改進修正,必然生而后熟。再次的熟,則與首先的熟,是有其根本的區別:前者是熟別人的書,后者則是熟自己的新造,建立了自己的風格。例如東晉書圣王羲之,初學衛夫人,后遍學秦漢諸家,眼界大開,既汲取前人養分,更豐富自我創新,在精研剖析、損益提煉,不斷作融合統一,創造了自己風格。唐代的顏真卿,先大力勤學蔡邕、二王、褚遂良,兼涉古人碑帖,無不心領神會,得其佳妙,并進行有破有立,有所選擇、有所取舍的學習,從而走向了自我風格,成為繼王羲之后卓立于書壇的一代大家 。
《國語》有言,“聲一無聽,物一無文(紋)”“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就是說,重復的聲音不能成為人們欣賞的旋律;單調的顏色不能織就人們所愛的花紋。只有參差不齊,各不相同的東西,才能取長補短,產生新的事物,而完全相同的東西聚在一起,則只能永遠停留于原有的狀態,不可能繼續發展。因此,孔子一貫強調必須尊重不同,故夫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智慧的人總是最善于使不同的因素和諧相處,最大限度地發揮其各自的特點,使之成為可以互相促進的有益的資源,這就是“和”。這是儒家的美學思想,反對單調乏味,推崇多樣統一的“和”。“熟后生”同樣是要求用心靈去感受自然生活中的萬物之象,從而創作出高于生活的藝術之象。書家不但要熟練的掌握高超的筆墨技巧,熟悉各家筆法字形結構,還要有求“生”的眼光,以自己的情感閱歷賦予作品以新的生命和情感。
《道德經》中言:“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為天下溪,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于樸。樸散則為器,圣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老子崇尚自然質樸的哲學觀念,“樸雖小,天下莫能臣”。可見老子把“復歸于樸”推向了最高的審美境界,“熟后生”與其意無異。如董其昌將自己的“生”解釋為“秀潤”,實際上這蘊藉著一種自我個性的內涵,回歸人的本真狀態即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種蘊涵表達的正是無欲無求,無為而有為的人生境界,表現在書法美上即與“熟后生”同義。
蘇東坡曰:“筆勢崢嶸,詞采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實非平淡,絢爛之極。”此處“老”“熟”不單是指人的年齡,技法的熟練,而是對老莊“無為無不為”審美的延續,此處之“平淡”與“熟后生”是同義語。
書法的審美受時代的制約,快節奏的現代生活與急功近利的滲透使得有些人把“熟后生”簡單的解釋為“創新”。熟后之生是經過生到熟再到生的過程,不單指創新,而是在師古達到熟的基礎上加入己意,更多追求的是一種心境,是取法古人又超越古人排除俗氣,接近自然的審美理想。熟后之生更不是拋棄傳統,不是對傳統的反叛,而恰恰是對傳統的繼承和發揚,是賦予傳統更深刻的意義。熟后之生也不是一味的追求生僻,不寫別人寫過的題材,不用別人用過的方法。“熟”中求“生”恰恰在同一表現對象同一表現方法中超越前人或他人。
如湯顯祖《牡丹亭》中的《驚夢》《尋夢》和他的《紫釵記》《牡丹亭》《南柯夢》《邯鄲夢》都寫到夢,但每個“夢”都有獨特的審視角度與構思,所以出色的創造了互不重復的“夢”戲。
中國近現代美術史上的開派巨匠,有“千古以來第一用墨大師”之譽的黃賓虹先生說:“畫有三:一、絕似物象者,此欺世盜名之畫;二、絕不似物象者,往往托名寫意、魚目混珠,亦欺世盜名之畫;三、唯絕似又絕不似于物象者,此乃真畫。”書法藝術亦是如此,“絕似又絕不似”的境界也正是由熟再到生的境界。
鄭板橋以詩書畫三絕著稱于世,尤以畫竹為佳,其感嘆說:“四十年來畫竹枝,日間揮寫夜間思。冗繁削盡留清瘦,畫到生時是熟時。”這里的生即“絕似又絕不似”,從生到熟,再由熟到生,乃是藝術的規律。正如臨熟先求像,像而求熟;熟而悟其意,意中見其神。然后,心聲共鳴,個性生發,字中有師亦有我,學古而出新意即達到了“生時是熟時”也就是“熟后生”的審美境界。
藝術的思維是感性重于理性的,書法藝術在進入人們視覺時也是一種感性大于理性的傳遞。如康德所言:
為了分辨某物是美的還是不美的,我們不是把表象通過知性聯系著客體來認識,而是通過想像力(也許是與知性結合著的)而與主體及其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相聯系。所以,鑒賞判斷并不是認識判斷,因而不是邏輯的,而是感性的、審美的,我們把這種判斷理解為其規定根據只能是主觀的。
由熟到生的作品也具有主觀性,也只是書法審美概念中的一個而已,書法中的佳品如百花,各有姿態,很難說哪個最好,只能說我們心目中誰是最好。董其昌為求變批判趙孟頫書,后人亦有批判董其昌書的,是同理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