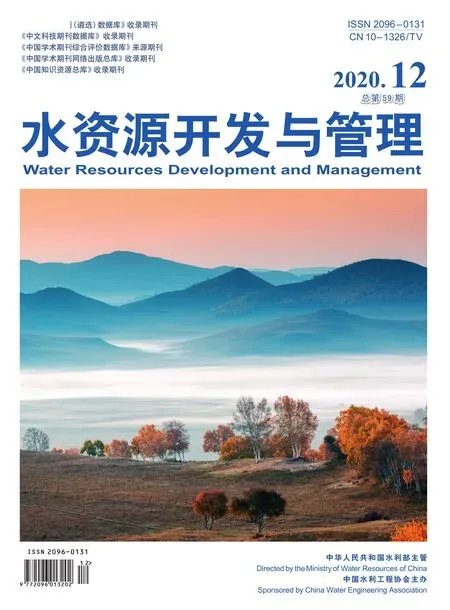湖南省流域生態補償實踐及改進建議
周 雙 何懷光 肖 熠
(湖南省水利水電科學研究院,湖南 長沙 410007)
生態補償是以保護生態環境、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為目的,依據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生態保護成本、發展機會成本,運用政府與市場來調節生態保護利益相關者之間利益關系的公共制度,其本質是生態服務功能受益者(或破壞者)與生態服務功能提供者(或保護者)之間的利益協調。湖南省流域生態補償工作起步較早,自2009年起,在經歷了政策研究、區域探索、全面實施等階段后,湖南省流域生態補償機制的建立工作已取得了明顯成效,但其仍存在市場化程度較低、資金補償量偏低、補償方式單一、配套政策不健全等問題。本文借鑒已有成功案例來梳理需加以改進和完善的內容,進而完善湖南省流域生態補償機制。
1 生態補償模式
1.1 政府直接買單模式
政府直接買單式生態補償主要指對森林、濕地、水流、耕地等自然資源或者具有重點生態功能的區域進行保護的行為給予補償,如對公益林保護、禁牧、退耕還林等行為的獎補,資金來源主要是轉移支付、預算內投資等。
1.2 受益者(破壞者)付費模式
受益者(破壞者)付費式生態補償主要指企業、政府或個人作為經濟受益者(生態環境破壞者)必須支付相應的補償費用,如排污企業向政府繳納排污費(稅),浙江、江蘇、廣州等省市對建設項目占用水域的行為進行收費等。
1.3 橫向補償模式
橫向補償式生態補償主要適用于具有重要生態功能、水資源供需矛盾突出、受各種污染危害的典型流域之間,補償主客體一般為流域上下游政府。
2 國內外流域生態補償實踐分析
2.1 國外流域生態補償現狀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生態補償理論研究和應用在國際上引起關注,尤其是發達國家學術界的高度關注。典型案例和做法如下:
a.易北河流域生態補償。涉及上游捷克和下游德國,雙方成立專門的合作組織對易北河流域實行統一規劃和管理,德國在捷克境內建污水處理廠并支付生態補償金,用于上游污染防治及補償因生態保護喪失的經濟成本和機會成本,補償資金來源包括財政貸款、水資源費和排污費[1-2]。
b.美國流域生態補償。美國生態補償起步較早且成效明顯,美國是世界上首個發掘生態服務商品屬性并引入市場化機制的國家,通過法律肯定了排污權交易在流域生態補償中的作用,推出流域銀行機制[2]。典型案例為紐約市與上游 Catskills 流域之間的清潔供水交易,其做法是對紐約市用水戶收費 ,整合資金轉移至上游地區,幫助上游農場主進行污染治理,改善飲用水水質,并為紐約市節省水凈化廠建設和運行維護費用[3]。
c.哥斯達黎加環境服務支付。其做法是建立森林基金,下游水電站向森林基金支付費用,上游林地所有者在履行造林、森林保護和管理等義務時從基金得到補償,使上游地區森林覆蓋率上升、受益農戶生活得到改善[4-5]。
d.南非則將流域生態保護與扶貧相結合,每年投入1.7億美元雇傭弱勢群體進行流域生態保護,既能改善水質、增加水資源供給,又能緩解貧困問題。
e.加拿大格蘭德河整治。以流域為單元綜合管理,利用 GIS技術準確劃定補償對象,使被補償者更加明確,將有限資金用到急需的補償項目,實現環保效益最大化[6]。
國外生態補償注重同時發動政府和市場的力量,主要特點為流域統一管理、生態(環境)服務付費、建立生態保護基金、引入市場化機制、探索生態扶貧模式等。
2.2 國內流域生態補償現狀
結合地方自然資源和經濟發展實際情況,浙江、安徽、福建等地區在流域生態補償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
a.金華江流域產生了全國首例跨行政區的水權交易案例,其做法是下游的義烏市以2億元一次性買斷上游東陽市約5000萬m3水資源的永久使用權。同時,金華江流域探索出異地開發補償模式,在金華市設置一塊屬于磐安縣的“飛地”,稅收全部歸磐安所有,以區位優勢代替傳統的貨幣或實物補償[7]。
b.新安江流域為全國首個跨省流域生態補償試點,由中央、浙江、安徽共同設立新安江流域生態補償基金(中央財政撥款3億元,安徽、浙江各1億元),資金專項用于流域產業結構調整、流域綜合整治、水環境保護和水污染治理等,建立了以兩省省界斷面水質作為考核依據的獎懲機制[8]。
c.閩江流域亮點是建立多元化資金籌措機制,通過整合中央轉移支付資金、各級財政專項扶持資金、水資源費、保費等,建立閩江流域生態補償專項資金賬戶,專款用于三明、南平閩江治理[9]。
d.東江流域江源生態補償屬于跨省域、跨流域生態補償,廣東省每年安排1000萬元用于江西東江源區涵養林建設,有效保障了下游廣東、深圳及香港用水安全[10]。
e.黑河流域為解決該地區水資源短缺、生態環境退化等問題,地方政府在草地資源規劃、林地建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通過移民安置、育林工程、水源保護等措施,保障了流域居民基本生活,流域生態環境逐步恢復[11]。
國內流域生態補償主要集中在水資源交易、飲用水水源地保護、生態環境治理等方面,主體為流域上下游政府,資金來源主要為財政資金,市場化程度、法制化程度較低。
3 湖南省流域生態補償主要措施
3.1 出臺流域補償政策法規
自2009年起,湖南省開始著手建立流域生態補償機制,成立了湘江保護協調委員會,出臺了《湘江流域管理條例》,推行湘江流域生態補償機制等。2012年9月,《湖南省湘江保護條例》經省人大常委會審議通過,為我國首部關于江河流域保護的綜合性地方法規,條例明確“建立健全湘江流域上下游水體行政區域交界斷面水質交接責任和補償機制”。2014年12月,省財政、環保、水利部門聯合出臺《湖南省湘江流域生態補償(水質水量)獎罰暫行辦法》,率先在湘江流域試行生態補償制度。2017年7月省政府辦公廳出臺《關于健全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實施意見》(湘政辦發〔2017〕40號),流域生態保護補償納入重點任務,提出探索建立多元化生態保護補償機制。2019年6月,省財政、生態環境、發改、水利部門聯合出臺《湖南省流域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實施方案(試行)》,在湘江、資水、沅水、澧水的干流和重要支流,洞庭湖流域的汨羅江和新墻河,珠江流域的武水流域,建立水質水量獎罰機制和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
3.2 加強部門分工協作
湖南省通過出臺專門文件,明確了相關職能部門及市縣政府職責。省財政廳負責流域生態補償資金的籌集、結算與分配,省生態環境廳負責市縣交界考核斷面設置與水質考核評價,省發改委負責流域生態補償機制建設相關工作,省水利廳負責水量監測及考核、確定最小生態流量標準等。各市州、區縣政府承擔本行政區域內水環境質量保護和治理主體責任,負責簽訂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協議,籌集和管理流域生態保護補償資金。
3.3 逐步完善補償機制
與2014年出臺的《湖南省湘江流域生態補償(水質水量)獎罰暫行辦法》相比,2019年出臺的《湖南省流域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實施方案(試行)》對補償方式、補償標準及核算方法、獎懲措施等作了進一步明確,其亮點和變化如下:一是補償范圍進一步擴大,由湘江流域擴大到湘、資、沅、澧干流和重要一、二級支流,以及其他流域面積在1800km2以上的河流;二是補償措施更加多樣,在原有水質水量獎罰基礎上,建立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三是獎懲機制更加完善,對方案發布1年內建立橫向生態保護補償機制且簽訂3年補償協議的,市州按800萬元/個、區縣按200萬元/個的標準進行獎勵,對除客觀原因未簽訂協議的,自2020年7月起,省財政按市州80萬元/月、省直管縣(市)20萬元/月的標準收取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資金。
3.4 省內省際補償相結合
除在全省流域范圍內探索和實施生態補償機制外,近年來,湖南省以河長制湖長制為契機,加強與重慶、貴州、江西、湖北等相鄰省市的對接,探索建立了省際協商合作機制。2018年4月,湖南、湖北、江西攜手簽署《長江中游地區省際協商合作行動宣言》,就強化生態環境聯防聯治等事項達成共識,并提出共同爭取國家支持長江中游跨區域生態補償。2018年12月,湖南省政府與重慶市政府共同簽訂《酉水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協議》,兩省市以位于重慶秀山縣與湖南省龍山縣交界處的國家考核斷面里耶鎮的水質為依據,實施酉水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2019年7月25日江西、湖南兩省政府簽訂《淥水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協議》,以位于江西省萍鄉市與湖南省株洲市交界處的金魚石斷面的水質為依據,開展淥水流域橫向生態保護補償。
4 湖南省流域生態補償實施成效
為總結《湖南省湘江流域生態補償(水質水量)獎罰暫行辦法》實施經驗及存在問題,提供完善生態補償機制的建議,彭麗娟等[12]在實地調研基礎上對《湖南省湘江流域生態補償(水質水量)獎罰暫行辦法》實施情況進行了評估。結果顯示,湘江流域生態補償機制運行保障體系逐步建立、重點政策措施穩步推進、社會效益初步顯現,湘江流域水生態環境質量得到明顯改善、地方政府流域治理責任不斷強化、湘江流域綠色發展態勢良好。
結合實際情況來看,湖南省生態補償機制主要存在以下問題:一是補償資金量偏小。公開資料顯示,2014年湘江流域生態補償獎罰資金總額約6500萬元,用于補償湘江流域范圍內8市35個縣市區,平均每個縣(市)補償金額約150萬元,遠遠低于地方環境污染治理和生態環境保護成本。二是補償方式相對單一。現有補償以資金補償為主,在政策傾斜、智力支持等方面相對欠缺。三是體制機制有待完善。生態補償以政府為主,市場化程度較低,未充分撬動社會資金和力量。四是基礎工作有待加強。目前,生態補償主要依據是斷面水質、水量等,未考慮生態系統服務價值,有待進一步加強相關研究,使生態補償的標準更加科學。
5 湖南省流域生態補償機制改進建議
5.1 拓寬資金渠道
湖南省生態補償資金來源單一、資金量少,需進一步拓寬資金來源。一是加大各級財政投入,參照江西、福建等省做法,在現有資金基礎上,建立省級投入逐年遞增機制,并注重撬動地方資金。二是強化資金整合,將重點生態功能區一般轉移支付、公益林生態補償、中央對地方的轉移支付等資金整合統籌。三是合理使用相關稅費,將按規定征收的水資源稅用于流域生態環境保護和管理等,推進水域占用補償制度,對合法占用水域的行為進行收費。四是爭取社會各界支持,鼓勵社會公益組織或公眾積極捐贈或資助。
5.2 探索多元化補償方式
現有生態補償以貨幣補償等“輸血式”模式為主,資金壓力大且成效不明顯,建議結合地方實際,積極探索“造血式”補償模式。一是發展“飛地經濟”,借鑒金華江流域異地開發補償模式,采用園區共建的方式,在長株潭等下游城市設置屬于永州、郴州等上游城市的“飛地”,上下游城市按一定比例對稅收分成,鼓勵和吸納上游農民工就業。二是強化政策和資金傾斜,加大上游地區污水處理廠等基礎設施建設,幫助上游城市更好解決環境污染問題。三是加大智力支持和幫扶,結合當前扶貧工作,組織專家團赴藍山、江華、新田等地區開展駐地幫扶,加大科技知識普及和農業推廣,開展職業技術培訓,提升群眾從業技能。
5.3 建立市場化補償機制
我國生態補償制度屬于政府主導型,市場化程度低,需進一步撬動社會資本,減少政府資金直接支出壓力。一是開展排污權轉讓,合理利用上游地區的初始分配排污權,在流域上下游之間進行排污權的轉讓和交易,保障上游地區的利益。二是推行水權交易,建立水權交易平臺,基于水量分配開展水權交易,流域上下游之間可通過市場化的手段對水權進行出售或購買。三是實行生態環境保護合同制度,上下游之間簽訂合同,明確上下游之間的權利和義務,根據合同履行情況實現流域之間的橫向補償。
5.4 強化生態補償基礎性支撐
當前生態補償實施過程中,存在法律法規不健全、自然資源產權制度不清晰、補償標準不統一等問題,亟須完善和細化相關配套措施。一是加強斷面監測能力建設,完善監測網絡體系,為生態補償提供有效依據。二是推動生態補償立法,對《湖南省流域生態保護補償機制實施方案(試行)》進行修訂、完善,在此基礎上出臺相關辦法或條例,通過地方性法規或規章對生態補償機制進行規定,實現生態補償由政策到法律的轉變。三是加快推進自然資源確權登記,結合河湖確權劃界工作,進一步明確水域(水流)的界限、范圍、面積以及所有權主體等信息,完善產權制度,為界定流域生態補償主客體責任提供依據。四是開展生態保護補償理論、生態保護補償效益評估體系、生態系統服務價值、生態補償標準測算等基礎性研究,強化生態補償基礎性支撐。
6 結 語
流域生態補償機制是水利管理和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促進生態環境改善的有效手段。通過對湖南省流域生態補償制度進行改進和完善,有利于提高該項政策的科學性和公平性,更好地實現流域上下游之間利益協調。同時,也可為更大流域(如長江流域)實施生態補償機制提供參考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