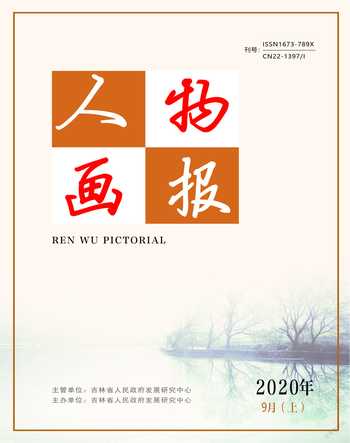辨析《魏晉勝流畫贊》內在含義
摘 要:《魏晉勝流畫贊》因張彥遠《歷代名畫記》轉錄而流傳至今。今世人多認為《魏晉勝流畫贊》是摹拓之法而常對其忽略。本文希望通過對其校釋進而闡發長康此篇文字的內在含義。
關鍵詞:顧愷之;《魏晉勝流畫贊》;校釋
《魏晉勝流畫贊》首句“凡將摹者,皆當先尋其此要,而后次以即事。”何為摹者,此處吾認為不可簡易釋為“臨摹”,“臨”“摹”有本質區別,“臨”者非定以效仿為目的,更注重于學習與自身理解進行創作。“摹”,《說文解字》云:規也。即有法度。摹者更多以嚴謹精細復制為目的。吾推斷,此贊更多以效仿為主,以匠人精神習前人之心得。“先尋其此要”,“尋”,用也。摹寫者應當先用此要法,而后再仿制。吾認為首句需注意點二:(一)摹者非畫匠,需在本跡摹寫中有所探索領悟。(二)摹者又需以匠人姿態學習,求乎法度之中。
“凡吾所造諸畫素,幅皆廣二尺三寸,其素絲邪者不可用,久而還正,則儀容失。以素摹素,當正掩二素,任其自正而下鎮,使莫動其正”。“素”,為繪畫所用的白色生絹。長康摹寫所用絹素,其面積皆廣至二尺三寸。“邪”,古同“斜”,若素絲斜而不齊,久后復歸于正,所摹寫之人物其儀態會發生改變致使神容盡失。以絹素摹寫,當使二素恰當遮掩。而后句中“任其自正而下鎮,使莫動其正”頗難理解,何為自正,吾認為此處不應將二字拆分而釋,“自”為“自然”。司馬遷《史記·老子列傳》載:“李耳無為自化,清凈自正”。自正,乃為自然事理。絹素當以自然下放,不可亂動此理。此進一步說明,摹者需具備嚴密謹慎之態度來做好前期準備工作。
“筆在前運而眼向前視者,則新畫近我矣。可常使眼臨筆,止隔紙素一重,則所摹之本遠我耳。則一摹蹉積蹉彌小矣。”吾認為,此句難于“近我”與“遠我”何為摹者所取。吾釋:眼隨筆勢,所摹之畫更傾向于“有我”,而眼觀筆勢,體悟筆勢所運,不局于紙素一障之隔,所摹之本才可到達“無我”的狀態。摹寫差誤隨“無我”狀態之補而越積越小。此當結合長康所處時代背景理解,魏晉時期玄學興起,貴“無”而輕“有”,“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1]故吾認為“遠我”亦或說“無我”才應為摹者所學習的。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中曾有這樣一個觀點:遍觀眾畫,唯顧生畫古賢,得其妙理。對之令人終日不倦。凝神遐想,妙悟自然,物我兩忘,離形去質。吾認為此可言及長康繪畫之道。
“可令新跡掩本跡,而防其近內,防內若輕物,宜利其筆重,宜陳其跡,各以全其想。”
是故可以用新跡遮蓋本跡,但要阻止新跡親近自己內心之想,防止心之所想如同輕物,何為“輕物”,嵇康《養生論》有云“外物以累心不存,神氣以醇白獨著”,“清虛靜態,少私寡欲”。故此,吾認為此應當是放棄對本跡刻意之追求,當如古人輕快流利而尋其筆之分量布列其勢,從而至各面得古人之所想。長康之描法,被后世人稱為“鐵線描”,明詹景風曾言“其行筆若飛而無一筆怠敗”。
“譬如畫山,跡利則想動,傷其所以凝。用筆或好婉,則于折楞不雋,或多曲取,則于婉者增折,不兼之累,難以言悉,輪扁而已矣。”畫山,當跡利神運,止,傷其結果。“凝”,《說文》載:止也。此當為停頓,此句例以說明筆跡當輕快流利,而后句則進一步闡述摹寫用筆之法。“婉”,《說文》載:順也。而“折”,斷也,于用筆中,當為止頓。摹寫者用筆或偏喜婉順之勢,則呆板而不雋秀,即無力勢,當多取彎轉之態。“不兼之累”,“累”,吾認為此不當釋“積累”,而應究本意,其本意為失衡也。于順中附加折頓之勢,則不會出現失衡之態。此用筆之法,長康亦無法以言釋之,故用輪扁斫論之典故而示讀者自己去心領神會。
“寫自頸已上,寧遲而不雋,不使遠而有失。其余諸像,則像各亦跡,皆令新跡彌舊本,若長短、剛軟、深淺、廣狹與點睛之節,上下大小醲薄,有一毫小失,則神氣與之俱變矣。”
對于脖頸已上之摹寫,寧當遲緩謹慎而不雋,不可使本跡神貌有所遺失。其余所摹之像,當尋本跡,摹寫神姿貌態,當不容有一毫之失。否則所摹寫之神氣便會發生改變。
“竹木土可令墨彩色輕,而松竹葉醲也。凡膠清及彩色,不可進素之上下也。若良畫黃滿素者,寧當開際耳。猶于幅之兩邊,各不至三分。”此句始言著色,畫面之竹木土之類可使墨彩輕柔,松竹葉當墨彩重染。摹寫者亦不可刻板仿本跡之形式。膠清與彩色,皆不可進素。若絹素隨時間而發黃,摹者不應刻意仿本跡之樣貌而故意作舊,寧當開際。
“人有長短,今既定遠近以矚其對,則不可改易闊促,錯置高下也。”所摹人物之長短高低,一旦確定其遠近位置,則不可隨意改變,打亂其高低順序。
“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視而前亡所對者,以形寫神,而空其實對,荃生之用乖,傳神之趣失矣。空其實對則大失,對而不正則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對之通神也”。
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曾言:“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凡是活的人,必須面前有個對象,他才能有所動作表情。如果沒有對象(‘空其實對’),他的動作表情就出不來,畫家畫他的肖像,很難達到傳神的目的。”吾認為這一見解對顧文原義解讀大致符合。然,“生人”吾認為此當釋為摹者所繪之人。摹者摹寫,若僅注重對其外在形象(眼所觀手所揖),這樣以形寫神的結果便是空其實對,難悟本跡之神,不待遷想妙得。
結語:謝赫列六法將傳移模寫列于六法之末,今世人多忽略摹寫之作用。吾卻認為傳移模寫為六法之基,乃學畫者所必通之本領,其內在心得吾認為畫者應當知曉。吾總結有三:(一),摹者當具備嚴格謹慎之態度,此為摹前之備。做到“凡將摹者,皆當先尋其此要,而后次以即事。”(二),摹者當“使眼臨筆”做到“所摹之本遠我耳”的“無我”狀態。把握太玄之理。(三)正確把握“以形寫神”,摹者當注重體會本跡之神氣所在,從而遷想妙得。
參考文獻:
[1]章宏偉編.歷代名畫記[M].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年
[2]俞劍華.中國古代畫論類編[M].人民美術出版社,2007年
[3]湯可敬譯注.說文解字[M].中華書局,2018年
[4] 葉朗.中國美學史大綱[M].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
[5]房玄齡.晉書[M].中華書局,2015年
[6]李瀚文編.史記[M].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6年
作者簡介:
王鑫,性別:男,民族:漢籍貫:山東,學歷:碩士研究生,單位:云南大學 研究方向:中國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