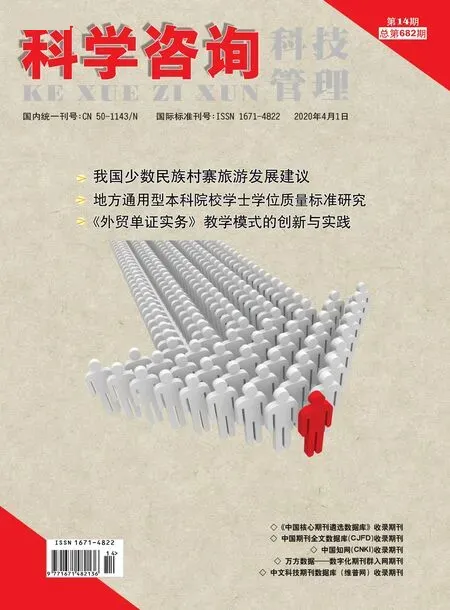從“碎片意象”探析本雅明的現代性思想
左曉晨
(重慶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 重慶 400044)
不同于齊美爾對現代性審美的關注,以及克拉考爾試圖在歷史和現實中還原現代性的本真面貌。碎片對于本雅明來說,更多地意味著是一種重構現代性理論的有效途徑。弗里斯比指出,“本雅明后期著作受某種十分明確的意圖激勵,那就是發展一種現代性理論。”[1](p253)本雅明重構現代性理論的嘗試體現在他的“拱廊街計劃”之中,這一龐大的計劃囊括了諸多社會領域,眾多計劃方案在政治、哲學、文學和個體關懷的語境中被不斷重塑和建構。
阿多諾認為,碎片在本雅明那里僅僅是類似蒙太奇的簡單堆積。但他沒有意識到,本雅明作為一個“拾荒者”,在廢墟之中撿拾碎片化的因素、垃圾,正是他揭示現代性史前史的必由之路。廢墟概念的出現,明顯受到費希爾“頹廢的現代性宣言”的影響。作為費希爾忠實的擁躉者,本雅明對現代性的理解持有消極和批判的態度。他將十九世紀的巴黎看作是給人以迷幻夢境的“現代神話”,而揭開神話的面紗后呈現出的卻是破敗不堪的廢墟世界,他的工作正是將廢墟世界化約為碎片意象,并通過研究廢墟中“辯證意向式”或“單子式”的客體碎片來指點迷津、解釋現代性的含義。因此,對于本雅明來說,“是碎片為總體保留著通道,而不是總體投射于碎片”。[1](p256)
也許是因為致力于對波德萊爾的研究,本雅明有關現代性的認識很大程度上與波德萊爾是重合的,但又有相異之處。弗里斯比評價道,“本雅明乃是致力于研究現代經驗的一個重要維度:那就是經驗的極端不連續性,它植根于瞬息萬變、短暫無常和偶然性,而且表現為由日新月異而帶來的震驚或轟動。”[1](p346)本雅明對于碎片的關注明顯受到了波德萊爾以及齊美爾的影響,但與此同時,他又提出了自己嶄新的觀測世界的方法。辯證意象、古今關系、巴黎城市、技術論證、商品消費等等新鮮元素,都在本雅明的研究里發揮巨大作用。
“現在關懷”與“過去比較”之間的辯證關系是本雅明關心的命題之一,“這種古代性與現代性的辯證,以及古代性存在于現代性本身之中的認同,已經賦予本雅明的現代性概念以獨到的特征。”[1](p259)若將本雅明的“拱廊街計劃”看作“現代性考古學”,那么現代性的起源和意義其實依附在十九世紀作為“當下實際時間的即刻實際存在”之中。換言之,即現代性的價值寓存于現在時刻、現在場域中的古代性因素。碎片在這種辯證的古今關系中凸顯其價值,作為現在存在與古代記憶的連接紐扣,它在被人們感知的同時,又帶領人們重返歷史意象的深邃之處。本雅明認為,能通過碎片接近歷史真實面貌的是城市中的“收藏家”和“考古學家”,他們有足夠的精力在繁雜的日常生活中剝除掩蓋現代性碎片的迷亂幻象,并從這些零碎的素材中重新理解現實世界。
現代性的一大特征是時間研究轉向空間研究,摒棄了傳統宏大的時間敘事模式,現代大都市帶給人們以支離破碎的散漫體驗,這一感覺只有在空間中才能被察覺。像波德萊爾流連于波西米亞社區,齊美爾考察都市對人們精神生活的沖擊以及克拉考爾對空間意象的專注,本雅明同樣注重空間展露出的現代性帶給人們的心理體驗。本雅明以十九世紀的巴黎作為考察對象,以閑逛者、收藏家的姿態徘徊在這座城市的每個角落,不斷收集、審視著散落于巴黎城市的各種碎片化意象。城市街道的迷宮、城市建筑物的遺址、大眾、藝術品、賭徒、妓女以及商品世界中的林林總總都在他的考察范圍之內。他試圖通過撿拾這些空間中不連續的瓦礫式碎片,予以其重新排列整合,從而捕獲碎片之間共含、貫通的現代性含義,并在現代性的變遷中觀測巴黎整座城市的歷史性內涵,以期撼動這座沉睡的現代迷宮。“本雅明的起始點是超現實主義的‘世俗幻象’,超現實主義面對的是‘拼湊狀態中的被曲解的世界’,是存在的真正現實主義面貌突破的世界。”[1](p309)作為現代性著落的巴黎世界,它不僅僅是考察現代性的空間集合,更是一個交織著資本主義物質關系、令所有人陷入集體夢幻的特殊場域。本雅明對巴黎這一現代性神話的態度是歷史的、批判的。不論是研究拱廊街,還是巴黎城中其他的“夢幻屋宇”,本雅明所做的不是稱頌,而是一種削減。正是在這種不斷地貶損、刺激中,被麻痹的現代性史前史記憶才得以逐漸蘇醒。換言之,本雅明所關心的“新奇與辯證同一”的現代性“瓦礫和碎片”,正是其提出的現代性史前史的起點。
諸如攝影術、照相機、電影、印刷品、廣告牌等現代技術的標志物也在本雅明考察的碎片序列之中。弗里斯比指出,技術對本雅明而言,不能被化約為“自然的統治”,它屬于純粹歷史變量的一部分。本雅明雖然對現代性持有批判態度,但他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技術擁抱者。他在肯定技術為人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時,也看到了現代性技術招致的弊端。這一思想體現在他關于藝術品的論述中,“在機械復制時代凋委的東西正是藝術作品的靈韻。”[2](p236),“如果能從靈韻的凋委這方面來理解當代感知手段的變化,我們就有可能表明這種變化的社會原因。”[2](p237)新的技術改變了“感知物本身”以及“人類與物之間的關系”,本雅明正是在技術帶來的改變中,看到了現代人與社會生活之間既迎合又對峙的緊張關系。技術作為現代性的碎片,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足夠多的震驚體驗。本雅明擅長放大、還原生活中這些被人們忽略的“最小物”,賦予散落碎片以新的意義,迫使人們重新審視現代技術成就令人驚跳和殘酷的本質,從而在更替、變化的世界中捕捉現代性對大眾日常生活沖擊的蛛絲馬跡。
本雅明在《中央公園》的一則筆記中詳述了“游手好閑者”與“人群”的關系,他認為“游手好閑者”是受大眾和生產商品化威脅的臨時現象。在十九世紀資本主義社會中,城市生活本質及商品化生產削弱了消費者的個性,批量生產、傾銷以及廣告文化應運而生,商品對人們生活的殖民擴展至全部領域,在機械般精確的生活節奏里,人的價值被壓榨和替換,由此產生了凌駕于人性之上的商品拜物教。本雅明將這些“商品的表達”視作窺視現代性的有效利器,他在商品中發現了“新奇”這一特征,而這一特征正是商品與現代性的之間共同的重要取向。“事實上,最新的感覺、最現代的東西就是那些像千篇一律的永恒輪回一樣的眾多事件的夢幻形式。”[1](p341)本雅明這段關于“新奇物的永恒輪回”的言論恰好揭示了現代性轉瞬即逝、不會恒久但本質上永遠同一的特點。在不斷重復的溯流中,時間不再具有意義,一切歷史都是當下,唯有“將過去從遺忘中拯救出來使我們能夠從過去中讀出現在”[1](p352),才能重返現代性史前史的古老記憶。
本雅明對現代性的理解和建構是侵略性、革命性的。他對十九世紀西方社會盛行的工具理性持有明顯的排斥態度,他企圖通過中止人與社會之間精確計算的“關系”來達成自己的反叛目標。從這個意義上說,本雅明的現代性革命更多的不是前進和躍升,反倒更像是向人性本質的復歸和回溯。從他對達達主義和超現實主義的認同能夠看出,本雅明對現代性的挑戰和不滿態度。他認為達達主義用奇譎、怪異的文字和圖片給麻木的都市大眾帶來猶如炮轟般的震驚體驗,這是向傳統理性秩序的有力挑戰。同樣,超現實主義作為一種“革命虛無主義”的思想,其離經叛道式的文藝美學觀亦被本雅明當作拒絕現代社會的偉大力量加以運用,他期望在現代性的夢幻中覺醒世界。面對現代性的迷幻夢境,“本雅明沒有選擇保留在‘夢的園地’,而是在歷史領域里通過‘摧毀神話’創造‘覺醒的星簇’。”[1](p282)原本斷裂、不連續的碎片在本雅明的思想中被串連在一起,在彌賽亞時刻的感知里被救贖,并閃爍著現代性冷暗而耀眼的光芒。通過重拾現代性碎片,本雅明在現代工具理性的紛雜世界中,重新填補起十九世紀巴黎社會與現代性史前史之間的巨大裂痕,并揭示了蘊含其中的現代性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