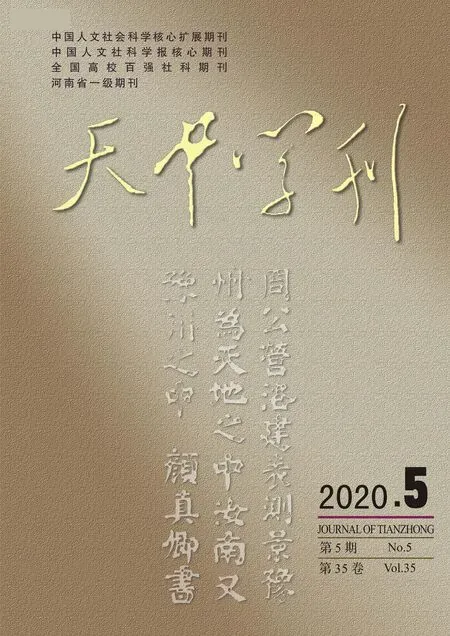詩禮文化視域中的婚禮之于家道的整全意義
趙國陽
詩禮文化視域中的婚禮之于家道的整全意義
趙國陽
(同濟大學 人文學院,上海 200092)
男女經由婚姻之禮而結為夫婦,形成生命共同體;婚姻之禮,謀合的是“二姓之好”,這意味著婚姻不是個人行為,而是包含著倫常秩序的社會行為。《詩經》中的相關婚姻詩為此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夫婦一倫是社會倫常關系正常展開的前提和基石,夫婦雙方要明確男女有別,各盡職分,既親愛又敬慎,以禮齊體,通過禮樂的教養而形成一個人倫的天地。
婚姻之禮;《詩經》;家道;生命共同體
婚姻之本義,是指締結了姻親關系的兩個家庭。《說文》釋“婚”曰:“婚,婦家也,禮娶婦以昏時,婦人陰也,故曰婚。”[1]259《說文》釋“姻”曰:“姻,婿家也,女之所因,故曰姻。”[1]259婚指女方之家(婦黨),姻指男方之家(婿黨)。可見婚姻的締結,不僅僅是男婚女嫁的個人之事,更與家道之成有著重要的關聯。本文將結合《詩經》中關涉婚姻之詩篇加以闡釋。家道的整全有賴于夫婦雙方謹守倫理職分,以禮齊體,經由禮樂教養而共同塑造有德性的人倫生活空間。
一、婚姻之道宜家人
(一)《桃夭》中的“婦德”與“家人”
婚姻是生命繁衍有序的紐帶,“昏以合男女”,婚姻是為人事之大者,婚姻之道在于能固兩姓之好。夫婦牉合則成家,家具有生生不息的道性,是對男女整全生命的成就和延續。《周南·桃夭》一詩歌唱了女子出嫁,女“歸”于男,并能咸宜家人之德;娶婦之家,既以繼嗣為慮,亦以“宜家”為先。蓋《桃夭》之女子素有賢名,故詩人見女子嫁人而美其如此。首章以“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喻女子之年時“少壯”,其容色如華之盛。觀其為女之時,又能得其時而嫁人,知其能為良婦也。二章言桃實,毛傳曰:“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2]56–57是何婦德,毛傳鄭箋皆未言明;但毛傳對于“婦德”的訓詁值得留意。若非有婦德,如何能藩育桃“實”?又如何能開枝散葉、“宜其家人”?詩篇反復詠嘆“桃之夭夭”,且每章末句都落在一個“宜”字上。毛傳訓“宜”曰:“宜,以有室家無逾時者。”[2]56鄭箋云:“宜者,謂男女年時俱當。”[2]56傳箋兩說皆言婚時,朱熹認為:“宜者,和順之意。”[3]6王先謙則引《說文》釋“宜、室、家”三字之義而認為:“‘宜其室家’,猶言安其止居。”[4]42總的看來,男女婚姻嫁娶以時,夫婦和順,其室家與家人自然能安樂和順。“宜”字與“桃之夭夭”的舒展之貌形成了緊密的呼應,“嘆其女子之賢,知其必有以宜其室家也”[3]6。
《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室、家不僅僅是居住的空間①,更承載著生生不息的道性。毛傳釋“家室,猶室家也”。鄭箋釋“家人,猶室家也”。傳箋未將“室家”“家室”“家人”詳做區別,恰恰說明了三者之間的關聯:室家一體,夫婦一體,共同構了“家人”的重要元素,是“家人”延續不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析言之,《桃夭》首章言“室家”,其文義重在“家”,這是于女子而言,“生以父母為家,嫁以夫為家”②,嫁人后有了自己的“家”。二章言“家室”,其文義重在“室”,這是于男子而言,而此室又為育桃“實”之居室。男與女,陰陽和合,夫婦和順,共同組成了家。而家之所以具有生生不息的道性,乃因其是生命孕育和成長的地方,是美德的集中地和社會倫理的發源地。故《桃夭》末章言“家人”,在夫婦和順的基礎上,一家之人皆能相“宜”,生命共同體得以生發,是以有“其葉蓁蓁”之貌,有枝繁葉茂、家人蕃盛之意。《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5]夫婦一倫,為人在天地間打開了一個倫常有序的空間。
在《桃夭》之詩所呈現的“家”空間中,由桃華而桃實,由桃實而桃葉,彰顯了“乾坤芳淑”之義,貫穿于其中的是一詠三嘆的“之子于歸”一句。女子嫁人,是聯結兩個家庭、延續生命的紐帶。《大學》獨引《桃夭》詩末章而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這就把“之子于歸”的女子嫁人放在更廣泛的“家人”“國人”的主體意義上來談。《易》家人卦之彖辭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6]138其卦象曰:“風自火出,家人。”風自火出,有內外相成之義。夫婦室家,內外一體;家人國人,內外一體。夫婦一倫,實乃王化之基。是故毛序從后妃能內修其化、襄助君子的方面認為“《桃夭》,后妃之所致也”[2]54。孔疏曰:“致使天下有禮,昏娶不失其時,故曰致也……此雖文王化使之然,亦由后妃內贊之致。”[2]54而王者之治天下,莫大乎于人倫。而夫婦乃為人倫之所始端,故“夫婦為王化之原”[4]11,可以化及四方。《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家邦。”此之謂也。
《桃夭》不僅呈現了生命長養繁育的空間——“家”,還呈現了一個整全的生命成長時間。在時間上,灼灼其華中蘊藏著生機的勃發,桃花盛開,桃實收獲,桃葉開散,在開放、收斂、再繁盛中,生命的“翕辟開合”通過時序上的陰陽和合而呈現。在空間上,之子于歸,男女各得其“所”——室與家,終宜其家人。夫婦室家,形成空間上的內外一體。四時行焉,百物生焉。開花結果,講究天時,陰陽交感,互根互養。在時間與空間的交互中,《桃夭》代表的是一個整全的、繁盛的生命共同體的衍續。與《碩人》《韓奕》描述婚姻嫁娶的盛大場景不同,《桃夭》對此并無所道,只是言其能“宜室家”“宜家人”,這就把“之子于歸”女子嫁人的重點放在了“婦德”上,為婦如此,方是內外兼備的“至貴至美”。
“婦德,陰德也。”[7]14《桃夭》對出嫁女子的婦德并沒有具體的直接描述,而是通過桃的意象來映襯其德。《詩經》中同樣以“桃(李)”指稱女子并稱贊其德的還有《何彼襛矣》一詩。該詩中描述的出嫁女子身份顯貴,但能“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2]120。首章從“襛”之顏色、“唐棣之華”光、“肅雝”之聲音,具象到“王姬之車”上,以此映托王姬敬和肅雝的德行,并道出其顯貴的身份。可見,顯貴的身份雖然系之于“平王”“齊侯”所代表的婦黨妻族,但王姬自身人品厚重,無挾貴傲矜之象,有敬和肅雝之德,這才是詩人稱贊她的緣由。婦德之為陰德,是因為它無須通過大張旗鼓來虛張聲勢,而是要把它沉淀到生活中,落實在生活中,并通過生命的長養來練就其德行。婚姻之本義,從字源說事關兩個家庭;婚姻的健康與否,則與夫婦雙方的德行倫理及職分定位緊密相關。
(二)婚姻中的夫婦倫理
《白虎通·嫁娶篇》關于婚姻的界定則是從時間及男女主從關系上說的,其曰:“婚者,昏時行禮,故曰婚。姻者,婦人因夫而成,故曰姻。《詩》云:‘不惟舊因’,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所以昏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昏亦陰陽交時也。”[8]491–492之所以昏時行禮,既取“陰陽交時”之時義,又彰顯了“示陽下陰”之男主女從、夫唱婦隨的陰陽互動關系。男女經由婚姻而結成夫婦,夫之得其為夫者,婦之得其為婦者,陰陽合德,剛柔健順,各正其位,此人倫之所以正。夫婦倫常關系是陰陽之道具體而微的顯現,夫婦之家是一小天地,天地之道是“大”,是夫婦要效法的對象。“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夫婦之間,在于能相互扶持。
夫婦一倫在五倫中尤為重要,夫婦之間既有父子親親倫常之義,還有君臣尊尊之義。“妻事夫有四義:雞鳴縰笄而朝,君臣之禮也;三年惻隱,父子之恩也。圖安危可否,兄弟之義也;樞機之內,寢席之上,朋友之道,不可純以君臣之義責之。”[9]195以夫婦喻君臣,是因“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10]164此理與君臣之義同。以夫婦喻兄弟,“兄弟謂昏姻嫁娶,是謂夫婦為兄弟也”[2]501。《詩》云:“宴爾新昏,如兄如弟。”《列女傳》亦曰:“執禮而行兄弟之道。”以夫婦喻父子,則強調了夫婦之親親的倫常關系。“夫婦之結合而能白頭偕老,其必然性可以說就建立在父子之倫的必然性上。”[11]但是夫婦一倫,與父子之倫不一樣的地方在于夫婦并非天然的血親關系,“婦之于夫,非天親也”[7]16。一方面夫婦一體同心,講求尊尊但不可害親親之義;另一方面,夫婦之間有陽主陰從之理,講求親親又不可害尊尊之義。而且,夫婦雙方所能達成的“內在相知與存在上之共同一體,連血脈相連、共同生活之父母子女都無法超越”[12]。《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晏子對齊景公論及五倫之義曰:
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
夫婦倫理的要求是夫義婦正,“義”與“正”的要求是一種雙向的互動,非單向只要求夫行“義”或妻行“正”,在要求妻子的同時,首先丈夫要能做好表率。夫妻雙方積極盡己之能,行己之義,立身行道,報施一體,生命在成長中趨于真實飽滿。《樛木》講的就是上施下報之情,“報施之情”可根據樛木與葛藟之“履”跡而“考祥”。樛木高木能下曲,葛藟攀附而上“猶能庇其本根”[13],上施下報,故能福履安之以“綏”、盛大而“將”、就之以“成”。需留意的是,葛藟是有根植物,并非無根的緣求與攀附。樛木下曲能施,葛藟上攀而報,施報之情乃“人道之常”,正是施報之情不絕,夫婦相輔相成,才能“樂只君子”,有福祿可安。毛詩是從“后妃逮下”的角度對其進行闡釋的,但落腳點依然在“逮下而安”。唯有內治安,由內而外,君子門外之治方成。
(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中的人倫與禮法
男女結合成家,要經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是一種經由人倫共同體、禮法社會共同體而加以確認的、族群性認可的象征。這與戀愛的情感不一樣。戀愛講的是無心之情感,而婚姻是人倫,人倫是講秩序的。經由婚禮而成家,這是由情感進入了秩序的共同體。父母之命,代表的是“家”這個人倫共同體的認可;媒妁之言,是禮法社會共同體的象征。父母代表的是“家”,家不僅僅是空間意義上的居所,它還是時間意義上的倫理存續之所,家具有生生不息的道性。中國傳統意義上的“齊家”是以“宗法社會”及“封建社會”相結合的“大家族”意義上的“家”,是由己身聯結的,上至高曾祖父、下及子孫玄曾的群體之“家”。“家”的縱貫維系,橫穿和依賴是的人倫之常。正是有了倫常,家才成為一個情感的歸所、一個交流和永續的基礎。婚姻之禮,謀合的是“二姓之好”,這意味著婚姻不是個人行為,而是包含著倫常秩序的社會行為。《鄭風·將仲子》中提到了“父母之言”不可不畏:“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然而關于該詩的主旨,毛傳以為是刺莊公也,他面對公叔段的失道之舉而不制止,也沒有聽從祭仲的勸諫,故意放任其弟段失禮失道;朱子《詩集傳》則認為該詩是淫奔詩,與莊公等無關;方玉潤則從詩本義出發,認為該詩或為民間夫婦相愛慕之詞,其詩義“有合于圣賢守身大道……惟能以理制其心,斯能以禮慎其守”[14]204。三說立意不同,但都突顯了“以禮自持”的主旨。面對權勢或情愛的迷惑,父母至親或有不敢欺,是故“欲念頓消,而天地自在,是善于守身法也”[14]204。《齊風·南山》亦有詩言:“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毛傳釋之曰“必告父母廟”[2]403。鄭箋云:“取妻之禮,議于生者,卜于死者,此之謂告。”[2]403這說明了娶妻必告啟父母,議于生,告于廟。具體來講,婚禮六禮中的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前五個程序都是女方在“家廟”接待媒人,此前還要先為神擺好案幾,安神尊命,然后迎接媒人并“聽命于廟”[15]1182。婚禮六禮中的最后一個環節“親迎”,男子承父命前往親迎,女子父親會先在家廟為神設幾,而后在家廟門外迎接,“主人筵幾于廟,而拜迎于門外”[15]1183。因此,娶妻必告父母的背后是對人倫共同體的追溯、對生命倫常的敬重,要在家廟祖先的見證下慎重地對待。
此外,父母為子女選擇的良配,主要從“孝悌”德行上來考量。《大戴禮記·保傅》云:“謹為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義者。”《論語》中記載的孔子嫁女、嫁侄女,為后人提供了嫁女擇婿之率范: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論語·公冶長篇》)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論語·公冶長篇》)
南宮適問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蕩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嫁,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適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論語·憲問篇》)
孔子嫁女,不問富貴地位,皆論其德。論及公冶長,不過曰“非其罪也”,更見公冶長行為之恒。論及南容,贊許其謹言明哲,其他不論,因為一家之內,言語不慎則喜怒無常,君子知言為心聲,見南容三復白圭,恐言有玷,其慎如此,既是修身之理又是齊家之義。孔子擇婿以“尚德”之君子為標準,真可謂擇婿之表率。從孔子擇婿不僅可見嫁女之道,更可見修齊之理。察乎人倫,以得其理。故,父母之命不可不慎擇。
媒妁之言所代表的社會禮法,其作用在于引導人的性情得其中正。《周禮·地官》有“媒氏”一職,“掌萬民之判”。賈疏曰:“‘掌萬民之判’者,謂治百族昏姻之事。”[16]1033可見媒氏作為“特掌其禮法政令”[16]1033的一種官職,不僅是“合二姓之好”的婚姻媒介,更重要的是合法婚姻關系締結的重要禮法保障。通過借助“媒妁之言”,“謀合異類,使和成者”[17],也避免了男女草率結合等行為,《士昏禮》鄭注說:“皆所以養廉恥。”[18]68《齊風·南山》一篇言道:“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此用“興”法,以析薪非斧不能,來興娶妻必有“媒”方可,“男女無媒不交”[15]1002。若是無媒而交,則是丑恥的一種行為。同樣的,《豳風·伐柯》中也出現了類似的詩句表達:“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毛傳曰:“媒,所以用禮也。”[2]618使媒用禮則得妻,這是婚姻締結的重要禮法保障。《衛風·氓》中的女子一方面也明白“良媒”的重要,但仍拋卻了禮法與男子私奔,終落得被棄的下場,這也從反面強調了“媒”在婚姻關系中的重要性。《鄘風·桑中》一詩諷刺男女相奔而“不待媒氏以禮會之”的社會亂象,這種亂象是由于衛國公室淫亂致使政教衰敗、民俗流散而導致的。
父母之命代表的是社會秩序的倫常形態,媒妁之言代表的是社會秩序的禮法形態。孟子曰:“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鉆穴隙相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可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成就幸福婚姻的兩個必要條件,若不依禮而奔則為妾;依禮而結成的夫妻關系對彼此和家庭有道德使命和義務驅使。夫妻關系,是人倫之始,是王化之端,人倫之常要經由禮法社會的聯結確定,而融入更大的族群生命延續與繁盛中,進而移風易俗,化王道之成。
二、婚禮之義宜有別
(一)婚禮之“別”與“合”義
婚姻是男女兩性建立生命共同體的標志,是一個人具備合乎禮法的社會身份的標志及社會生命的確定。男女經由婚姻之禮而結成夫婦,夫婦關系乃人倫之本,故而婚姻之禮于社會各種倫常關系的穩定非常重要。《禮記·昏義》開篇就道出了婚禮的功用:“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后世也。”[15]961昏禮之用,在于合兩姓家族之好,非合男女二性之好;昏禮必告祖宗,也是宗祖的衍續,這是一種“共生、共長、共好”的生存原則,由此也可見夫婦關系的形成對于人類生命繁衍存續的重要意義。
婚禮謀合二姓之好的前提是要明“別”。首先,明人禽之別。《禮記·曲禮》曰:“夫唯禽獸無禮,故父子聚麀。是故圣人作,為禮以教人,使人以有禮,知自別于禽獸。”[15]6圣人制禮,使人明禮,遠離“父子聚麀”的禽獸之行。其次,明男女之別。男女要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族群性共同體的認同方能結為夫婦。人之情以男女之情尤甚,男女若無防則性情散亂,故圣人制禮復其性,對待婚禮要“敬慎重正”,即要敬謹、審慎、鄭重、規正地對待婚禮。《禮記·經解》曰:“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15]955明男女之別,不是對男、女本身的限制,而是基于他們都作為“身之為人”的共同前提下,尋找并實現兩性差異所蘊含的“和合與共”的人性生存意義。明曉男女之別,也就明了夫婦之義,這就需要通過恰當的人文形式,即婚禮來體現,“婚禮享聘者,所以別男女,明夫婦之義也”[19]。夫婦是至親,越是如此,越是要明確夫婦間應有的界限,這個界限涉及夫婦在家“內”領域與社會“外”領域的角色與職分等。“禮者別宜”[15]725,夫婦有別,要依禮而行,明分才能使群,家內之治與門外之治各有分工。若婚姻之禮廢,夫婦不依禮而行,“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也”[15]956。所以,“禮始于謹夫婦……辨外內”[15]545。明辨內外,各自分工,循其名責其實,才有利于人倫共同體的發展。
婚禮是其他社會儀禮和倫常關系的根本和基礎,冠禮是成德之始,兩者皆不可以童子之道論;“夫禮始于冠,本于昏,重于喪祭,尊于朝聘,和于射鄉。此禮之大體也”[15]1185。這從五個方面標舉了人在社會關系中的常規禮儀,其功用分別是“始、本、重、尊、和”。婚姻之禮,其慎重如此,是因為“敬慎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15]1182。婚禮之所以是禮之要本,在于它是社會倫常關系的邏輯起點。夫婦為人倫之本,男女只有通過婚姻關系才能確定在人倫共同體和禮法社會共同體中的歸屬。
(二)《大雅·大明》一詩中的婚姻六禮
“婚姻之道,謂嫁娶之禮。”[2]360婚姻之道通過嫁娶之禮明其規制。禮為天地之序,“婚姻之禮正,然后品物遂而天命全”[20]。人之性情得以通過禮樂而潤澤,生命就不再是漂泊無依,而是與禮樂連接,并經禮樂潤澤的生命。昏禮之名,是因為以昏為期,故名之。之所以以“昏”為期,取其“陽往而陰來”[18]68之義。婚姻之六禮有個逐步完善的過程。唐代杜佑《通典》提道:“燧皇氏始有夫婦之道,伏羲氏制嫁娶以儷皮為禮,五帝馭時娶妻必告父母,夏氏親迎于庭,殷迎于堂,周制限男女之歲,定婚姻之時,親迎于戶。六禮之儀始備。”[21]《大雅·大明》一詩就簡要而又集中地展現婚姻六禮。其詩曰:
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大邦有子,伣天之妹。
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孔疏據毛傳鄭箋之義將此八句訓為“準行六禮之事”[2]1138。文王贊美“大邦有子”,大邦之女宛若“天之妹”,是贊美女子有賢德。既知其賢,便“求昏”。此“求昏”是指婚姻六禮程序之初禮——“納采”,男方通過媒氏向女方提親,行采擇之禮。鄭箋下云:“既使問名。”[2]1136據《儀禮·士昏禮》,納采初禮過后,即請問名,“擯者出請,賓執雁,請問名。”[18]72可見納采、問名兩禮在同一天進行。下言“文定厥祥”,鄭箋云:“問名之后,卜而得吉,則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使納幣也。”[2]1137娶妻占卜的目的是“卜女之德,知相宜否”[8]472,結果是“祥”,則納吉,繼而納征。孔疏曰:“昏以納幣為定,定此吉祥,唯納幣耳,故知文王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2]1137下言“親迎”,則“請期”之禮可知也。文王親迎于渭水,并造舟以為橋梁,可見敬慎鄭重。鄭箋云:“欲其昭著,示后世敬昏禮也。”[2]1137婚姻六禮,依次漸進,有漸卦之道,猶然待禮而漸進也。婚姻六禮,不貞而能之乎?男女結為夫婦,要依禮而行,循禮漸進,急欲躁進者如《氓》之女子而未能有終。
婚姻六禮,以親迎為重。孔疏引鄭玄曰:“天子雖至尊,其于后猶夫婦也。夫婦判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于此哉!”[2]1139《韓奕》一詩也講到了諸侯親迎:“韓侯迎止,于蹶之里。”韓侯娶妻,親迎至蹶里。然春秋以降,禮崩樂壞,親迎之禮漸廢。《春秋》隱公二年九月,“紀履緰來逆女”,公羊傳譏“始不親迎也”[9]38。按《春秋》書法,外逆女不書,然此事被書之于冊,乃因紀國國君未行親迎禮,而是派遣紀國大夫履緰前來。國君不親迎此前已有,然公羊傳文譏諷“始”不親迎,乃是因此這是入《春秋》后的首例不親迎之事,故雖此為“外逆女”,仍書之。何休解詁曰“民所以必親迎者,所以示男先女也”[9]39。此事托為《春秋》不親迎之例始,是為了彰明王者行教化之端義。“《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夫婦正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和,君臣和則天下治,故夫婦者,人道之始,王教之端。”[9]40
《著》是一首描述婚禮現場的詩。毛序以為該詩刺“時不親迎”,即《著》從正面描述了婿至婦家親迎之禮;三家詩無異議。然而新郎所俟之處(“著、庭、堂”)不一,所著冠服之飾異,毛傳以為是親迎之人身份不同,分屬士、大夫、人君;三家詩認為是夏商周三代禮制不同,詩篇錯陳三代親迎之禮;鄭箋則以為三章俱述人臣親迎之禮;而朱熹引呂祖謙言認為,新郎沒有親迎,“故女至婿門,始見其俟己也”[3]67。王先謙結合三代禮制的分析認為,《著》之三章分述三代婚禮之制。雖三代婚姻禮制不同,但《著》分章歷陳,足見“其禮端嚴之盛自見,列代崇重之義自明”[22]。而這也是《著》要表達的主題,即以三代親迎禮制諷刺齊俗之時衰,以刺時失。
親迎之禮如此重要,首先是因為夫妻是親人,“敬而親之”,既是對婦的重視,也是對婦的尊敬。《禮記·郊特牲》曰:“婿親御授綏,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15]500新郎親自為婦駕車,是要表示夫婦之間的相互親愛之情。尊敬并親愛親人,先王以此推而廣之并得到了天下。整個親迎禮,是特別能表示夫妻之敬的。其次,表示男剛女柔、夫唱婦隨、陰陽和合的夫婦倫理。《禮記·郊特牲》曰:“男子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15]500剛柔相濟、陰陽和合、明夫婦相扶之意,如此“剛來而下柔”,配合得當,自然會有“動而說”的良效。再次,要端正人倫之始。“親迎之道,重始也。”[23]479夫婦乃人倫之本,天子亦親迎,就是要表示對妻子的尊重,夫婦一體。在《禮記·哀公問》中,魯哀公認為戴著冠冕身著禮服去親迎,豈不是過于隆重了嗎?孔子正色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圣之后,以為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15]962《列女傳》有“宋恭伯姬”一則,記載伯姬因宋恭公不親迎之故,不肯聽命行夫婦之道,習魯詩之劉向贊其“守禮一意”。
婚姻六禮中,除“納征”用幣帛外,其他五禮均用雁,取的是彰別、相從之義。《禮記·郊特牲》:“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15]500執雁以為禮,表示對婦的恭敬,同時彰明男女之別。《白虎通》曰:“取其隨時而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是隨陽之鳥,妻從夫之義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逾越也。”[8]457這是根據大雁隨陽之習性而寄望夫婦和諧,夫唱婦隨,明禮有序。納征之禮是男女成婚的關鍵一步,《禮記·坊記》曰:“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15]1002其用“玄纁束帛、儷皮”作為聘禮。納征講求的是“幣必誠”,即“幣帛必須誠信,使可裁制,勿令虛濫”③。這代表的是一份誠意和信諾,“信”意味著“誠”的落實,是扎扎實實的生長之德。經由納征之禮男女婚姻關系初步正式確立,為即將結成的夫婦生命共同體長養出扎實可信的生命力,故“昏禮者,禮之本也。”[15]1185
(三)《召南·行露》之貞女謹禮守志
禮是實現人與人美好關系的儀則,禮的背后彰顯的是分寸節度。“婚姻之際,非禮不可。”[2]364通過莊嚴恭敬的婚禮,使人們的“習性”轉化為“德性”。《召南·行露》一詩則講述了女子因夫家婚禮不備,拒不肯往,結果招致獄訟,但依然持節守義、“亦不女從”的堅定態度。毛序釋詩旨曰:“《行露》,召伯聽訟也。”[2]93毛詩認為在衰亂之世,因被澤文王之化,“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2]93,該詩重點在德行教化。三家詩的解釋重在貞女謹守禮制方面,強調了對婚姻禮制的堅守。其中,《韓詩外傳》明確指出該詩是女子許嫁之事:“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為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24]男子“一禮不備,一物不具”,是財禮不足。婦道之宜,即是能以禮自守,持志不從。《齊說》也認為是關于婚禮之訟:“婚禮不明,男女失常。《行路》有言,出爭我訟。”[25]劉向在《列女傳》中為這首詩安排了一個具體的故事情節:召南申女乃申國女子,被許嫁給豐城的一位男子,因夫家“輕禮違制,遂不肯往。”[10]155毛傳亦曰:“昏禮純帛不過五兩。”朱子沿用此說,認為是“媒娉求為室家之禮初為嘗備”[3]13。可見,該獄訟的起因是男子納征之幣不足,女子謹禮持志而不從。
《行露》之女子能謹禮,謹的是室家之禮。納征之財禮,并非僅僅是物,也是“誠”的表征。《禮記·郊特牲》曰:“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26]《行露》之女子并非貪財的女子。“昏禮純帛不過五兩”,可見求為室家亦易備禮,但男子為什么不備禮呢?《行露》雖然借女子之口來談婚禮不備的問題,其實也是在談強暴之男的德行問題。“禮,毋不敬。”夫妻一倫,是敬親相加。既要相親愛,又要能誠敬。親愛與誠敬是一對陰陽的關系,沒有誠敬,何談真正的親愛;沒有真正的親愛,所謂的誠敬也是一句虛言。婚禮作為夫妻倫常關系的開端,源頭清明,根基方正,《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故君子慎始。”《行露》之女子注重的是室家之禮背后的夫妻倫理,也是“愛身”的表現,是敬身自重。《禮記·哀公問》曰:“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15]962敬身,是因為己身是父母遺留下來的身體,是天地之間的生生之物,是通過自己與父母、天地的關系而達成的,它不是自己一個人的專屬。是故,敬身,才是愛身。
《行露》之女子能守志,守的是大貞之志。《易》之屯卦九五爻辭曰:“小貞吉,大貞兇。”[27]19對于《行露》之女子而言,小貞是名節,大貞是作為人的尊嚴。屈從小貞,就不會招來獄訟,是為“小貞吉”;堅守大貞,被訟而獄,是為“大貞兇”;這是從“利”的角度進行的判斷。然而,從“義”的角度來看,“兇,義也;吉,非義也。”[7]11堅守大貞的結果雖是兇,但此舉是合乎“義”的。屈從小貞的結果雖為“吉”,但卻是不義之舉。獄訟之事會傷其名節,一般人可能會選擇屈從。但《行露》之女子寧失小貞之名節,也要堅守大貞之志,不違禮而從。固然,她會因為招惹獄訟而有損名節,但她“亦不女從”的抗爭是在捍衛她作為一個人的尊嚴。“大貞者,保己而不保物者也。”[7]11其為“大貞”者,真正保全自己的心志而不汙于身,不畏世俗,奮起抗爭,選擇將活但不活于茍活。
女子尚能謹禮持志,男子亦要自省其身,《行露》之男子也該有所警醒。《易》之訟卦六三爻辭曰:“食舊德,貞厲,終吉。”對女子而言,堅守其志不畏世俗眼光,以保全其有,是因為她能“食舊德”,以本性之德為本,守住中正之道,雖然過程危險,但結果可能呈現吉象。對男子而言,要能夠“守素分而無求”[27]31,回到自己的生命本身來思考,甚至是無訟,而不是憑勢訴訟。“無訟在于謀始,謀始在于作制。”[6]28若男子按婚姻六禮之制迎娶女子,則無訟而吉。此外,方玉潤認為該詩恉是貧士持志,“士處貧困而能以禮自持”[14]104,從男子的角度以啟示。不論《行露》一詩的主人公是“貞女”還是“貧士”,在他們身上都展現出謹禮持志的一點。“禮者,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必顛蹶陷溺。”[23]479禮,乃人行走的節律,失其禮節,必陷其困。《史記·外戚世家》:“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28]夫婦一倫,乃人道之開端,而婚姻嫁娶之事就顯得尤為慎重,“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為宗廟主也”[10]155。
總體而言,《行露》之女子,堅守禮制,迎險而健行,為的是大貞之志。行其當行,不以利害,行其可行,走從容的“中道”。“天地合而萬物興焉,人以昏姻訂其禮。”[15]500男女需守禮而結成夫妻,敬慎親愛,并通過禮樂的教養形成一個人倫的天地。這樣的人倫天地形成的家國具有文明的教養,是一個有禮義的人倫共同體。而夫婦之禮,彰顯其義。如《鵲巢》篇從正面呈現了一個有禮義的共同體生活,所有的禮樂生活是圍繞共同的空間展開的。鵲建巢,鳩居之,比喻夫婦相比而居,將之成之,共同孕育、建設新的家庭,這是一個整全的婚姻家庭生活。詩中反復出現的“百兩”,是“文之備也”。這與《行露》中的“室家不足”“一禮不足”形成鮮明對比。
婚姻之禮乃“禮之本也”[15]1185。婚姻之禮是男女結成生命共同體的重要禮法保障,對于家道的整全具有實質性的意義,而并非簡單的系列程序。“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15]985文之以禮樂,通過禮樂恰當地表達情感,通過情感表達自返其性,這是一種通往“復性”的生活狀態。“人之自然生命之生與婚姻及死,皆在禮樂中,即使人之生命不致漂泊無依。”[29]而男女經過婚姻之禮結為夫婦,進而奠定政治社會生活的倫常基石,也標志著一個新的人倫共同體的誕生。
① 朱熹將室、家從空間上做了闡述:“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參見朱熹《詩集傳》(中華書局2019年版)第6頁。
② 見《公羊傳·隱公二年》“婦人謂嫁曰歸”注。
③ 見《禮記正義》(鄭玄注、孔穎達疏,龔抗云整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951頁。“幣必誠”,這與今日聘禮虛高形成強烈比照。
[1] 許慎.說文解字注音版[M].徐鉉,校定.愚若,注音.北京:中華書局,2015.
[2] 毛詩正義[M].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3] 詩集傳[M].朱熹,集注.趙長征,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9.
[4] 王先謙.詩三家義集疏[M].吳格,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1.
[5] 朱熹.四書章句集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9:24.
[6] 王弼.周易注校釋[M].樓宇烈,校釋.北京:中華書局,2012.
[7] 王夫之.詩廣傳[M].北京:中華書局,2009.
[8] 陳立.白虎通疏證[M].吳則虞,校.北京:中華書局,1994.
[9] 春秋公羊傳注疏[M].何休,解.徐彥,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10] 綠凈.古列女傳譯注[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4.
[11] 林安梧.血緣性縱貫軸:解開帝制重建儒學[M].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6:38.
[12] 簡良如.詩經論稿:卷1[M].臺北:Airiti Press Inc,2011:174.
[13]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1:551.
[14] 方玉潤.詩經原始[M].北京:中華書局,2011.
[15] 禮記[M].胡平生,張萌,譯注.北京:中華書局,2017.
[16] 孫詒讓.周禮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7.
[17] 周禮注疏[M].鄭玄,注.賈公彥,疏.趙伯雄,整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271.
[18] 儀禮注疏[M].鄭玄,注.賈公彥,疏.彭林,整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19] 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M].王文錦,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144.
[20] 班固.漢書[M].北京:中華書局,2012:2880.
[21] 杜佑.通典[M].北京:中華書局,1984:333.
[22] 王禮卿.四家詩旨會歸[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728.
[23] 王先謙.荀子集解[M].北京:中華書局,2013.
[24] 韓嬰.韓詩外傳集釋[M].許維遹,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0:2–5.
[25] 徐芹庭.焦氏易林新注[M].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10:320.
[26] 禮記正義[M].鄭玄,注.孔穎達,疏.龔抗云,整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949.
[27] 程頤.周易程氏傳[M].王孝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16.
[28] 司馬遷.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2013:3893.
[29] 唐君毅先生復牟宗三先生書[M]//牟宗三.人文講習錄.長春:吉林出版集團,2010:7.
The Complete Meaning of Marriage to Family in the View of Poem and Rite
ZHAO Guoyang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The men and women become couples through the rites of marriage, and then form a community of life. The rites of marriage cooperate with “the good of two surnames”, which means that marriage is not an individual behavior, but a social behavior that contains the ethical ord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sband and wife is the premise and cornerstone of the normal development of social ethics. Couples should make clear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between men and women, so that to do their best with love and respect; and in the end to form a world of human relations through the upbringing of rites and music.
the Rites of Marriage;; family Tao; community of life
G02
A
1006–5261(2020)05–0139–09
2019-12-16
趙國陽(1986―),女,河南南陽人,講師,博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 楊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