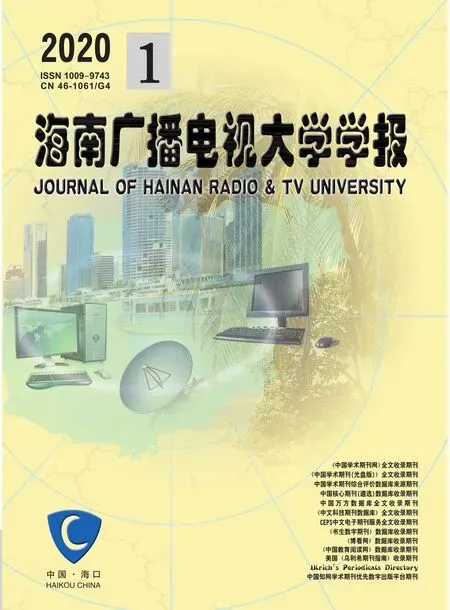清末民初湖南佛教慈善事業(yè)研究
干紅強(qiáng)
(蘭州大學(xué) 歷史文化學(xué)院,甘肅 蘭州 730000)
作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自漢朝傳入中國(guó)以來,經(jīng)過近兩千多年的發(fā)展,已經(jīng)成為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中一個(gè)重要組成部分。清末民初中國(guó)的佛教慈善事業(yè)作為近代中國(guó)慈善事業(yè)的一部分,為近代中國(guó)慈善事業(yè)的發(fā)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xiàn)。清末民初湖南的佛教慈善事業(yè)是近代中國(guó)佛教慈善事業(yè)的一個(gè)縮影,清末民初湖南佛教界所舉辦的慈善公益事業(yè)客觀上幫助了一批亟待救援的弱勢(shì)群體,緩解了社會(huì)救濟(jì)的壓力,有助于穩(wěn)定社會(huì)秩序,促進(jìn)社會(huì)發(fā)展。總的來說,研究清末民初湖南佛教慈善事業(yè)對(duì)于當(dāng)今湖南以至中國(guó)佛教慈善事業(yè)的發(fā)展有重要啟示意義。
關(guān)于清末民初湖南的佛教慈善事業(yè),學(xué)界并沒有專門的有關(guān)論述,與之相關(guān)的只有對(duì)于近代中國(guó)佛教慈善事業(yè)的整體研究以及對(duì)于近代湖南慈善事業(yè)的研究,前者包括周秋光、曾桂林所著的《中國(guó)慈善簡(jiǎn)史》,鄧子美的《傳統(tǒng)佛教與中國(guó)近代化:百年文化沖撞與交流》,高秀峰的《近代中國(guó)佛教慈善事業(yè)研究》,于媛的《民國(guó)佛教慈善事業(yè)研究》等。后者包括周秋光、張少利、許德雅等著《湖南慈善史》,簡(jiǎn)婷的《晚清湖南賑災(zāi)救災(zāi)》,鄭自軍的《傳統(tǒng)到近代的轉(zhuǎn)軌——論民國(guó)前期的湖南賑務(wù)》,向常水的《教會(huì)對(duì)戰(zhàn)地的慈善救濟(jì)——以民國(guó)時(shí)期的湖南地區(qū)為例》等。
慈善事業(yè)是一項(xiàng)龐大的系統(tǒng)工程,涉及到社會(huì)生活方方面面,因此對(duì)其研究不應(yīng)固守成規(guī),要善于因事制宜,本文擬在前人研究基礎(chǔ)上,采用歷史研究方法并結(jié)合相關(guān)史料,闡明清末民初湖南佛教慈善事業(yè)的緣起、發(fā)展以及影響。
一、清末民初湖南佛教慈善事業(yè)的發(fā)展背景
(一)清末民初湖南的社會(huì)狀況
甲午戰(zhàn)爭(zhēng)前湖南仍然是一個(gè)傳統(tǒng)社會(huì)。 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zhēng)使中國(guó)國(guó)門打開,面對(duì)數(shù)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面對(duì)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guān)鍵時(shí)刻,許多有識(shí)之士開始向西方學(xué)習(xí),一些地方省市也相應(yīng)地進(jìn)行變革以挽救中國(guó)社會(huì)于危亡。此時(shí)的湖南雖然也開始了一些近代化的歷程,但是相比之下其封閉性還比較頑強(qiáng):湖南的書院仍以重視經(jīng)世之學(xué)而聞名,以曾國(guó)藩為代表的湘軍集團(tuán)雖然對(duì)傳統(tǒng)社會(huì)有種種厭惡但還沒有徹底改變的想法;歷時(shí)三十年之久的洋務(wù)運(yùn)動(dòng)未給湖南帶來多大變化,湖南也沒有創(chuàng)辦什么近代工業(yè)、學(xué)習(xí)近代科技,因此就有人稱湖南為中國(guó)“大陸腹地中一座緊閉的城堡(1)周錫瑞:《改良與革命》,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頁。。”
甲午戰(zhàn)爭(zhēng)之后,面對(duì)中國(guó)在戰(zhàn)爭(zhēng)中的慘敗尤其是湘軍在遼東戰(zhàn)場(chǎng)與日本作戰(zhàn)的失敗,給了湖南各界以警醒,湖南社會(huì)也發(fā)生了一系列變化。為了救亡圖存,湖南的一部分有識(shí)之士開始不再固守傳統(tǒng),轉(zhuǎn)而積極向西方學(xué)習(xí),學(xué)習(xí)西方先進(jìn)的科學(xué)技術(shù)以及政治制度:1897年10月,由譚嗣同等發(fā)起在長(zhǎng)沙創(chuàng)辦了以開民風(fēng)為己任的時(shí)務(wù)學(xué)堂;1898年3月7日,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在長(zhǎng)沙創(chuàng)辦《湘報(bào)》宣傳“愛國(guó)之理”“救亡之法”,倡導(dǎo)變法維新。 湖南各種實(shí)業(yè)在甲午戰(zhàn)后幾年競(jìng)相開辦,如寶善成機(jī)器制造公司、和豐火柴公司等;此外,新式教育在湖南日益勃興以及官費(fèi)、自費(fèi)留學(xué)人數(shù)不斷增加。
民國(guó)初年,湖南社會(huì)處于發(fā)展與動(dòng)蕩相交織的時(shí)期。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首義之后,10月22日,以焦達(dá)峰、陳作新為代表的湖南革命黨人率先響應(yīng)起義,光復(fù)長(zhǎng)沙并隨即成立中華民國(guó)湖南軍政府(次日將其改為中華民國(guó)軍政府湖南都督府),到11月上旬,湖南全省大體光復(fù)。民國(guó)成立后,湖南的實(shí)業(yè)得到了進(jìn)一步振興、資本主義經(jīng)濟(jì)獲得了一定發(fā)展。但與此同時(shí),辛亥革命失敗后的湖南政局極端動(dòng)蕩,“民國(guó)成立后的八九年間,湖南都督(督軍、省長(zhǎng))先后九易其手(2)劉泱泱:《湖南通史》(近代卷),長(zhǎng)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727頁。,”此外湯薌銘、張敬堯的殘暴統(tǒng)治,再加上北洋各派軍閥為爭(zhēng)權(quán)奪利爭(zhēng)斗不休,湖南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
(二)清末民初湖南佛教的發(fā)展
辛亥革命前,是湖南佛教日益衰落的時(shí)期。首先十九世紀(jì)中期出現(xiàn)的太平天國(guó)運(yùn)動(dòng)因其信仰拜上帝會(huì)而對(duì)佛教等其他宗教有強(qiáng)烈的排斥性,因此“所過名城繁鎮(zhèn),梵宮寶剎,必毀拆殆盡,朱碧紺黃悉焚之,金身法相悉火之(3)李文海:《世紀(jì)之交的晚清社會(huì)》,北京: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頁。。”太平軍不僅毀壞佛教寺廟,還禁止僧侶進(jìn)行宗教活動(dòng),這對(duì)湖南等地的佛教事業(yè)造成了極大破壞。其次為了解決戊戌變法中提倡的辦新式學(xué)堂所需經(jīng)費(fèi)和場(chǎng)地問題,各地大規(guī)模征用寺廟地產(chǎn),湖南也不例外。“大率每一縣之寺觀,取十之七以改學(xué)堂,留十之三以處僧道;其改為學(xué)堂之田產(chǎn),學(xué)堂用七,僧道仍食其三(4)張之洞:《勸學(xué)篇·設(shè)學(xué)》,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1頁。。” “廟產(chǎn)興學(xué)運(yùn)動(dòng)”的開展,給佛教寺院經(jīng)濟(jì)以沉重打擊。此外,自鴉片戰(zhàn)爭(zhēng)以來,中國(guó)開始向西方學(xué)習(xí)的同時(shí)也貶低、否定、拋棄傳統(tǒng)文化,其中就包括對(duì)中國(guó)傳統(tǒng)宗教如佛教的批判。“一切宗教都是一種騙人的偶像:阿彌陀佛是騙人的……一切宗教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無用的騙人的偶像,都應(yīng)該破壞(5)任建樹:《陳獨(dú)秀著作選編》(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2頁。,”“反宗教運(yùn)動(dòng)”的日益發(fā)展,給湖南等地的佛教事業(yè)帶來了一定破壞。
民國(guó)初年,是湖南佛教在衰落中求生存的時(shí)期。面對(duì)社會(huì)上出現(xiàn)各種團(tuán)體,出版各種刊物,佛教界為了保護(hù)佛教徒的合法權(quán)益,為了向社會(huì)上傳播佛教文化,在當(dāng)時(shí)的政府政策允許范圍內(nèi),也組織了一些佛教團(tuán)體如中華佛教總會(huì)湖南支部、湖南佛學(xué)會(huì)、長(zhǎng)沙佛教正信會(huì)、湖南佛化會(huì)等。此外有些寺廟為了抵制“廟產(chǎn)興學(xué)運(yùn)動(dòng)”有不少寺院主持或法師自辦佛教學(xué)校培養(yǎng)僧伽人才如南岳佛學(xué)講習(xí)所、湖南佛學(xué)講習(xí)所等,有自辦出版機(jī)構(gòu)流通佛典如長(zhǎng)沙刻經(jīng)處等,也有組織各種公益慈善事業(yè)機(jī)構(gòu)為社會(huì)服務(wù)如湖南佛教慈兒院、寶慶佛教慈兒院等,還有開辦各種私立小學(xué)校如衡陽縣私立覺明小學(xué)校、湘潭私立海會(huì)小學(xué)校等。
(三)清末民初湖南慈善事業(yè)的發(fā)展
甲午戰(zhàn)爭(zhēng)前,由于湖南社會(huì)傳統(tǒng)性比較濃厚,因而此時(shí)的慈善事業(yè)仍以傳統(tǒng)慈善事業(yè)為主:在災(zāi)荒救濟(jì)方面,“救災(zāi)預(yù)災(zāi)的方法仍是倉儲(chǔ)、蠲免、賑濟(jì)、借貸、平糶、工賑等(6)周秋光:《湖南慈善史》,長(zhǎng)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72頁。;”在育嬰事業(yè)方面,既有官辦的育嬰機(jī)構(gòu),也有民間人士出資設(shè)立的育嬰機(jī)構(gòu),包括育嬰堂、保嬰會(huì)、就嬰局、育嬰局等多種形式;在養(yǎng)老事業(yè)方面,仍承襲清前期的恤老惠政;在恤嫠方面,清末湖南的恤嫠組織較多,“以省城長(zhǎng)沙為例,有全節(jié)堂、勵(lì)節(jié)堂、恤鄉(xiāng)嫠局、保節(jié)堂等,恤無告堂也兼收嫠婦(7)周秋光:《湖南慈善史》,長(zhǎng)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05頁。;”具有極強(qiáng)傳統(tǒng)色彩的慈善活動(dòng)——惜字,則只是一種精神理念,表達(dá)對(duì)傳統(tǒng)文人地位的維護(hù);在救生方面,清末湖南許多地方都設(shè)有救生局,主要是為了救援落水者和打撈浮尸;在喪葬慈善事業(yè)方面,清末湖南的助喪慈善機(jī)構(gòu),除專門的漏澤園、保骼堂外,還有許多綜合性善堂如長(zhǎng)沙同善堂、湖南零陵永善堂等;此外,義橋、義渡、義莊、義田仍然是這時(shí)期慈善事業(yè)重要組成部分。
甲午戰(zhàn)爭(zhēng)后,隨著真正向西方學(xué)習(xí)的開始,此時(shí)湖南的慈善事業(yè)也開始向近代慈善事業(yè)轉(zhuǎn)變。在維新變法期間,不少新的措施豐富了慈善事業(yè)的內(nèi)容:1898年4月創(chuàng)辦的具有公益性質(zhì)的湖南不纏足會(huì)旨在破除婦女纏足陋習(xí),但也救助弱勢(shì)群體;1898年成立的湖南保衛(wèi)局及其附屬機(jī)構(gòu)遷善所很大程度上著眼于社會(huì)公益事業(yè),具有公益性機(jī)構(gòu)特點(diǎn)。在清末新政時(shí)期:隨著中國(guó)歷史上首個(gè)管理民政事務(wù)的政府機(jī)構(gòu)民政部的設(shè)立,湖南設(shè)立首個(gè)民政分局;隨著湖南地方自治運(yùn)動(dòng)的開展,湖南地方自治遵循的清政府頒布的《城鎮(zhèn)鄉(xiāng)地方自治章程》的8項(xiàng)自治事宜中有6項(xiàng)設(shè)地方的贍養(yǎng)慈善事業(yè),正所謂“地方自治以專辦地方公益事宜(8)周秋光,曾桂林:《中國(guó)慈善簡(jiǎn)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45頁。;”慈善教育的興盛特別是女學(xué)的興辦以及新式義學(xué)的興辦也是這一時(shí)期慈善事業(yè)的新景象;此外,隨著傳教士傳教活動(dòng)的發(fā)展,包括教會(huì)醫(yī)療、教會(huì)慈幼在內(nèi)的教會(huì)慈善事業(yè)日益興盛。民國(guó)成立后,湖南紅十字會(huì)、湖南省城慈善事業(yè)公所、湖南省會(huì)貧民救濟(jì)會(huì)、湖南佛教慈兒院、湖南貧女院、湖南孤兒院等近代慈善事業(yè)機(jī)構(gòu)相繼成立。
二、清末民初湖南佛教慈善事業(yè)
(一)布施賑濟(jì)
施粥:寺廟在災(zāi)荒時(shí)期或一些傳統(tǒng)佳節(jié)期間布施窮人的傳統(tǒng)。最典型的屬臘八節(jié)施粥,湖南各地地方縣志都比較明細(xì)地記載一些寺廟在臘八節(jié)的時(shí)候布施臘八粥:“同治攸縣志、同治安仁縣志、同治武陵縣志、同治黔陽縣志、光緒衡陽縣志、民國(guó)常寧縣志等都記載在十二月時(shí)各地與佛教有關(guān)的主要風(fēng)俗為臘八粥(9)徐孫銘,王傳宗:《湖南佛教史》,長(zhǎng)沙:湖南出版社2002年版,第310-313頁。。”
災(zāi)害救濟(jì):“三湘四水”之地的湖南自然災(zāi)害頻發(fā)尤其是水災(zāi),因此時(shí)常會(huì)見有不少僧侶奔波在救災(zāi)一線,也有寺廟以廟產(chǎn)募捐賑災(zāi)或?yàn)闉?zāi)民提供住所、吃食。此外,在災(zāi)荒年間,寺廟也主動(dòng)為人們舉行祈雨、祈福消災(zāi)等祭告活動(dòng)以寬慰人心。
(二)慈善教育事業(yè)
清末民初,面對(duì)持續(xù)不斷發(fā)酵的“廟產(chǎn)興學(xué)運(yùn)動(dòng)”,為了緩和佛教與社會(huì)各界矛盾也為了體現(xiàn)佛教慈悲為懷宗旨,此時(shí)許多寺廟以及一些著名的僧人都舉辦了不少慈善教育機(jī)構(gòu)。
創(chuàng)辦各種僧學(xué)堂或佛學(xué)講習(xí)所:戊戌變法后,由日本僧人水野梅曉協(xié)助沙門笠云在長(zhǎng)沙開福寺開辦了“湖南僧立師范學(xué)堂”;“1922年南岳祝圣寺住持佛乘,得廣東一居士布施,在金雞林開辦一所僧人學(xué)校,初名‘衡山僧立僧學(xué)校’”(后改名為南岳佛學(xué)講習(xí)所)(10)湖南省志編纂委員會(huì)編:《湖南省志·宗教志》,長(zhǎng)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頁。; 1922— 1933年寶生任開福寺主持時(shí),又辦過湖南佛學(xué)講習(xí)所。這些僧學(xué)堂或佛學(xué)講習(xí)所,其學(xué)習(xí)環(huán)境優(yōu)良,設(shè)有圖書室、自修室等,藏書豐富,各種報(bào)紙雜志包括佛教刊物一應(yīng)俱全;授課內(nèi)容以佛學(xué)為主,兼講國(guó)文、英文等其他課程;招收或培養(yǎng)的學(xué)生大部分是一些青年僧侶;資金來源主要是各大寺廟的田租收入,還向各寺長(zhǎng)老和僧侶或男女居士募捐以彌補(bǔ)。
各省市的佛教界人士還創(chuàng)辦一些初級(jí)或高級(jí)小學(xué)校:1915年,湘潭縣創(chuàng)辦了湘潭縣私立海會(huì)小學(xué)校,“經(jīng)費(fèi)由海會(huì)寺、西禪寺、龍巖寺、五龍山大杰寺、佛子圖、白云峰六個(gè)寺廟攤派(11)湖南省志編纂委員會(huì)編:《湖南省志·宗教志》,長(zhǎng)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頁。;” 1918年,衡山縣由南岳各大寺院共同創(chuàng)辦了一個(gè)規(guī)模比較大的學(xué)校即衡山縣私立覺民小學(xué)校,原是初級(jí)小學(xué)后又改為高級(jí)小學(xué),校址在初創(chuàng)時(shí)設(shè)于衡山縣三元宮后又搬遷至南岳鎮(zhèn)云峰寺。這些初級(jí)或高級(jí)小學(xué)校,經(jīng)費(fèi)一般由當(dāng)?shù)負(fù)碛刑镒獾乃略撼袚?dān),校長(zhǎng)由各大寺院推選佛教界比較有代表性的人物擔(dān)當(dāng),招收或培養(yǎng)的學(xué)生一般都是當(dāng)?shù)氐男『ⅲ毮芘c現(xiàn)在的小學(xué)已比較接近,這對(duì)于當(dāng)?shù)氐奈幕逃聵I(yè)可謂是一大支持。
(三)佛教慈善機(jī)構(gòu)
各佛教寺院除開展一些佛教慈善教育事業(yè)外,還創(chuàng)辦一部分慈善資助機(jī)構(gòu)和慈善醫(yī)療機(jī)構(gòu)如湖南佛教慈兒院、寶慶佛教慈兒院、湖南省佛教會(huì)慈濟(jì)醫(yī)院等。
湖南佛教慈兒院,1915年由湖南佛教界全體出資設(shè)立于長(zhǎng)沙開福寺,以“收養(yǎng)孤貧兒童授以國(guó)民教育兼習(xí)各種工藝俾能獨(dú)立謀生為宗旨(12)武昌佛學(xué)院:《海潮音》,武昌:正信印書館1922年版,第84頁。。”其經(jīng)費(fèi)來源除開辦時(shí)發(fā)起人所捐助外分兩種:平常的費(fèi)用“由湖南省佛教總會(huì)就各地方寺廟宗教財(cái)產(chǎn)項(xiàng)下酌量勸捐認(rèn)定之但已經(jīng)捐款辦有慈善事業(yè)或教育事業(yè)而力難再捐者不在此限(13)武昌佛學(xué)院:《海潮音》,武昌:正信印書館1922年版,第86頁。,”而臨時(shí)經(jīng)費(fèi)來源于各界捐款或各寺院除常年捐款之外的特別捐助。由此可見,湖南佛教慈兒院的大部分經(jīng)費(fèi)來源于廟產(chǎn),其所從事的是收養(yǎng)孤兒并對(duì)其進(jìn)行知識(shí)教育以使其能謀生等慈善工作。
寶慶慈兒院,1926年由邵陽縣點(diǎn)石庵沙門出塵創(chuàng)立于濟(jì)傳庵,“共收容孤兒100余名,施以小學(xué)教育,并教縫紉、織布、制造毛筆、粉筆等生產(chǎn)技能(14)湖南省志編纂委員會(huì)編:《湖南省志·宗教志》,長(zhǎng)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頁。。”
湖南省佛教會(huì)慈濟(jì)醫(yī)院,湖南省佛教會(huì)在長(zhǎng)沙該會(huì)辦事處內(nèi)設(shè)立的“以博愛普濟(jì)中西兼醫(yī)利樂人群為前提”“以我佛慈悲療治疾病為宗旨”的慈濟(jì)醫(yī)院(15)中國(guó)佛教會(huì):《中國(guó)佛教會(huì)報(bào)》第七、八、九期合刊,上海:國(guó)光印書局1930年版,第66-67頁。。該院所聘醫(yī)士以曾畢業(yè)于各省中西各醫(yī)校并且經(jīng)各省公安局考驗(yàn)登記合格者為主,經(jīng)費(fèi)來源于發(fā)起人(即湖南省佛教協(xié)會(huì))或募捐所得,其施診時(shí)一概不收取任何費(fèi)用。
(四)佛教居士慈善事業(yè)
清末民初,在國(guó)家危亡之際,有不少政界、軍界、商界人士因苦苦追尋救國(guó)救民之路無果,轉(zhuǎn)而成為佛教居士,積極投身慈善事業(yè),救難濟(jì)貧。其中湖南的熊希齡就是一個(gè)典型代表,多年的宦海沉浮使他對(duì)政治深感失望,于是他準(zhǔn)備皈依佛教,其信佛后,法名妙通,自署“雙清居士”。但是熊希齡皈依佛教并不是出世以逃避現(xiàn)實(shí),而是他決意遠(yuǎn)離仕途的表現(xiàn),準(zhǔn)備以佛家大慈大悲精神從事社會(huì)慈善與教育等公益事業(yè)。對(duì)于家鄉(xiāng)湖南的災(zāi)難救助,熊希齡就曾多次為之奔波:“1918年4月3日,會(huì)同旅京湘人范源濂、郭宗熙等,聯(lián)名向全國(guó)發(fā)出為湘省兵災(zāi)乞賑通電”,“1918年4月18日,他邀同旅京湘人,在石駙馬大街本宅成立一賑湘機(jī)構(gòu),定名為‘湖南義賑會(huì)(16)周秋光:《熊希齡傳》,北京:華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442頁。’;”為了籌集賑款,他提出四點(diǎn)建議——將他保管的米鹽公股到期的證券換現(xiàn)、開辦慈善救濟(jì)獎(jiǎng)券、臨時(shí)救濟(jì)安撫災(zāi)民并以工代賑、請(qǐng)全國(guó)慈善機(jī)關(guān)聯(lián)合維持湘賑。通過以上辦法和措施,湘賑得以最終告竣,有了大批錢糧進(jìn)入湘,使湖南災(zāi)民得以渡過兵災(zāi)以及水旱災(zāi)害帶來的困境。
(五)其他
除上述所述慈善事業(yè)外,清末民初湖南的各寺廟及佛教界人士還從事其他活動(dòng):首先是放生,即將被捕獲的魚、鳥等放之于山野或池沼之中,使其不受人宰割、烹食。因?yàn)榉鸾绦麚P(yáng)“眾生平等”,每個(gè)物種包括人、動(dòng)物等都有在這世上生存的權(quán)利,因此他們嚴(yán)禁殺生、提倡素食。每次浴佛節(jié)后,各寺廟都會(huì)組織一些放生活動(dòng),一些寺院還修建了放生池。其次是進(jìn)行慈善宣傳,如舉辦法會(huì)等號(hào)召人們向善,多做善事才能“好人有好報(bào)”。此外還有修橋補(bǔ)路、造船義渡、開設(shè)義莊(即免費(fèi)存放尸骨的場(chǎng)所)等從事公共基礎(chǔ)設(shè)施的建設(shè)。
三、簡(jiǎn)評(píng)清末民初湖南佛教慈善事業(yè)
(一)清末民初湖南佛教慈善事業(yè)的特點(diǎn)
以中日甲午戰(zhàn)爭(zhēng)為節(jié)點(diǎn),甲午戰(zhàn)爭(zhēng)之前的湖南佛教慈善事業(yè)仍以傳統(tǒng)慈善為主,而甲午戰(zhàn)爭(zhēng)之后的湖南佛教慈善事業(yè)已經(jīng)具有近代慈善事業(yè)的一些特征。正如之前所提到的,1840年的鴉片戰(zhàn)爭(zhēng)以及之后持續(xù)30年之久的洋務(wù)運(yùn)動(dòng)未給湖南社會(huì)帶來多大改變,此時(shí)的湖南仍是以傳統(tǒng)社會(huì)為主,在此影響下的湖南佛教慈善事業(yè)也仍延續(xù)了自古以來的傳統(tǒng)。但是自從甲午戰(zhàn)爭(zhēng)后湖南的慈善事業(yè)開始向近代化轉(zhuǎn)型之后,湖南的佛教慈善事業(yè)也隨之進(jìn)行了變革。
1.廣度的變化即慈善事業(yè)的開展開始突破地域局限。甲午戰(zhàn)爭(zhēng)之前各個(gè)寺廟各自辦事,沒有突破地域局限;而甲午戰(zhàn)爭(zhēng)之后一些佛教界著名人士和寺廟開始聯(lián)合起來從事一些比較大型的慈善事業(yè),如湘潭縣的湘潭縣私立海會(huì)小學(xué)校就是由海會(huì)寺、西禪寺、龍巖寺、五龍山大杰寺、佛子圖、白云峰6個(gè)寺廟聯(lián)合創(chuàng)辦的,湖南省佛教會(huì)慈濟(jì)醫(yī)院就是湖南省佛教會(huì)創(chuàng)立的。
2.深度的變化即慈善事業(yè)的實(shí)施開始有組織、有目的、有紀(jì)律。甲午戰(zhàn)爭(zhēng)前湖南佛教所做的一些慈善事業(yè)大部分都是諸如施粥、募捐、祈福、放生等一些臨時(shí)救濟(jì);而甲午戰(zhàn)爭(zhēng)后一些寺廟開始創(chuàng)辦僧學(xué)堂、講習(xí)所、小學(xué)以從事善教育事業(yè),開辦慈兒院以收養(yǎng)并教育孤貧兒童,開辦慈濟(jì)醫(yī)院以無償救助傷患。
3.救濟(jì)對(duì)象的變化即救助對(duì)象范圍更廣、需要救助的群體增多、救助對(duì)象日益復(fù)雜。甲午戰(zhàn)爭(zhēng)前,由于湖南社會(huì)封建性仍十分濃厚,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解體十分緩慢,再加上安土重遷傳統(tǒng)思想影響, 此時(shí)的湖南佛教慈善其救濟(jì)對(duì)象主要限于該寺廟所在當(dāng)?shù)氐呢毨巳海患孜鐟?zhàn)爭(zhēng)后,隨著西方文化的大量沖擊和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解體的迅速加劇、戰(zhàn)爭(zhēng)頻發(fā)、人口流動(dòng)頻繁,加上湖南許多佛教慈善團(tuán)體的建立,因此,救助對(duì)象不僅限于當(dāng)?shù)氐娜藗儯€包括外地許多流民和社會(huì)底層的弱勢(shì)群體。
4.資金來源的變化甲午戰(zhàn)爭(zhēng)前,湖南佛教所進(jìn)行慈善活動(dòng)的經(jīng)費(fèi)主要來源于寺廟收入,包括封建政府賞賜、寺廟出租土地的收入以及香客的捐贈(zèng);甲午戰(zhàn)爭(zhēng)后,隨著湖南一些佛教慈善機(jī)構(gòu)的創(chuàng)立,其資金大多來源于社會(huì)募捐、機(jī)構(gòu)的經(jīng)營(yíng)收入或是會(huì)員的會(huì)費(fèi)。
5.慈善事業(yè)綜合性突出并發(fā)揮了很大作用甲午戰(zhàn)爭(zhēng)前,各個(gè)佛教寺廟只“就事而論事”,救助具有專門針對(duì)性,如對(duì)無家可歸者提供住宿、對(duì)貧窮者給以錢財(cái)、對(duì)饑餓者施以飯食。甲午戰(zhàn)爭(zhēng)后,佛教開辦的許多機(jī)構(gòu)都具有綜合性,如創(chuàng)辦的湖南佛教慈兒院、寶慶慈兒院除收養(yǎng)孤兒外還教他們識(shí)字及謀生技能。
6.佛教居士慈善事業(yè)的興起甲午戰(zhàn)爭(zhēng)前從事佛教慈善事業(yè)的主要是寺廟僧侶,而甲午戰(zhàn)爭(zhēng)后以熊希齡為代表的一部分湖南佛教居士開始以居士團(tuán)體或佛教機(jī)構(gòu)為依托,積極投身社會(huì)公益慈善事業(yè),開展賑災(zāi)、助學(xué)、濟(jì)貧等多種類型的慈善活動(dòng)。
(二)清末民初湖南佛教慈善事業(yè)的影響
1.對(duì)湖南佛教的影響一方面,“廟產(chǎn)興學(xué)”運(yùn)動(dòng)的發(fā)展使人們把目光盯在了各寺廟的廟產(chǎn)上,而寺廟主動(dòng)把自己的土地、錢財(cái)?shù)蓉暙I(xiàn)出來用于修建學(xué)校、創(chuàng)辦慈善機(jī)構(gòu)等社會(huì)公益事業(yè),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護(hù)教護(hù)產(chǎn),維護(hù)湖南佛教的生存地位。另一方面,在社會(huì)反宗教的思潮影響下,佛教在進(jìn)行慈善活動(dòng)的同時(shí)弘揚(yáng)佛法,向?yàn)?zāi)民等宣傳佛教知識(shí),消除社會(huì)上人們對(duì)佛教產(chǎn)生的一些誤會(huì),這有助于減少人們對(duì)佛教的抵制與仇恨,維護(hù)湖南佛教在人們心中的美好形象,在民眾中重塑了佛教濟(jì)世的印象。此外,在當(dāng)時(shí)其他宗教特別是基督教在中國(guó)大地日益盛行的情況下,佛教所做的慈善事業(yè)有利于提高佛教在人們心中的地位,從而更有助于湖南佛教于基督教、道教等競(jìng)爭(zhēng)中取得優(yōu)勢(shì)。
2.對(duì)湖南社會(huì)的影響面對(duì)清末民初湖南社會(huì)的動(dòng)蕩不安,人們時(shí)刻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佛教所做的慈善事業(yè)彌補(bǔ)政府力所不能及之處,救助了處于中國(guó)社會(huì)底層的蕓蕓眾生,從而有利于安定人心、維護(hù)社會(huì)團(tuán)結(jié)和政權(quán)穩(wěn)定。
3.對(duì)湖南佛教慈善事業(yè)發(fā)展進(jìn)程的影響面對(duì)自鴉片戰(zhàn)爭(zhēng)以來尤其是中日甲午戰(zhàn)爭(zhēng)之后湖南社會(huì)的急劇變化,湖南的慈善事業(yè)發(fā)生了轉(zhuǎn)變,相應(yīng)地湖南的佛教慈善事業(yè)也必然出現(xiàn)變革:不再因循守舊而是采取許多新措施,推動(dòng)了湖南佛教慈善事業(yè)的復(fù)興與近代化歷程。
(三)清末民初湖南佛教慈善事業(yè)的啟示
清末民初,面對(duì)處于向近代化轉(zhuǎn)型關(guān)鍵時(shí)期的湖南社會(huì),湖南佛教慈善事業(yè)的一系列舉措給當(dāng)今湖南以及中國(guó)佛教慈善事業(yè)的發(fā)展留下了經(jīng)驗(yàn):1.順勢(shì)而變。清末民初湖南佛教慈善順應(yīng)社會(huì)變化而進(jìn)行的一些改革使其逐漸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啟示現(xiàn)如今的佛教慈善團(tuán)體面對(duì)中國(guó)改革開放深入發(fā)展的需求應(yīng)當(dāng)做出相應(yīng)調(diào)整,從而更好地服務(wù)社會(huì)及弘揚(yáng)佛法。2.勇于創(chuàng)新。清末民初湖南的佛教敢于實(shí)踐,創(chuàng)辦諸如僧學(xué)堂、佛教慈兒院等自古以來沒有出現(xiàn)過的慈善機(jī)構(gòu),這種創(chuàng)新精神值得如今佛教慈善團(tuán)體學(xué)習(xí)。3.走出去。清末民初的湖南寺廟敢于走出一縣、一鄉(xiāng)的地域局限而走向全省,這就啟示如今的佛教團(tuán)體要勇于走出一市、一省的地域局限而走向全國(guó)甚至全世界。4.多元化。清末民初湖南佛教所從事的慈善事業(yè)不局限于單種形式,而是賑災(zāi)、助學(xué)等多方面發(fā)展,這啟示如今的佛教慈善事業(yè)也要善于采用多種多樣的救助方式,滿足不同社會(huì)人群需求。
雖然清末民初湖南佛教的慈善事業(yè)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不足之處,這給當(dāng)今佛教慈善事業(yè)的發(fā)展留下了教訓(xùn):第一,從清末民初湖南佛教進(jìn)行的一些社會(huì)公益事業(yè)或創(chuàng)辦的慈善機(jī)構(gòu)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這其中的絕大多數(shù)都只是佛教界人士在四處奔走、組織運(yùn)行,他們很少想到去和政府部門或其他慈善團(tuán)體合作共同舉辦慈善活動(dòng),這啟示如今的佛教慈善團(tuán)體應(yīng)積極尋求政府幫助以及其他相關(guān)慈善機(jī)構(gòu)的合作,要注意建立全國(guó)性統(tǒng)一的佛教慈善機(jī)構(gòu),大家齊心協(xié)力促進(jìn)中國(guó)的慈善事業(yè)良性發(fā)展;第二,清末民初的湖南佛教在進(jìn)行慈善活動(dòng)的時(shí)候也存在私吞捐款為自己建廟、造佛像等自私違法行為,這啟示現(xiàn)今的佛教慈善機(jī)構(gòu)要加強(qiáng)監(jiān)管,做到慈善公開化、透明化,讓佛教慈善真正造福社會(huì)。
此外,完善佛教慈善的法律法規(guī)及規(guī)章制度建設(shè)、提高佛教慈善組織的公信力、加強(qiáng)佛教慈善事業(yè)的專門化建設(shè)、注意培養(yǎng)人民的慈善意識(shí),這也是清末民初湖南佛教慈善事業(yè)的發(fā)展對(duì)當(dāng)今佛教慈善事業(yè)的啟示。
四、結(jié) 語
佛教慈善事業(yè)方興未艾,而關(guān)于佛教慈善研究任重道遠(yuǎn)。本文僅從背景、內(nèi)容、意義三方面大致勾勒出清末民初湖南佛教慈善事業(yè)發(fā)展的面貌,遭逢亂世,湖南佛教以其濟(jì)世救人的慈悲情懷積極投入社會(huì)公益慈善事業(yè),興辦教育、賑災(zāi)濟(jì)貧,與國(guó)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運(yùn),譜寫了慈善救濟(jì)的一曲贊歌。雖然清末民初湖南佛教慈善在當(dāng)時(shí)的時(shí)代背景下所取得的成就畢竟有限,但這有限的成就及其所反映的問題對(duì)當(dāng)今湖南以至中國(guó)佛教慈善事業(yè)的發(fā)展意義重大,在如今中國(guó)面臨大發(fā)展大變革的形勢(shì)下,如何正確地借鑒和吸收這些經(jīng)驗(yàn)與教訓(xùn),是現(xiàn)代佛教慈善事業(yè)所需要考慮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