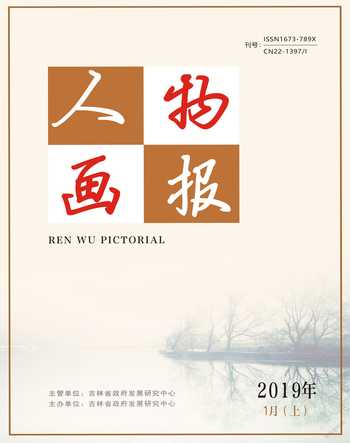博物館參與式展覽的觀眾體驗研究
摘 要:博物館作為一個公眾社會組織,其許多活動都必須在觀眾參與體驗下進行,可以感受到在展覽和活動的設計過程中,觀眾自身的參與和表達成為活動的重要構成部分。本文從觀眾體驗角度切入,分析博物館參與體驗角度的轉變,以探究博物館的展覽設計與觀眾體驗之間的主動與被動關系,提高觀眾參與熱情,發揮博物館公共教育功能,以思考博物館體驗更多的可能性。
關鍵詞:展覽設計;公眾參與;娛樂化
一、博物館展覽發展中的觀眾參與度變化
目前博物館參觀方式來看,各個博物館比較常見的是“一對多”傳統靜態參觀形式。展覽參觀觀眾的年齡層比較集中,大部分是教育水平較高的專業人員和院校學生,普通民眾人數比例相對較小,這種現象在二三線城市尤為明顯。隨著技術的發展,互動類型的展覽應運而生。就現場情況來看,展覽的觀眾群變得相對寬了一些,展覽現場不僅有家庭群體,同時還有六七十歲的老人以及年輕學者。
21世紀博物館、美術館以及劇院等文化機構不再是以往莊重肅穆的神殿,博物館從單一同構型的“大眾”轉變成“社區”的公共大眾平臺,博物館會更注重觀眾互動體驗的多元化。
近年來我們見證了博物館為了吸引觀眾,越來越多的使用可以互動的展覽項目。互動類型展覽的盛行標志著展覽體驗由審美轉向體驗,由靜觀轉向互動,對于這一展覽趨勢,博物館學家彼得·馮·門施曾說:第三次博物館革命發生在2000年,也就是我們正在經歷的。雖然我們還沒對它正式命名,但其關鍵詞就是“參與”[1]。參與式展覽圍繞主題運用各種多媒體技術手段設計情境,借助游戲、情景模擬的手段,鼓勵觀眾動手動腦參與展覽,將觀眾從被動的觀看過程轉變成一個欣賞、發現與思考的雙向傳播體驗學習過程。在參觀的過程中加入觸覺的有形參與,這讓觀眾體驗互動不僅僅是簡單的信息表達和傳輸,同時聚焦于身體交互、以及創造力的設計互動,并在實踐中具體化為行動。
二、博物館展覽設計中觀眾體驗的主動與被動
博物館作為教育學習的第二課堂,具有自由選擇的、非正式情境的雙重教育特質,如何滿足觀眾的需求,如何把這種博物館教育特質發揮到最大?博物館展覽設計如何滿足觀眾學習、探求實踐、欣賞的需求,是博物館設計目前最關心的話題。本章節分析的是在展覽設計上如何調動觀眾參與主動性,以期達到博物館參與體驗的最佳效果。
(一)觀眾被動觀看
傳統展覽形式圍繞展品內容的進行靜態展示,展覽設計類似于學校課程理念,以流線式方式展開。觀眾的參觀方式也是跟隨講解員解說被動的參與。但是就現場情況來看,參觀者并不一定規矩的按照策展人設計的路線解讀展品,這種行為被特芮南稱為“主動的閑散”和“文化逛街”。傳統的展覽的觀看時間和學習效果取決于觀眾本身的知識和經驗儲備,同時也取決于觀眾自我學習的興趣。觀眾在展覽扮演被動接受者的角色,觀眾與展品之間的互動存在于觀眾自主選擇,也就是說觀眾與博物館的關系是分離的。
近年興起的沉浸式展覽打破傳統展覽平面、沉靜的體驗感,將新媒體技術應用到展覽當中,強烈的聲光電的視覺沖擊,觀眾會產生時間和空間上的游離感,產生強烈的視覺效應。例如2019年7月在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辦的“心靈的暢想—梵高藝術沉浸式體驗”就是一個沉浸式的展覽,現場將梵高的藝術作品投影到墻壁上循環播放,同時與畫作一起播放的還有或悠揚或悲戚的音樂,大面積的動態畫面調動多感官沉浸式體驗感和觀眾參與積極性。沉浸式展覽表面看來是由大眾傳媒帶來的圖像動態化、流動性,實質上觀眾被刻意的視覺技術控制,并且在圖像刺激的重壓之下容易產生逃避圖像的沖動。觀看者被觀看對象控制,圖像通過對觀看者欲望的捕捉控制了主體,使其在不知不覺間服從了圖像所傳達的意志,在我看來,沉浸式展覽的觀眾參與度仍然有待考究。
上述二種情況,傳統流線式展覽以及沉浸式展覽的展覽方式其實質都是被動的,背后缺失社會脈絡和環境脈絡的考量[2],缺乏個人、社會、環境的綜合考慮。單向的展覽設計致使觀眾與觀眾之間的交流幾乎為零,觀眾實際參與度不高。
(二)展覽設計的觀眾主動參與
隨著社會的發展,博物館核心問題是如何做到更具開放性和參與精神。美國博物館協會在1992年的《卓越與平等》報告中就指出:博物館是觀眾與觀眾、觀眾與實物進行交流的場所,并通過相互影響來增進體驗[3]。
1、物與人:參與地點的重新審視
博物館參與式體驗設計的優勢在于采用多種手段調動觀眾的積極性,建立信息雙向流通渠道,當傳播者將展示信息公開后,觀眾可以對展示信息做出反應,并在現場將信息反饋給原傳播者,這樣就有了雙向互動特性的信息傳播方式,縮短了博物館與觀眾之間的距離,觀眾擁有了“現場表達”的權利。
在肯塔基的國家童子軍博物館其中一個影院,觀眾可以扮演偵探的角色尋找一名失蹤兒童,劇情將依照觀眾的選擇來發展,大家投票的結果就是下面將要播放的內容。童子軍博物館這種播放影片的設計模式,故事情節由觀眾意愿推動,充分調動了觀眾的積極性。以這樣一個方式觀眾真正參與到展品的展示和傳播當中來,取代了僅僅是專家才有闡釋博物館作品的特權,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博物館民主化的體現。觀眾在自主探究的過程中,發現展覽與知識之間的關聯,在博物館交互中創造新的內容。博物館與觀眾這種傳統的傳播者與接受者的關系越來越模糊,觀眾體驗從我變成了“我們”。博物館體驗從單向的、被動的體驗轉向多元的、雙向的參與式體驗。
2、人與人:觀眾與觀眾之間的社交雙向傳播
博物館為觀眾提供了創作、分享并于他人交流的場所[4],互動體驗不僅存在觀眾與展品的互動,也存在于觀眾與觀眾之間的社交[5],而參與式展覽就為觀眾與觀眾之間的交流提供了實用性的空間[6]。
雷安德羅·埃利希在中央美術學院重新制作并呈現的“太虛之境”是一個典型的參與式展覽。展覽利用裝置、現成品、雕塑、視頻,甚至音樂等媒介和視聽覺形式,成功制造了眾多挑戰我們感知慣性的文化景觀。“太虛之境”《游泳池》作品是一個懸浮在空中的裝置,仿佛人在另一個時空里漫游,如果沒有其他觀眾的參與,岸上的觀眾無法完整的感受水池底下的波動。可以說,參與式展覽實現了由我到我們的社交式體驗,觀眾變成是展覽的創作者、傳播者、消費者。
“太虛之境”的另一個作品《建筑》也把觀眾的參與度充分調動起來。其靈感來自于唐人街的經典招牌和防火外墻,通過唐人街反射國人的生活,采用鏡子為投射載體,反射出一個立體的中國城鏡像。在活動體驗過程中,觀眾在地面的門窗之間坐躺等活動動作,鏡子會反射出來,這時觀眾自己的身體又和圖像之間形成新的關系。觀眾在參與過程中,不僅能夠看到自己,也與其他參觀者共同組場景,當參與人數不斷增多時,才能體現展覽的最佳效果。此時地面上的磚磚瓦瓦已經不重要了,是觀眾自己的創造給他們帶來愉悅感,也是觀眾與觀眾之間的互動交流帶來的社交體驗,因而藝術家的設計就成了觀眾進行創造的平臺,為觀眾自己的表達帶來了更多的可能性。“太虛之境”打破傳統展覽觀眾被動旁觀者的狀態,觀眾成為展覽的參與者、貢獻者。展品不是放在櫥窗中的圣物,觀眾可以觸摸展品,也可以進行互動,觀眾變成展覽的一部分。
總的來說,參與式展覽促使觀眾與展品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傳統博物館與觀眾的關系認為:博物館是傳播者,觀眾是接受者;參與式展覽觀眾的關系認為:觀眾是生產者和創造者。傳統博物館的觀看方式依賴文本的闡釋,這使得闡釋本身受展覽內容的限制。而參與式展覽為觀眾提供多維度的感知,而非單純閱讀,互動體驗作為博物館觀看的補充。可以說參與式展覽為觀眾提供了思考的空間以及客觀解釋的機會。
三、參與式展覽中藝術體驗與娛樂化的考量
娛樂功能是博物館既定存在的功能,娛樂化與藝術體驗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在《學自博物館》中,作者約翰·赫·福克和林恩·迪·戴爾金就提到,沒有明顯證據表明觀眾去博物館的目的是要么學習、要么娛樂;幾乎毫無例外的是,觀眾都是兼顧學習和娛樂的。去博物館的個體是尋求一種學習導向的娛樂體驗[7]。博物館參與式體驗的愿景是不僅能讓觀眾僅獲得體驗與快樂,更重要的是讓觀眾在娛樂中獲得深層次的思考和感悟,并在這種愉悅中加深這種體驗,激發進一步的學習。
參與式展覽借助游戲、情景模擬的手段,在公共領域展開的一種敘事性體驗,大大提高了展覽的參與性、趣味性,寓教于樂,達到交流和操作的作用。在這里需要反思的是:參與式展覽的娛樂方式是否恰當,或者說過度的娛樂化是否造成展覽的孤立和知識的獲取困難。參與體驗怎樣能避免過分娛樂而不丟失博物館本質特征,又能達到與其他游樂場等娛樂場截然不同的要求,盡力做到在娛樂中學習,達到寓教于樂的效果。這個問題是博物館人員一直思考的問題,也是未來博物館發展的趨勢,是博物館人一直追求的目標。另外,博物館也應該擴大觀眾的參與空間范疇,不僅局限于參觀過程,在參觀前展覽設計和參觀后展覽效能評量中也加入觀眾參與,共同營造公眾滿意的博物館。
參考文獻:
[1](美)妮娜·西蒙.參與式博物館:邁入博物館2.0時代[G].喻翔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1.
[2]福爾克和戴爾金在《博物館體驗》中提出“互動體驗模式”,認為博物館體驗是個人和社會、環境共同作用的結果。
[3]美國博物館協會主編.博物館教育與學習[G].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4.
[4](美)妮娜·西蒙.參與式博物館:邁入博物館2.0時代[G].喻翔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4.
[5]葛伯恩(NelsonGraburn)認為人們期待博物館要充滿三個重疊的經驗之需求其中之一就是社交(一種社會經驗的分享).
[6]70年代,地理學家SheldonAnnis發表了一篇文章,描述觀眾反應的三個共存的層次之一就是:實用性的空間(社交互動的場域).
[7]常丹婧.“博物館娛樂”的特性及誤區談.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博物館》2019年第一期.
作者簡介:
張冰(1996.1.14)女,漢族,山東省,單位:山東藝術學院,學位:碩士,職位:學生,研究方向:美術教育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