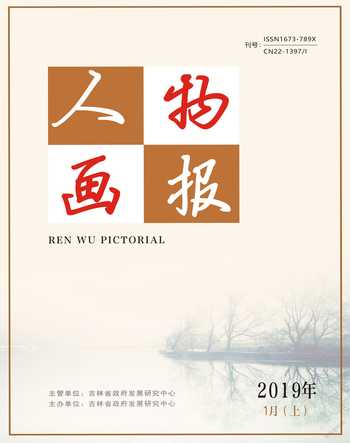再論《孫子兵法》之“不戰而屈人之兵”
袁毅
摘 要:在逐步靠近世界舞臺中央的過程中,中國始終高舉“愛好和平”的大旗,先后提出“親、誠、惠、容”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新型周邊外交方案,強調中國發展對亞洲乃至世界來說,是機遇而非挑戰。面對群雄環伺的挑戰,中國也從未忘記“兵者,國之大事”,在緊抓練兵備戰、自強御侮的同時,以古代 “兵經”《孫子兵法》為綱,塑造“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大格局,全力維護世界和平,樹立中國態度。
關鍵詞:再論;《孫子兵法》;“不戰而屈人之兵”
一、不戰而屈人之兵,重在“屈人之兵”而非“不戰”
關于《孫子兵法》的二次解讀往往將“不戰而屈人之兵”作為它的統領思想,然而從作者將這一思想放在全書的第一部分,而不是貫穿全書的論述方法,就可以看出,“不戰而屈人之兵”更多是一種理想目標或者邏輯起點,而非一以貫之的戰爭形態。
一是力戒窮兵黷武式的好戰。從理想目標看,“不戰而屈人之兵”并非作者的獨特見解,更多的是對他所處時代逐漸弱化的“圣賢尚德治天下”范式的深刻反思。任何偉大思想的誕生都離不開特定的時代背景,孫武所處春秋時代是諸侯紛爭兼并,“好戰者亡、怠戰者亦亡”的的歷史大舞臺。作者經歷了吳國衰而興,興而再衰的大國悲劇,發出“兵者,國之大事,不可不察”的哀嘆,更多的是對“興,百姓苦,亡,百姓苦”戰爭之罪的惋惜。面對戰與不戰的選擇,作者所持的應當是盡可不戰的美好愿望,針對的是窮兵黷武的惡果,而并非戰術意義上的“不戰”。二是不打無準備之仗。從邏輯起點角度看,現代戰爭尤其大國之間對抗,依然長期表現為通過戰略威懾達到“屈人之兵”的基本狀態,避免核心利益遭到實質性的侵犯或者破壞。我們的對手,正是通過長期保持軍事實力的絕對優勢震懾對手,或者通過局部有限戰爭的連續介入塑造其統治地位。然而,我們不能忘記孫武在其著作里依然提到: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提示我們控制規模與時間跨度至關重要,這取決于對戰局的主導,而并非委曲求全。因此,只有在進行了充足準備,對戰局有了較為充分的預估和判斷,才能邁出求勝的第一步。三是明確終極勝戰目的。從制定切實可行的戰略目標角度講,我們所謂的勝戰究竟是如何定義的、達到怎樣的態勢是終極目的非常關鍵。我們是要擊敗對手還是毀傷對手,又或者僅僅達到拒止阻嚇的效果,必須有可控的把握,而不是根據戰局的發展而輕易退縮或冒進。在這里,“不戰而屈人之兵”應當更多指有效拒止,而非全勝。只有盯著這一終極目標,擁據“九地”優勢,集中區域力量達成有限毀傷目標,而非專注于嘗試“破擊體系、打敵要害”的正面對抗而取得全勝的結果,才能成就全局。
二、有限區域拒止,重在“拒止”而非“有限”
區域拒止是我們實施的一種旨在限制戰爭規模的高維度戰略規劃,力圖將戰爭限定在可控態勢之下。《孫子兵法》當中亦有“故善出奇者,無窮于天地,不竭如江河”。二者互為補充,相得益彰。
一是面對強敵設置有限拒止目標。欲以奇勝,先以正合。正面戰場的實力相對均衡依舊是爭取戰機的前提基礎,我們需要居安思危,積極練兵備戰,不斷提升全面反介入的體系建設。同時我們的拒止目標不能簡單得定義為防止敵方軍事力量的區域介入,而是從整體上遲滯或者阻止其大規模建制力量的投入,進而如毛主席所說的那樣:攥緊拳頭,對敵人各個擊破。二是在有限區域采取超限戰法。《孫子兵法》在九地篇將用兵之地做了分類,如爭地、交地、死地等,說明敵我雙方在同一地域可以倚重不同的優勢條件。由此,基于優勢實施靈活機動的任務式指揮,對于區域拒止就顯得格外重要。換句話說,要在能力所及的非地理范疇的無限空間內尋求戰機。三是確保局部絕對優勢,力求全勝。在區分地理有限空間和能力所及的無限空間概念基礎之上,確定打擊目標依然是至關重要的一環。否則,游擊戰就可能演變為匪擊戰,寄希望于漫無目的的意外遭遇,始終無法達成嚇阻對方的戰略目的。《孫子兵法》認為要畢其功于一役是理想狀態,而在戰術層面,作者更加強調的是攻其不備。這種情況下,跳出地理上的有限區域,在主戰場之外形成某一點的絕對優勢可能具備更高效費比。
三、蘊勝戰之道于勝戰之念
《孫子兵法》作戰篇中有這樣的論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縱觀人類戰爭史,從來沒有一廂情愿的和平,當那一天真的來臨,我們要有勝戰之念,更要有勝戰之道。
一是以逸待勞,打好陣地戰。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后處戰地而趨戰者勞。這里所說的以逸待勞是自古以來兵家常識,那么如何創造以逸待勞的環境就成為決定戰局的關鍵。我們奉行積極防御的戰略,但片面認為我們具備以逸待勞的條件是非常危險的。打贏戰爭對于我們來說,首當其沖是使陸基防御體系成為整個戰場環境的閉環中的一節,進而打好陣地防御以謀求綜合優勢。二是虎口奪食,經略運動戰。將防御體系納入戰場中心區將大大增加“先處戰地”的優勢,那么如何做到“敵佚能勞之,飽能饑之,安能動之”呢?如果僅僅停留在堵截的層面,勢必冒失敗風險。認識到這一點并非要退卻,而是督促我們進行更加縝密的情報收集、判讀及決策工作,在關鍵節點迎險而上、險中求勝。粟裕大將就坦誠自己曾因為所處環境極其險惡,打了一些冒風險的仗。但是在特定時期,冒險可能是最優選項,重要的是認識風險使得指揮員更加“慎戰”,某種角度又降低了風險的概率。 三是奇兵制勝,精打游擊戰。孫子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在外圍形成有效毀傷是運用“奇兵”的終極目標,圍繞這一方針我們可以在對手的后方與前線的戰略通道中開展廣泛的游擊戰,從而迫使對方回援或后置部署,從而提高我軍在有限環境有限時間內達成進攻目的的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