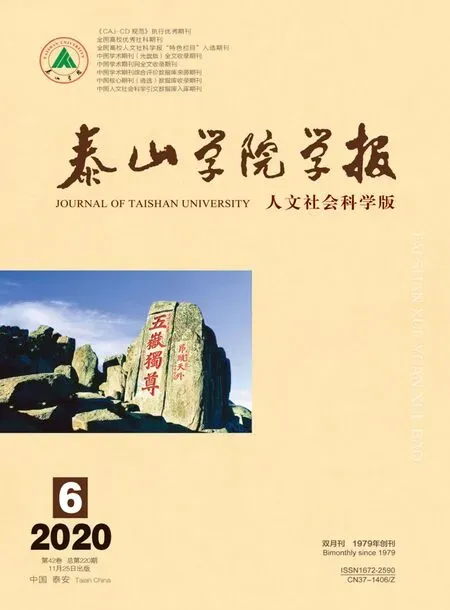黨建視角下抗戰時期山東鋤奸糾錯工作再審視
張業賞
(山東農業工程學院,山東 濟南 250100)
鋤奸工作是抗日戰爭時期中華民族抗日斗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抗戰全面爆發后,山東各級黨組織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厲行鋤奸運動的部署,將鋤奸工作作為一項政治性極強的技術性工作。但由于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山東鋤奸工作也曾犯過嚴重錯誤。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在恢復黨的實事求是路線之后,山東省各級黨組織對抗戰時期山東鋤奸錯案進行了全面調查處理,明確了錯誤的性質,予以徹底平反糾正。抗戰時期山東鋤奸錯誤自發生至完成糾正、平反,歷時近五十年時間,其曲折復雜的過程及其經驗教訓頗有借鑒意義。本文試以黨建角度,分析研究其中蘊含的經驗教訓,為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加強黨的建設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啟迪。
一、實事求是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思想基礎
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是黨的基本思想方法、領導方法、工作方法。抗戰時期,中共中央高度重視反奸細斗爭,黨的六屆六中全會提出,如果不加強鋤奸工作,抗戰勝利是不可能的。1939年10月10日,專門作出反奸細斗爭的決議,要求將反奸細斗爭作為政治上組織上的重要任務,將保衛部門看作黨的工作不可分離的部門,責成各級黨組織的書記和軍隊首長首先負責,成立專門的工作部門,配備政治上堅定忠實、能力上勝任稱職的干部。[1]山東黨組織對鋤奸工作有比較深刻的認識,認為“黨的鋤奸保衛工作是黨的工作的一部分,是保衛黨、保衛革命的一種工作。黨的鋤奸保衛工作的本質是政治加技術。”[2]為加強鋤奸保衛工作,山東黨組織首先教育黨員干部從政治上正確認識鋤奸保衛工作,制定各種教材及反奸細的具體材料,用以教育全黨;建立健全各級鋤奸保衛部門,配備專門干部,舉辦干部訓練班,加強偵查審訊工作,鋤奸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績。但由于鋤奸政策存在一些錯誤,對奸細的定性存在偏差,有的鋤奸干部素質能力不高,偵查、審訊等工作方式方法存在逼供等,給革命事業造成不同程度的危害。
抗戰時期山東鋤奸錯誤主要表現在把托洛茨基派當作日本奸細,虛構夸大托派在山東的組織和破壞活動,在一定時期內把“肅托”(肅清托洛茨基匪徒)當作鋤奸的中心工作,把許多忠誠的黨員、干部打成托派逮捕、關押、審查甚至殺害,造成了一批冤假錯案。中國托派,又稱托陳取消派,是大革命失敗后產生的一個重要政治派別。在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前后,中國的托派分子成員已經很少,基本沒有活動,已沒有多大力量。從歷史事實來看,在八年抗戰時期,中國托派的觀點也是主張抗日的,不同之處在于在對待國民黨的態度上與中共不同。托派的錯誤在于不承認國民黨政府有抗日的可能,主張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政府,反對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攻擊第二次國共合作。起初,中共中央把中國托派看作是一個政治派別,積極爭取其共同抗日,后來鑒于中國托派反對國共合作,再加上受蘇聯、共產國際“肅托”等因素的影響,把托派定性為漢奸、奸細、民族公敵。康生1938年1月在延安《解放》雜志第29、30期連續發表題為《鏟除日寇偵探民族公敵的托洛茨基匪徒》一文,毫無根據地斷言托派分子陳獨秀、羅漢、俞秀松等人都是日本奸細、漢奸,并號召在全黨開展所謂肅托運動。[3]
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山東是托派活動的重要地區之一,在曲阜省立二師、濟南鄉村師范等學校確有托派組織和托派活動,“山東的托派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即開始發展,在此革命力量脆弱的地方發展的較大。”[4]在日軍進攻山東之時,大多數托派分子隨國民黨山東省政府撤往河南、湖北、重慶一帶,極個別托派分子如諸城的臧丙兮等留在山東參加抗日活動,事實上在山東已不存在托派組織,更遑論進行破壞抗日的活動。山東黨組織受肅托運動的影響,違反黨的實事求是的原則,對托派在山東的組織和力量缺乏正確認識,根據所謂口供,任意夸大,虛構出根本不存在的組織和破壞事實,錯誤地認為山東存在自上而下系統的托派組織,“至于托派的組織,上層有中央、有省委、有縣委,派到我們團體中的,每單位成立支部,支部中有委員、有書記;在支部下即小組,每小組三人至五人;一般的支委間、小組長間有橫的關系。”[5]如魯中地區泰山區鋤奸肅托“在認識上夸大了奸細的力量,認為奸細是成群結隊的集體活動。于是任意牽連,將許多黨內與群眾團體內的成員當成奸細,把思想認識、個人觀點、性格愛好、個人習慣等思想、行為當成奸細活動,以法律懲處、刑事處罰代替黨內思想斗爭、批評教育和行政處罰,采取所謂一網打盡、斬草除根等幼稚瘋狂的方式辦法去逮捕和處理,因而造成了錯誤”[6]“由于輕信口供隨意牽連,致使相當數量之無辜群眾被捕被殺”。[7]
基于對托派在山東活動的主觀認識,山東黨組織的鋤奸工作在指導思想上一度產生嚴重偏差,在1940年前后把“肅托”作為鋤奸工作的中心任務,號召“我們要以肅清托洛茨基分子為中心,展開廣泛的群眾鋤奸運動!”[8]中央對山東存在的對托派組織與事實相差甚遠的錯誤認識和鋤奸錯誤進行了嚴肅批評,中共中央社會部在1941年1月根據山東分局發給中央的鋤奸肅托報告所談內容,發出專門指示,明確指出西安有托派中央的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在華北各地所傳托派自上而下的組織省委、特委等等只能當作參考消息或敵探奸細的有意宣傳。中央社會部指出,山東分局單純依據口供,沒有充分證據,就確定全境有自上而下的托派組織,是不妥當的、危險的,對山東把“肅托”作為鋤奸工作的中心任務的指導思想提出尖銳批評:“分局社會部報告的整個精神把‘肅托’作為一切鋤奸工作的中心,在工作計劃和今后的工作方向上也僅僅提出‘肅托’問題,是不妥當的。這既夸大了托派的力量,又忽略了反對整個敵探漢奸的斗爭,因為托派只是敵探的一種,不等于敵探的全部,肅清真正的托派,只是鋤奸工作的重要任務之一,不等于鋤奸工作的全部。”[9]
由于鋤奸工作指導思想上存在偏差,在中央、山東分局多次下達指示要求糾正錯誤的情況下,仍有一些地區的區黨委和地委、縣委等固執己見,沒有及時改變認識,仍把一些黨組織領導的群眾團體無端懷疑為托派組織,把黨員、干部懷疑為托派分子。如直到1943年,膠東區黨委的主要負責人和鋤奸部門仍主觀認為膠東地區特殊,別的地方沒有托派組織,在膠東的地方、軍隊中都有一套系統的組織,有所謂的昌濰系、煙臺系、投降派系,在地方上存在中國托洛茨基膠東區委員會,區委之下有東、西、南、北四個分會,分會之下又有縣分會、區分會、支部、小組。[10]
由于在鋤奸保衛工作指導思想上違背黨的實事求是原則,導致1939年春至1943年初四年多的時間里,魯南、湖西、魯中、魯西、清河、膠東等山東抗日根據地各戰略區、山東分局、山東縱隊的司令部、政治部等機關及部隊等都開展了“肅托”運動,致使山東與其他抗日根據地相比,“肅托”持續時間長、涉及范圍廣,受牽連者眾多,被殺害的黨員領導干部也較多,造成一批冤假錯案。山東黨組織在認識到錯誤之后,陸續對一些鋤奸錯案進行了糾正。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得以恢復,黨中央不再堅持認為托派是漢奸這一不符合歷史事實的結論,重新對托派組織定性,山東鋤奸錯誤在此情況下,也得以徹底糾正。
二、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根本保證
山東發生鋤奸錯誤與抗戰初期山東抗日根據地在較長時間內沒有形成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有關。如發生鋤奸錯誤較早,且危害最為嚴重的湖西區,“殺死了這么多黨員干部,摧毀了這么多組織機構,竟始終沒有向山東分局報告,沒有向一一五師的首長報告,更沒有向黨中央報告。”[11]造成這一問題的重要原因就是當地未能形成具有權威的統一領導機構和領導核心。當時湖西區互不統屬,主力部隊是屬于一一五師序列的蘇魯豫支隊,地方黨組織蘇魯豫邊區黨委及其地方武裝則屬于中共山東分局領導,兩者由于在征召兵員、地方武裝整編等方面存在不同觀點和利益沖突,導致領導人之間矛盾頗深。如被當作托派分子殺害的湖西區委軍事部長張如,是湖西抗日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曾對參加過長征的蘇魯豫支隊第四大隊政委王宏鳴并編地方武裝的行為有所不滿,對其提出過尖銳批評,為王宏鳴所忌恨。王宏鳴個人品質惡劣,自恃握有軍事大權,看不起、不相信湖西地方黨組織的干部,且從本位利益和個人私欲考慮,對整個地方黨組織的干部和部隊中的干部,凡是不合其口味的都懷疑有政治問題,造成用槍桿子威脅湖西區黨委書記白子明,采用武力消滅了區黨委,造成惡劣影響。[12]由于黨、政、軍指揮不統一,沒有形成堅強有力的集中統一領導,導致在湖西“肅托”的三個多月里,一一五師政委羅榮桓、蘇魯豫支隊支隊長彭明治、山東分局書記郭洪濤等屢次阻止逮捕殺人的指示,得不到貫徹執行,最后只有一一五師、山東分局、山東縱隊三方主要負責人一起去湖西,才制止了事態的惡性發展,錯過了減少損失、解決問題的最好時機。
與其他抗日根據地相比,山東抗日根據地是在沒有八路軍主力部隊參與,由長期處于地下狀態的山東黨組織根據中央部署,結合山東實際,統一籌劃實施,組織發動群眾、舉行武裝起義、組建抗日武裝而獨立創建的,1938年底到1939年初主力部隊一一五師到達山東之前就初步形成。“在主觀方面,山東黨發展很遲,很年輕,干部弱。黨是由很少數量的地下黨很短時間內很快地創造與擴大起來的。”[13]1939年初一一五師進入山東后,與山東地方黨的領導機構山東分局成為分別接受中央和北方局領導的兩個互不統屬的平行組織,在較長時間內,山東黨組織的最高領導機構山東分局未能實現對全省黨、政、軍、民的集中統一領導。山東各戰略區也是這種狀況,致使山東各種矛盾交錯疊加,錯綜復雜。與此同時,一一五師和山東縱隊這兩支平行的部隊,均直接受中央和八路軍總部的指揮,互不統屬,相互之間爭奪兵源的情況也十分突出。當時中共中央為統一各地黨、政、軍領導,采取成立由各方參加組成軍政委員會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實際上由一一五師、山東分局、山東縱隊等負責人組成,由山東分局書記朱瑞任主任的山東軍政委員會,雖名義上是統一領導山東黨政軍群各系統的機構,實際上根本發揮不了作用,山東分局和山東縱隊、一一五師在戰略戰術、發展方向、統一戰線、群眾工作等問題上觀點分歧,想法各異,很難實現集中統一。
1942年,中共中央意識到,要度過抗戰困難時期,解決山東抗日根據地存在的鋤奸錯誤等問題,必須對山東領導機構進行調整,解決長期以來存在的黨、政、軍缺乏集中統一領導問題。于是,決定讓從蘇北新四軍回延安的劉少奇途經山東時代表中央解決山東矛盾和問題。2月4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朱(瑞)、羅(榮桓)相互不滿,發生爭論為時已久,中央未予解決。你經山東時請加考察,予以解決。”[14]劉少奇來山東后,經過調查研究和與各方負責人交流協商,指出了山東在發動群眾、統戰工作、武裝斗爭和鋤奸工作等方面存在的問題,初步解決了黨、政、軍之間的矛盾和認識分歧。1943年3月,山東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明確規定各級黨委是最高統一領導機關,羅榮桓成為山東黨政軍最高負責人,統一指揮山東各部隊,實現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對鋤奸工作進行全面總結,從而各地區的鋤奸錯誤才基本得以杜絕。1942年四月份,在劉少奇的指導下,山東分局先后作出關于泰山區鋤奸錯誤的決定、關于總結全山東鋤奸工作的決定,分析造成錯誤的原因,制定了開展鋤奸運動的正確政策和方法,要求“對湖西與泰山區之鋤奸錯誤經驗,分局負責制定文件教材,在全黨全軍中進行教育。”[15]
在1942年之前,山東鋤奸工作屢犯錯誤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未能實現,黨組織對各項工作的領導出現了弱化、虛化現象,黨內矛盾和問題不能得到及時有效的解決,甚至出現下級黨組織無視乃至公然違反上級黨組織指示的現象。有的甚至假借上級黨組織的名義和權威違背組織原則,以求達到自己的目的,結果是產生更多的矛盾和問題。黨對鋤奸工作在領導上重視不夠,缺乏有效的指導和監督。山東分局認為:各級黨委及政治保衛機關對鋤奸工作的領導不夠有力,脫離實際,過分地信任鋤奸干部,沒有把逮捕、審查和處決人命的責任真正承擔起來,輕易推諉到鋤奸干部身上。[16]
山東鋤奸錯誤得以徹底糾正和建黨近百年的歷史證明,只有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才能解決黨內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并為糾正黨內存在的錯誤傾向提供根本保證。只有不斷糾正錯誤,才能為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提供重要保障和支撐。山東鋤奸錯誤及其糾正、平反的實踐證明,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不能放松解決黨內問題;解決黨內問題,必須著眼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解決黨內問題統一于推進黨的自我革命,二者不可割裂偏廢。二者有機結合,才能相互促進、相得益彰,不斷解決前進中的困難和問題,促進黨的事業健康發展。
三、制度健全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重要基礎
在整個抗戰時期,山東負責鋤奸肅托的機構在地方先后是保衛局、社會部和公安局。起初鋤奸工作沒有得到真正重視,更談不上履行嚴格的制度和程序,對逮捕、處決的權力由哪一級負責也沒有明確具體規定,各地自行其是,任意妄為,“各地亂打亂罵亂捕亂殺的事非常普遍,非常厲害,甚至兒童團都可以隨便殺人。”[17]如泰山區鋤奸就以反“掃蕩”為借口,一次處決18人,“以國家法律的處罰代替黨內思想斗爭和行政上教育處罰,以一網打盡、斬草除根等幼稚瘋狂的辦法去逮捕處理”[18]“將許多黨內落后分子、異己分子、社會中的落后分子當成奸細捕起來殺掉”。[19]
劉少奇到山東后,在對鋤奸工作進行總結時,反復強調建立相關制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山東分局避免鋤奸錯誤再次發生,要求在鋤奸工作中要保障黨員的權利,嚴格紀律,嚴格程序,“任何地區或軍隊逮捕任何一名共產黨員,必須經過分局、師政、縱政批準后執行。否則一經查出,直接負責之黨委及鋤委同志應受黨紀嚴重處分,一直到開除黨籍。此后一切奸細案件的極刑批準權屬于分局、師和縱隊,各區黨委與旅支取消批準權。現行犯或特別情況下,區黨委、旅支政治部可負責批準執行,但須報上級審查,如不合適,區黨委或旅支負責人應受處罰。那些不經批準而隨意進行逮捕或處決的人,應依情節送司法或軍法機關判罪。對犯罪人予以上訴權,一直可訴到分局、戰工會、師部、縱隊。”[20]
重視制度建設是黨的優良傳統和優勢,也是從近百年來黨的波瀾壯闊的發展進程中得出的寶貴歷史經驗。山東鋤奸錯誤及其糾正、平反的歷史充分說明,只有加強黨的制度建設,依法依規治黨,建立科學合理、符合實際、運行良好的體制機制,嚴格執行各項制度,才能不斷改正錯誤,永遠保持黨的純潔性和生命力。
四、高素質專業化干部隊伍建設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組織保證
突出政治標準是黨的優良傳統,是我們黨選人用人的一貫方針。高素質表現為政治過硬,是黨員干部內在的政治素養。領導干部要做到加強黨性鍛煉,不斷提高政治覺悟和政治能力,把對黨忠誠、為黨盡責作為根本政治擔當。專業化表現為本領高強,要求干部隊伍在專業能力上不斷增強專業本領,具有專業作風、專業精神。政治過硬、本領高強是融會貫通和有機統一的。山東鋤奸及其糾正平反的歷史,從正反兩方面充分說明,只有重視干部的選擇、培養,建設高素質專業化的鋤奸保衛干部隊伍,才能避免鋤奸錯誤的發生。
抗戰時期山東在鋤奸保衛干部的選擇上存在偏差,往往忽略干部的政治素質,過分注重鋤奸工作的技術性,致使干部整體素質不高,特別是對政策把握不夠準確。“鋤奸干部和黨的干部對鋤奸政策認識的不具體、不辯證,運用的不靈活,甚至有討厭鋤奸政策的,以為這政策會限制了他的自由。”[21]如泰山區在召開各縣公安局長會議時,不從鋤奸工作的實際出發,簡單制定量化指標,逼著各縣公安局長按月提出殺人計劃數字。而一些堅持原則,有獨立見解,工作認真負責,對鋤奸工作的問題敢于對上級提出不同意見的鋤奸干部,受到排擠打擊,甚至成為鋤奸肅托的對象和受害者。
有的鋤奸保衛干部專業化水平極低,對偵察審訊毫無技能,只是一味使用肉刑逼供。保衛干部專業化水平低的一個表現,就是對革命隊伍中的知識分子有偏見和歧視。從山東各地鋤奸受害者的成分分析,以知識分子干部居多數,工農干部相對較少。知識分子干部一般具有獨立思考精神和個人見解,社會背景和社會經歷復雜。他們被懷疑為奸細的理由五花八門,有的對上級領導不滿,有的對職務工作安排不滿,有的因資歷深瞧不起直接上級領導,有的因為性格因素,如好開玩笑,經常說一些調皮話等,有的是因為與鋤奸干部有矛盾摩擦等等。從山東各地鋤奸肅托的整個情況來看,宣傳、教育等知識分子干部相對集中的部門是重災區,鋤奸肅托一般是從這些部門開始,被打成托派而慘遭殺害的人往往最多。鋤奸肅托受害者另一個重要群體是抗戰爆發后從外地來山東的平津流亡學生、民先隊員和從延安來的知識分子干部。一些在抗日軍政大學、陜北公學、八路軍隨營學校、臨汾學兵隊等學習的黨員干部被當作奸細托派懷疑對象,受到逮捕、審查、殺害。
由于一部分鋤奸干部政策水平低下,把主觀的懷疑估計當作客觀的事實,將黨內錯誤與破壞抗戰的犯罪行為混為一談。從各地最初的鋤奸情況看,將敵我矛盾和黨內矛盾混為一談,分不清思想認識問題和政治原則之間的區別,把想像當事實,把語言當行動的現象比較突出。
鋤奸干部隊伍中個別人品質惡劣也是造成鋤奸錯誤的重要原因。湖西鋤奸肅托的始作俑者、湖邊地委組織部長王須仁曾在北京大學上學,工于心計,善于察言觀色,對領導投其所好,鉤織罪名隨心所欲,善于阿諛奉承、投機鉆營,翻手為云、覆手為雨,有的干部積極肯干,他就說這是偽裝,是為了騙取領導的信任;有的干部自由散漫、干勁不足,他又說這是仇視抗戰事業,進行消極破壞。[22]1941年冬泰山區學山案件和泰萊邊案件的始作俑者,分別是萊蕪縣上游鎮公安特派員李友恩和萊蕪縣西北區店子村公安員陳殿文,是品質惡劣的鋤奸干部典型。李友恩為掩蓋自己故意殺人的罪行而陷害他人;陳殿文為躲避參軍、表現成績,偽造奸細的文件和一本托派分子登記表及托派在香山區的活動地圖,交給公安干部邀功;泰山區公安局不做認真調查分析,把漏洞百出的材料當成證據,致使100多人被逮捕,香山區區長等多人被殺。山東縱隊第一支隊的鋤奸肅托錯案導致38人被殺害,也是因為鋤奸科長王文軒的個人品質問題而造成的。
結語
抗戰時期鋤奸錯誤自1939年春發生到1989年徹底糾正平反,歷經五十年的時間,這一歷史進程充分闡釋了敢于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具有自我革命精神是黨的政治品質和精神本色。研究山東鋤奸錯誤及其糾正、平反的歷史,對于黨在新時代不斷增強自我凈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具有極其重要的借鑒和啟迪作用。山東鋤奸錯誤及糾正、平反的歷史給我們留下的借鑒和啟迪是:必須時刻遵循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為了人民利益堅持真理、修正錯誤;必須始終堅持將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和解決黨內矛盾統一于推進黨的自我革命;必須時時不忘制度建設的重要性,把黨的制度建設貫穿于黨的政治建設等各項建設始終;必須把思想政治素質放在第一位,重視干部的教育培訓,建設高素質專業化的干部隊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