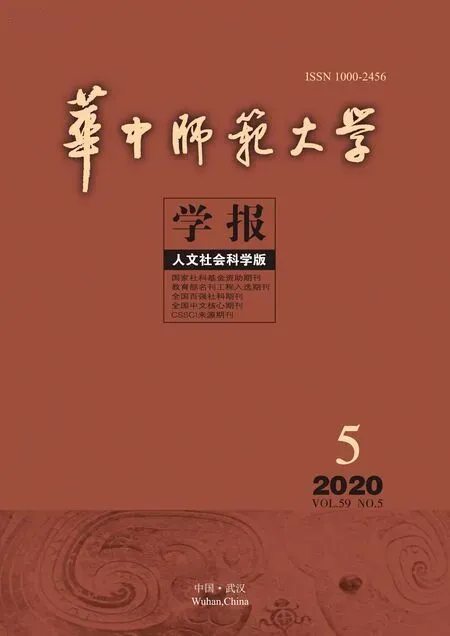老舍訪日與20世紀60年代的中日文學交流
余 迅
(華中師范大學 文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79)
20世紀60年代,受《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簽訂的影響,“美帝國主義”成為了中日兩國人民共同的敵人,在此背景下兩國作家互訪頻繁,1965年由老舍任團長的中國作家代表團在日本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訪問。對于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的訪日經歷,老舍并沒有留下太多的文字,本應該發表的長篇散文《致日本作家的公開信》,也“石沉大海,杳無音信”①。關于老舍訪日的研究成果,多為基本情況的介紹②,鮮見對于訪日背景、中日作家交流、訪日意義等問題的探討。本文通過梳理老舍相關文獻,日本作家和新聞界的記述文字,回到歷史現場,嘗試窺視晚年老舍的心境,考察20世紀60年代中日文學交流所呈現出的歷史特征。
一、老舍訪日的背景和概況
1965年3月24日至4月28日,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了日本。此代表團由老舍任團長、劉白羽任副團長,成員還有張光年、杜宣、茹志鵑等。
在眾多老舍傳記中,這次出訪被描述為“極為愉快的一次國外旅行,完全生活在友好的情誼之中”③,一次“能暫時避開政治陰霾的外事活動”④。這類說法基本與《人民日報》《朝日新聞》的宣傳保持一致。代表團到達日本時,《人民日報》的報道為:“代表團受到日本文化界和其他各界知名人士、東京華僑總會代表共一百多人的歡迎”⑤。《朝日新聞》更是在代表團訪日前兩周開始預熱:“他們是受亞非作家會議日本協會(負責人堀田善衛)的邀請,計劃在日本停留1個月”⑥,“日中文化交流協會與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之間于去年10月在北京簽訂了1965年度日中兩國文化交流計劃,本次就是按此計劃實施的交流活動”⑦。
但是,這種友善平和的外表顯然隱藏了當時復雜多變的國際形勢。新中國成立以后,在“冷戰”的背景下,日本政府為了追隨美國,一直為中日文化交流設置種種障礙。直到1955年,以郭沫若為團長的中國科學代表團訪日,才實現了兩國學術界的首次互訪。但因“長崎國旗事件”和“新日美安全條約簽訂”的影響,中日文化交流舉步維艱。1960年以后,隨著中日政治關系的緩和,新中國作家才真正意義上踏上日本的國土⑧。在老舍訪日之前,中國作家代表團曾兩次訪日。1961年3月,巴金率領代表團參加了“亞非作家東京緊急會議”。自1958年參加在蘇聯烏茲別克塔什干召開的第一屆亞非作家會議以來,中國作家參加“亞非作家會議”就成為國家外交工作的一部分,通過在文學領域與新興的亞洲獨立國家展開交流與合作,有利于在美蘇兩大陣營之外,尋找到新的發展空間⑨。因此,亞非作家會議為中日作家的交流提供了親密接觸的機會。而此后1963年巴金和冰心的訪日,1965年老舍訪日也被納入國家的外交軌道。
此次中國作家代表團的成員構成頗有“新意”。團長老舍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在日本也頗具聲望。日本戰后曾出現過“老舍熱”,《四世同堂》被翻譯到日本后,產生了強烈的反響。《駱駝祥子》在日本也讀者眾多,先后出現過七個日文譯本⑩。因此,《朝日新聞》為了引起日本讀者的關注,報道中大多以“老舍”為標題。其次,副團長劉白羽,時任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1958年開始參與亞非作家會議籌備委員會的工作,1961年就曾訪問過日本,對日本文學界非常熟悉。而團員張光年不僅是評論家代表,而且時任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書記,能夠很好地把握訪日的政治方向。另一團員杜宣則早年留學日本,1960年代之后,一直擔任中國作家協會派駐亞非作家會議常駐代表,與很多日本作家交往頗深。年齡最小的茹志鵑是代表團中的“青年骨干”,這次與前輩作家出訪也表明獲得了某種“承認”,她的加入不僅展現了當時中國女作家的精神面貌,也有利于在與日本女作家交流時更好地開展工作。
在一個月零四天的行程中,老舍一行參觀了東京、大阪、奈良、京都、箱根、鐮倉、仙臺、日光等地名勝,拜訪了近30位日本知名作家、評論家的私邸,參與了亞非作家會議日本協議會、京都大學中國文學會的活動,與日本腳本作家、京都業余女性文學愛好者等群體進行了交流。這次被日本學者稱為“超人”行程的日本之旅,對于已經66歲高齡,腿腳不便,因為高血壓經常無法寫作的老舍來說,顯然頗為“辛苦”。在日本作家回憶中,訪日時期的老舍“清瘦矮小”“顯得特別老”,“象個終身終世埋頭于某項手藝的工匠”。
從一些細節還是能夠察覺到這次訪日之行的“危險”。因為中日當時并未建交,只能從香港中轉。“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之后,出訪時的航班安全成為了敏感話題。在香港等待赴日的老舍,經常無法入眠。另外,在中國代表團下榻的賓館旁常有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法西斯主義分子“游行示威,雜以怪叫”。
老舍的訪日之行并沒有后來敘述中那么“愉快”,夾雜其中是嚴肅的外交任務,繁重的日常行程以及危機四伏的環境。但為了打破中日交流之間的壁壘,年邁的老舍愿意克服困難,承擔起那份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此他在“疲憊”背后,始終給周圍人一種“硬硬朗朗”的感覺。
二、對日印象:源自日記與舊體詩
收錄于《老舍全集》的1965年日記,只有3月20日至4月29日赴日期間的記載。其中對于去過的地方,遇到的人,甚至吃過飯的菜單,事無巨細,依次羅列。但這些文字多為碎片式,表達也缺乏邏輯,看上去像老舍為創作長文準備的素材。其次,日記中并沒有過多表現初訪東瀛的興奮,只有“飲酒寫詩,甚快”“路過蘆湖,甚美”“極倦怠”等為數不多的情緒表達。
這種語言上的“謹慎”,并不是個性使然,對比老舍1961年夏天的內蒙古之旅,他不僅發表了三十余首舊體詩,還創作了新詩《扎蘭屯的夏天》,散文《內蒙風光》《可愛的內蒙古》等,他動情地寫到:“我是那么快活,我時時刻刻總想唱一支歌!”情感體驗的“缺失”,也不完全是外事紀律的要求,因為其他作家留下了極具“感情色彩”的文字。劉白羽在《櫻海情思》中深情描述了這次充滿美好回憶了櫻花之旅:“我在這大地上行走過,我不只留下腳印,我也留下我的一段生命。”而張光年則永遠難忘好友龜井勝一郎在病重之際卻堅持出席酒宴,“向中國作家告別,也是向他多年共患難的親密戰友告別”。
訪日途中老舍的“沉默”,可以作為他晚年心境的一種寫照。一方面,訪日前的幾年,老舍已經漸漸遠離文壇的中心,創作數量也是逐年減少,面對各種批判活動,他大多采取了不表態的緘默態度。另一方面,在訪日期間,他身處多種角色之中,當作為文化官員時,他時刻要維護國家的形象,發表符合國家意志的言論;但是作為作家,他又希望有屬于自己的獨立空間,可以沒有“束縛”地進行精神交流。當老舍無法化解不同身份造成的重重矛盾時,他只能選擇用一種“沉默”來隱藏真實的情緒,或者用較為含蓄、曖昧的話語來表達。
老舍訪日期間共創作了34首舊體詩,其中多為應日本友人邀請寫的贈答詩。這些詩主要寫給一直投身于中日文化交流、曾訪華過的日本學者文人。針對不同的對象,老舍在創作時有著各自的考量。如《贈白土吾夫》:“白花笑對紫花開,土暖風輕春雨來。吾輩生涯愛勞動,夫隨婦唱菜親栽。”就是一首藏頭詩,對應了“白土吾夫”的名字。白土吾夫自1956年開始參加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事務局工作,曾接待梅蘭芳為團長的中國京劇代表團訪日演出,隨后曾一百多次訪問中國,為中日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在老舍訪日過程中,他幾乎全程陪同,這首詩就表達了老舍對于老朋友的感謝。又如《贈土歧善麿》一詩:“白也詩無敵,情深萬古心。愁吟啟百代,硬語最驚人。”3月25日的《老舍日記》中,在“土歧善麿”名字的后面標注有“杜詩”的字樣,可見老舍對于接觸的日本友人有過詳細的了解。土歧善麿是日本著名的歌人和國文學者,曾翻譯杜甫詩歌,著有《新譯杜甫詩選》。在詩中,老舍首句就摘用了杜甫《春日憶李白》中的“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中的句子,后面“愁吟”“硬語”也反映了杜甫詩歌的典型特征與風貌。老舍晚年的舊體詩呈現出“師唐傾向”,他對于杜甫詩歌的駕輕就熟,使得在同日本友人交流過程中,讓對方很容易體會到來自中國的美好情誼。收到老舍贈詩的日本友人,也會用和歌的方式進行唱和,如日本詩人扇畑忠雄就寫有:“孤芳自賞還自憐,老舍先生倚杖前。”
訪日期間,老舍還創作了不少紀游詩。其中既有對京都美景的贊賞,也有對奈良歷史古跡的感懷,還有給聶耳墓獻花時對“譜歌人”的紀念,以及在仙臺魯迅碑前對先賢的敬仰。老舍的紀游詩同樣充滿著唐詩氣質,詩歌中的意象、色彩、聲音都映照著盛唐文化的圖景。比如在游覽奈良的時候,老舍寫道:“阿倍當年思奈良,至今三笠草微黃。鄉情莫問天邊月,自有櫻花勝洛陽。”第一句敘述了日本奈良時代的遣唐使阿倍仲麻呂來中國留學的歷史,第二句古今對比,“三笠”一詞則點出了阿倍仲麻呂《三笠詞》中“春日三笠山,明月出山前”的典故。“明月”和“洛陽”都是唐詩中經常使用的意象,“微黃”“櫻花粉”中明亮的色彩對比也輝映著盛唐景象。
老舍在回國之后,曾把在京都和奈良時寫的不少紀游詩寄贈給郭沫若,請他“斧正”。郭沫若也曾創作過相似的舊體詩,1955年在訪問奈良的唐招提寺時,他寫下《拜鑒真上人像》:“弘法渡重洋,目盲心不盲。今來拜遺像,衷懷一瓣香。”這首詩表達了對鑒真這位中日友好先驅者的崇敬。同為致力于中日交流的著名作家,老舍和郭沫若在創作時,經常從歷史中汲取中日文化之間的認同感,其中既有對中日文化使者的懷念,也有對于源自中國的日本文化中服飾、飲食、禮儀的青睞,而承載各種情緒的舊體詩則成為傳遞情感時中日文化人之間重要的紐帶。
三、拜訪作家:傳遞友善與期待
老舍在訪日過程中,行程密集地前往了中島健藏、龜井勝一郎、白石凡、芹澤光治良、木下順二、阿部知二、志賀直哉、依田義賢、谷崎潤一郎、大岡升平、丹羽文雄、水上勉、井上靖等人私邸,加上在歡迎會上的交流,可以說與當時的日本文壇有了一次深入的接觸。
這些作家中,老舍最熟悉的就是一批投身于中日文化交流的左翼作家和評論家。在訪日之前,老舍就曾多次與來華訪問的日本文藝界人士進行過交流。如木下順二回憶,在1964年訪華期間曾專門前往人藝看《茶館》,在老舍家中與他愉快地談論起“日本崇尚菊花”的話題。因此,日本作家期待通過老舍訪日,在向中國作家介紹日本文壇現狀的同時,讓日本讀者有機會和老舍見面,使得中日之間的交流更加的“有效”。
老舍一行到達日本之后與時任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中島健藏以及副會長龜井勝一郎有過多次的會面。特別是回國前的聚餐,劉白羽和張光年后來均回憶,這其實是病重的龜井勝一郎與中國友人間“最后的晚餐”。1949年以后,正是在這批日本左翼作家和評論家的努力下,中日文壇間才保持了持續的交流,正是中日作家朝著共同目標執著追求,才促成了此次老舍之行。
老舍訪日期間接觸最多的日本作家之一是井上靖。通過這次的交流,井上靖體會到了老舍作為團長角色的艱難,“老舍應對有方,機敏周到。看來他始終在努力不要讓對方感到不滿意”。日本作家對于老舍,不像郭沫若、巴金、冰心那樣熟悉,因為他之前并沒有留日經驗。例如井上靖曾提到一個細節,老舍曾在宴會上講了一個關于“壺”的故事。一位破落子弟藏有一只珍貴的瓷壺,因不愿意讓覬覦的富豪家得逞,選擇與壺一起同歸于盡。日本老作家廣津和郎聽后“當場駁斥”,認為在日本面對如此珍貴的寶物,“決不會去摔破它們的”,場面一度比較尷尬與緊張。就如劉白羽后來所說,“其實老舍和廣津各自講出各自的道德典范:老舍說的是面對橫梁,寧死不屈;廣津說的是不顧自己,珍惜國寶”。但這體現出日本作家對于老舍的某種“隔膜”,他們并不了解老舍講這個故事的原因,既不會把它當成一個“助興的笑話”,也不會體察到老舍當時的境遇與這個故事之間的內在聯系。老舍去世后,當井上靖再次提起這個細節,日本作家開始反思,認為這個故事是老舍命運的寫照,對于老舍的人格肅然起敬。老舍的形象在日本作家眼中,經歷了一個從“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到“令人敬佩的作家”的轉變。
老舍出訪的重要任務是做“中間力量的工作”,與這類作家交流時顯然更需要把握尺度與注意技巧。水上勉就是對象之一,他是當時日本炙手可熱的作家,因發表《霧與影》《海的牙齒》《饑餓海峽》等作品廣受好評,他的小說社會批判性強,常常以揭發社會黑幕為主題,被認為是社會派推理小說的代表。但在1965年之前,水上勉對于“中國的情況一無所知”,作家老舍更是“不大熟悉”。在《蟋蟀葫蘆》一文中,他回憶了老舍造訪的經歷。老舍“質樸”的第一印象拉近了與貧苦出身的水上勉之間的距離。他們并沒有討論政治外交的話題,而是從“蟋蟀葫蘆”這個小物件聊到了民間習俗,談話在老舍邀請水上勉訪華的美好期盼中結束。若干年后來看,這顯然是一次“成功”的外交活動,以老舍為代表的中國作家給水上勉留下了博學多聞、平易近人的印象。此后,水上勉曾多次訪華,為了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老舍與日本青年作家的交流也值得注意。老舍曾創作過一首名為《贈有吉佐和子》的舊體詩,其中寫到:“有吉女文豪,神清筆墨驕。驚心發硬語,放眼看明朝。”有吉佐和子是日本戰后著名的女作家,作品擅于揭露社會問題,特別是長篇小說《非色》(1963)批判了美國社會中的種族歧視,以及“世界各國的不平等思想”。雖然除了那首舊體詩,老舍沒有留下其他文字,但是從老舍去世后,有吉在中國訪問期間,特意走訪調查尋找老舍死因可以看出,兩人已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來自老舍的信任與友善,使得這位日本青年作家更加明確想要了解中國的愿望,日后完成了《有吉佐和子的中國報告》等作品。
在訪日過程中,老舍雖然在情感上并沒有過多的外露,但是在和日本作家交流的過程中,努力傳達了來自中國作家的善意。對于老朋友一直以來的情誼,老舍格外地珍視;而對于日本青年作家的支持與鼓勵,也顯示出他對未來中日兩國文化交流的某種期待與憧憬。
四、媒體訪談:為中國文化界發聲
老舍在日本接受的媒體專訪以及與日本作家的對談,為考察本次訪日之旅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進入20世紀60年代,日本進入了高速發展期,在“安保運動”中明確的政治獨立目標,也慢慢轉化成了對于經濟問題的關注。在地方人口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城鄉貧富差距的加大,使得一部分日本知識分子站在了反商業主義和社會批判的立場,而面對著意識形態完全不同的近鄰中國,他們急需從中國經驗中尋找方法,破解自己的文化困境。因此,面對著老舍一行,日本文藝界最關注的問題可以用現在、傳統、未來這三個關鍵詞來概括。
1965年3月29日,《朝日新聞》就關心的“中國文學界的現狀”等問題采訪了老舍。老舍高度肯定了梁斌、楊沫等作家表現“無所畏懼的革命者的優秀作品”;對于“深入生活,描寫人民”的創作方法,老舍表現出謙虛的態度,認為自己對“全新組織”了解得還不夠透徹。當被提問到如何評價邵荃麟“中間人物”的觀點時,他認為“‘中間人物’本身是并不壞”,但“邵荃麟只是一味強調這點是不對的”。
眾所周知,1962年大連會議中邵荃麟提到的“中間人物論”的觀點,在此后幾年受到了嚴厲的批判,1964年更是發展為震驚中國文壇的“中間人物”事件。日本學者一直持續關注此事進程,對于“中間人物論”的觀點也進行過深入探討。例如竹內實在《中間人物論》中認為,通過了解以“中間人物論”批判為代表近來中國文壇的動向,有利于加深對于中國的認識。他敏銳地指出,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日本讀者與邵荃麟的意見一致,認為人物有過于簡單化的傾向,但他們僅就基本的文學常識發表觀點,并沒有觸及中國文學的根本問題,而“中間人物論”的提出及其批判問題遠比觀點本身更為重要。
而以上老舍的回答,顯然看到了批判者與被批判者之間的錯位,較為曖昧地點明問題的本質。與之相對,張光年在向日本讀者介紹“中間人物論”這一觀點時,則直接表明了批判的立場,認為這是用修正主義的理論,用同情的態度描寫走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時一種苦難和痛苦的過程,這是違背現實的。
而在與武田泰淳的對談中,老舍少了些拘謹,多了幾分朋友間的“暢所欲言”。他們的對談主要圍繞著文學創作的主題,老舍以作家身份向好友介紹了最新的寫作計劃。他極為真誠地表達了內心的矛盾,一方面覺得應該通過體驗生活,書寫全新的中國大眾的生活;但是一方面卻“不知不覺中,也常帶著從前的生活,從前的感情,不能把變化后的新生活寫得詳盡”。老舍吐露了“五四”新文學家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創作轉型之艱難,雖然已經在創作理念上徹底向工農兵文學看齊,但在創作的具體過程中,已經形成的創作風格很難在短時間內完全改變。
中日兩國都有著悠久的歷史,面對著現代化帶來的沖擊,如何對待文化遺產,成為兩國作家在交流過程中關注的話題。例如在一次訪談中,日本作家木下順二向老舍詢問關于“京劇現代化”的問題。老舍認為京劇作為中國數百種地方戲曲的代表,對其進行改革具有指導意義。他提出要在京劇中融入現代主題,用這種古老的形式為社會主義新社會服務,而對于老的劇目,也并不是完全放棄,只是目前以現代主題為主。而在仙臺召開的交流會上,老舍同樣指出,對于京劇的改革,就是要在京劇里反映工農兵的生活,因此作為創作者要去體驗工農兵的生活,寫出以工農兵為主的作品。而面對相同的問題,劉白羽的回答則和當時中國國內外的政治形勢結合更加緊密。劉白羽指出,國際社會普遍關注中國的京劇改革問題,其中也包括“惡意”攻擊,給這個古老藝術形式注入新的生命力是一項時代的任務,能夠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
對于“未來”的闡釋則是老舍一行訪日的主要目的。中國作家代表團努力踐行中國政府當時的外交政策,希望通過影響日本在內的亞非拉國家的世界想象,建構第三世界的共同體。例如,老舍多次在訪談中提到了“亞洲文藝復興”的想法:“以中國和日本為代表的亞洲和非洲各國,自古以來就有燦爛優秀的文化,但是近代以來,由于受到外部的壓迫,被推廣的文化越來越少了。……如果他們攜起手來,一定可以振興新的文化,為世界文明的進步做出貢獻。”與老舍的觀點形成呼應,劉白羽在談到重寫世界文學史時指出:“過去的世界文學史,老實來講總是以西方為中心來寫的。奮斗多年已經覺醒的亞洲人民,面對當前亞洲的斗爭現實,為什么不會出現好的文學作品呢?”
在20世紀60年代中蘇交惡的背景下,中國領導層十分重視與亞非拉各國之間的關系,將其視為反帝國主義的重要力量,日本顯然在這些國家中有著重要的戰略地位。而以老舍訪日為代表的中日文藝界交流,不僅僅是中國政府的外交宣傳,也為戰后日本知識分子在反思日本與亞洲關系,建構新的世界秩序時提供了不一樣的思路。
結語
近代以來,中日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雖然受到戰爭等政治因素的影響,時而順暢親密,時而困難重重,但并沒有中斷。新中國成立之后,面對當時復雜的國際形勢,作家出訪成為重要的民間外交手段,承擔著外交上的聯絡任務。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中日作家的互訪經驗為兩國間的文學交流提供了一個新的途徑,通過作品的翻譯和介紹,直接面對面的親密交流,逐漸加深彼此的理解,形成中日友好的社會風氣,讓政治、經濟領域的合作變成了可能,進而為70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對于中國作家來說,出訪日本既是懷舊也是探索。1955年之后,郭沫若、巴金、冰心等一大批重要作家訪日,他們中有的曾早年在日本求學和工作,訪日之旅變成尋訪舊時光、邂逅老友的契機。而同時,訪日經驗帶給中國作家更重要的是對于戰后日本的全新認識與重新理解。他們一方面感嘆于日本日新月異的變化,資本帶來的物質上的高度繁榮;另一方面也對商業社會天生具有的拜金本質,資本主義對于社會的毒害充滿著警惕。如茹志鵑面對著機場通往市區的高速公路,清晰地認識到,“這是為鋼鐵資本家開辟道路,這樣鋼鐵就有了銷路”。老舍在日本特地參觀了農戶家庭,他敏銳地發現了貧富的差距:政府大量扶植中農以上的農民,但貧農們面對著來自美國進口農產品的沖擊,只能勉強維持生計。日本變成了一個參照物,讓中國作家對于自己祖國的社會現狀和歷史進程有了更深層的認識和體悟。
出訪日本時,中國作家都十分注意言行,盡量避免由于意識形態不同造成的爭端與沖突。他們在與日本作家交流的過程中,在表達自身立場的同時,傳遞來自中國的善意,努力營造亞洲共同體的印象。回國之后,作家代表團還召開報告會,把訪日期間的所見所思傳達給其他文藝界人士,如文潔若就回憶,老舍曾在文聯禮堂做過專題匯報,并評價從未聽過“如此生動的報告”。這種信息的傳遞有利于改變二戰以來中國對于日本的刻板印象,而加深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
而從日本作家的角度來看,老舍一行訪日,是“過去十年間日中文化交流的基礎上結出的果實”。戰后日本左翼作家一直對于中國百廢待興的革命事業非常關注,努力創造條件來華訪問交流。特別是60年代以后,圍繞著《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簽訂問題,日本國內興起聲勢浩大的“反美”浪潮,中國對于日本民間組織反美立場給予高度評價并明確聲援。而表現在文藝界,日本作家在亞非作家會議等國際舞臺上不斷發聲,希望尋求盟友,打破冷戰背景下的對立局面,因此他們格外重視與一衣帶水的中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日本作家通過各種機會訪華,創作了大批和中國有關的文學作品與報告文學。
作家出訪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方式,這種民間外交的形式,有利于拉近彼此之間的距離,從而進一步推動國家間在政治與經濟上的合作。老一代作家因為有著廣泛的國際關注度,更利于擴大出訪的影響力;而年輕作家更容易在出訪中感受到異文化帶來的沖擊,進而影響之后的創作。另外在與東亞漢文化圈的文人交往時,從歷史中尋找文化間的認同感,通過諸如舊體詩的酬唱等方式,更加能夠傳達情意,引起共鳴。
注釋
①③舒乙:《我的父親老舍》,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5頁,第144頁。
②例如孟澤人在《印在日本的深深的足跡——老舍在日本的地位》(《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1期)一文中,對老舍訪日期間拜訪過的日本作家、前往的地點、日方相關報道做過整理。
④克瑩:《患難情緣:老舍與胡絜青》,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33頁。
⑤《我作家代表團到日本訪問》,《人民日報》1965年3月27日,第6版。
⑥「中國の作家代表団近く來日」,『朝日新聞』1965年3月8日,第12版。
⑦「老舎氏、日本へ中國作家代表団長で」,『朝日新聞』1965年3月10日,第14版。
⑧參見孫承:《近現代中日文化交流概說》,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145-171頁。
⑨參見王中忱:《走讀記》,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7年,第149頁。
⑩參見布施直子:《老舍在日本被接納之狀況》,《漢語言文學研究》2015年第1期。